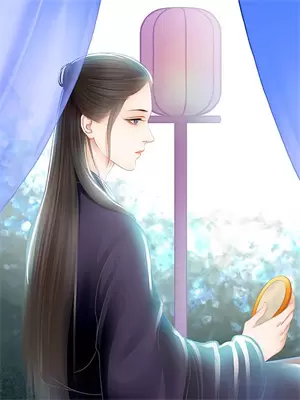序言那年夏天的事,我到今天都不敢晚上独自靠近河边。那天晚上,村里放《地雷战》,
我和小马正看得起劲,一扭头,竟看见一个人从河里直挺挺地走上岸,
混进了看电影的人群里。他浑身湿透,脸色灰白,两眼凸出,就悄无声息地蹲在廖俊身后,
地上淌了一摊水。我吓得从凳子上摔下来,小马却笑我胆小。可第二天一早,
廖俊淹死在河边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和他一起浮上来的,
还有邻村已经死了好几天的二狗。那张脸,就是我昨晚见到的那张。村里老人都说,
那是水鬼趁人多上了岸,找了替身。如果你也听过这样的传闻,记住,
夜里看电影……千万别坐在靠近水边的那一排。--第一章 夏夜盛宴那是1998年夏天,
我十二岁。乡村的时光总是慢得像村口那棵老槐树上滴落的树脂。漫长的暑假里,
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或者在场院里追逐打闹。直到那天下午,
"放映队要来"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庄。"叶子!叶子!晚上放《地雷战》!
"小马像一阵风似的冲进我家院子,满脸通红,汗水顺着鬓角流下,"快点吃饭,
去晚了就没好位置了!"小马大名马建军,是我最铁的哥们。我们同年同月生,
一起光屁股长大,一起上的村小学。他胆子大,我心思细,
性格互补的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母亲在灶台前忙活,笑着说:"看把你们急的,
那片子都看八百遍了。""不一样,妈!在场院看和在家里看不一样!"我一边帮着摆碗筷,
一边争辩。确实不一样。露天电影是全村的大事,那种集体狂欢的氛围,
是现在任何IMAX影院都无法比拟的。那天晚饭我吃得心不在焉,
玉米面饼子嚼在嘴里不知其味,心思早已飞到了场院。匆匆扒完最后几口,
我抓起那个专属我的小木板凳——那是爷爷亲手为我做的,
凳面上还有我七岁时刻的歪歪扭扭的名字——冲出了家门。夏日的白昼格外漫长,
虽然已是傍晚七点多,天色却还未完全暗下来。西边的天空燃烧着壮丽的晚霞,
给田野、房屋和树木都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的边。通往场院的小路上,满是兴高采烈的人群。
男人们叼着烟卷,讨论着今年的收成;女人们三五成群,
手里拿着针线活;孩子们更是像出笼的小鸟,在人群缝隙中追逐嬉戏。"叶子,这边!
"小马早在场院边缘向我招手。我们像两条灵活的小鱼,在越来越密集的人群中穿梭,
最终在距离幕布约十米远的地方找到了理想位置。这里不算太近伤眼睛,
又能清晰地看到屏幕上的每一个细节。场院上弥漫着一种节日般的气氛。
放映员老张正在调试机器,那台老旧的放映机发出熟悉的"咔哒"声,
一束光柱射向白色幕布,上面晃动着各种形状的光影。
孩子们兴奋地用手在光柱中做各种手势,幕布上便出现了小狗、小鸟的影子。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星星开始在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中,
电影正式开始。熟悉的音乐响起,"地雷战"三个大字出现在幕布上,
场院里爆发出一阵欢呼。
第二章 河边的黑影电影演到高潮部分——鬼子工兵偷地雷出尽洋相,场院里笑声此起彼伏。
小马笑得前仰后合,用力拍打着我的后背:"叶子你看那个鬼子,
像不像咱们学校王老师走路的样子?"我本来也笑得开心,但突然间,
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脊背升起。那不是夜晚的凉风,而是一种粘稠的、阴冷的感觉,
仿佛有人把一块冰贴在了我的后颈上。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场院的西边。场院西边约百米处,就是那条被称为"界河"的小河。
河面不宽,但老人们都说它"宽不过十丈,深不见底"。夏天这里是我们的乐园,但天一黑,
就很少有人靠近。传说这条河淹死过不少人,尤其是我们出生前的那场大洪水,
据说一下子卷走了七八个人。我的目光在昏暗的河面上扫过。起初一切正常,
河水在逐渐暗淡的天光下静静流淌,对岸的芦苇丛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但就在我准备收回目光时,河心处突然出现了不寻常的动静。
一个黑色的物体缓缓从水中升起。先是头顶,然后是肩膀,最后是整个上半身。
那绝对不是正常的游泳或洗澡的动作——没有水花,没有声响,
就像是水下有什么东西把这个身影托举上来一样。"小马..."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扯了扯还在专注看电影的伙伴。"干啥?正精彩呢!"小马不耐烦地回答,眼睛还盯着屏幕。
"河...河里..."我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有人从河里上来了!
"小马这才不情愿地转过头,眯着眼朝河边望去:"哪有人?黑灯瞎火的你看花眼了吧?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别自己吓自己,肯定是树影或者什么。"当我再次望向河边时,
那个身影确实不见了。河岸上空空如也,只有芦苇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我长舒一口气,
也许真的是我眼花了?可能是电影屏幕的光线造成的错觉吧。我试图集中注意力回到电影上,
但那种不安感却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场院里的欢笑声此刻显得那么遥远,
仿佛隔着一层透明的薄膜。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从黑暗的河边盯着我们,
盯着这片热闹的人群。第三章 恐怖的真容内心的不安驱使我再次在人群中搜索。
我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一张张被屏幕光影照得明暗不定的脸——有熟悉的邻居,
有外村来看电影的亲戚,还有几个我不太认识的面孔。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我的目光定格在了前排靠右的位置。同村的廖俊坐在那里,他是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
比我大四五岁,已经不上学了,帮着家里干农活。此刻他正被电影情节逗得开怀大笑,
身体不自觉地向后仰靠。这一仰,暴露了他身后那个原本被遮挡的身影。
那是一个浑身湿透的人。头发紧贴着头皮,水珠不断从发梢滴落,
在月光和屏幕反光下闪着诡异的光。深色的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
脚下已经积聚了一小滩水渍。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周围的人都专注地看着电影,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异常湿漉漉的存在。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呼吸变得急促。我想喊,
却发不出声音;想指给小马看,手臂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就在这时,
电影画面突然亮起——是地雷爆炸的火光。这一瞬间的强光,
清晰地照亮了那个湿漉身影的脸。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那是一张我永生难忘的脸。
皮肤是那种在水中浸泡过久的死灰色,浮肿得像是发酵过度的面团。
两只眼睛像死鱼一样恐怖地凸出眼眶,空洞无神。
最可怕的是左脸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孔,像是被什么蛀空了,
浮肿的肌肉随着呼吸如果那算呼吸的话微微颤动。那不是活人的脸。绝对不可能。
"啊——!"极致的恐惧终于冲破了我的喉咙,我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连人带板凳向后翻倒在地上。后脑勺重重撞在泥地上,疼痛让我瞬间眼前发黑。巧合的是,
电影里正好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那颗最大的地雷炸响了。
我的尖叫被完美地掩盖在了电影音效中。"叶子你怎么了?
"小马和其他附近的人被我的动静吓了一跳。看到我四仰八叉地摔在地上,他们愣了片刻,
随即爆发出笑声。"看个《地雷战》也能吓成这样?叶凡你也太怂了!
"隔壁家的二胖指着我说,引来更多哄笑。小马一边笑一边把我拉起来:"没事吧你?
是不是做噩梦了?"我浑身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死死抓住小马的手臂,牙齿打颤,
语无伦次地指着廖俊的方向:"鬼...有鬼!廖俊后面...水...水鬼!
"小马将信将疑地望过去,但那个位置现在只有廖俊和空荡荡的板凳。
地上的水渍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哪有什么鬼?你肯定是看花眼了。
"小马皱起眉头,"是不是这几天听鬼故事听多了?"周围的人也投来异样的目光,
有人小声嘀咕:"这孩子是不是中邪了?"屈辱、恐惧、无人相信的委屈交织在一起,
我再也无法在这个热闹的场院待下去。抓起我的小板凳,
我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跌跌撞撞地逃离了那里,背后是电影的对白和人们的欢笑声,
与我内心的惊恐形成了残酷的对比。第四章 河边的尸体那一夜我几乎没睡。每次闭上眼睛,
那张浮肿溃烂的脸就会在黑暗中浮现。我把头蒙在被子里,夏夜的闷热让我大汗淋漓,
但揭开被子又觉得阴风阵阵。
窗外的任何声响——风声、虫鸣、甚至远处隐约的狗吠——都让我心惊肉跳。
母亲起来小解时发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推门进来问我怎么了。我支支吾吾地说做噩梦了,
不敢告诉她实情。在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说见到鬼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