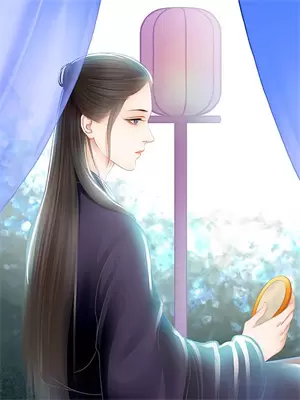1 天台坠落与冰冷解剖消毒水的味道像针一样扎进鼻子时,我还趴在天台的水泥地上,
后背传来撕裂般的疼。风卷着楼下住院部的灯光,在我眼前晃成一片模糊的光斑,
我能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响声,像破了的风箱。“你不该看那东西的。
”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影站在我旁边,声音冷得像太平间的瓷砖。我费力地抬头,
看见他袖口沾着的碘伏——下午我去普外科办公室找病历,就见过这个痕迹,
当时他正给一个病人换药。我想说话,可嘴里满是血沫。那枚U盘还在我胃里,
是我趁他转身时偷偷拿的,里面存着密密麻麻的表格,
标注着“供体编号”“受体信息”“费用明细”,还有几个被划掉的名字,
后面跟着“抢救无效”的字样。我才知道,这半年来医院里突然去世的几个病人,
根本不是意外。他蹲下来,手指按在我胸口,力气大得像要把我的骨头捏碎。“吐出来,
我让你少受点罪。”我死死咬着牙,把脸扭向一边。他笑了,
笑声里全是寒意:“那就别怪我了。”下一秒,我被他拽着衣领提起来,天旋地转间,
我看见楼下的花坛越来越近。风灌满了我的耳朵,最后听见的,是骨头撞在地面的脆响。
再有意识时,我飘在半空中,脚下是太平间的冷柜。我的身体躺在里面,脸色惨白,
胸口的衣服被血浸透,像一块深色的污渍。太平间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两个穿蓝色防护服的人走进来,手里提着银色的工具箱,轮子在地上滚过,
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在空荡的房间里特别清楚。“确定在他身上?”其中一个人问,
声音压得很低。“主任说肯定吞了,不然不会推他下来。”另一个人打开工具箱,
里面的手术刀闪着冷光,“赶紧找,别被人发现。”他们把我的身体从冷柜里抬出来,
放在旁边的推车上。我飘在他们头顶,看着手术刀划开我的皮肤,
鲜血顺着推车的缝隙滴在地上,发出“滴答”的声音。我的胃被切开,
他们的手指在里面翻找,动作粗鲁得像在翻垃圾桶。“没有啊。”其中一个人皱着眉,
额头上渗出汗,“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再找仔细点,主任说了,找不到我们都得完蛋!
”他们又划开我的胸腔,手术刀碰到肋骨时,发出“咯吱”的轻响。我的心脏被取出来,
放在不锈钢托盘里,他们捏着心室壁翻来覆去地看,连血管都没放过。接着是肝脏,
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在盘子里,像一堆血淋淋的石头。
我看着他们把我的内脏翻得乱七八糟,托盘里、推车上、地上,到处都是我的血和肉。最后,
他们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妈的,真没有,难道被他藏别的地方了?”“不可能,
他从办公室出来就被我们跟着,没机会藏。”其中一个人站起来,踢了踢我的身体,
“不管了,先把他塞回去,就说没找到,让主任再想办法。
”他们把我的内脏随便塞进我的胸腔,用针线胡乱缝了几针,就像缝一个破布娃娃。
然后把我的身体扔回冷柜,“哐当”一声关上柜门,提着工具箱匆匆走了。
太平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冷柜的压缩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我试着伸出手,
碰到了旁边的推车,金属架突然“哐当”一声撞向冷柜,震得上面的标签纸飘落在地。
标签上写着我的名字,还有“高处坠落,多器官破裂,抢救无效”的字样,落款医生的名字,
正是推我下楼的那个普外科主任。原来我能碰东西。我飘到冷柜前,
看着里面自己残破的身体,胃里的U盘早就随着他们的翻找,
掉进了旁边的医疗垃圾桶——刚才我看见其中一个人的手套勾到了U盘,掉在垃圾桶里,
他们没发现。我要报仇。这个念头像火一样烧起来,我飘出太平间,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
消毒水的味道更浓了,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
2 第一个目标——麻醉科李医生走廊尽头的值班室亮着灯,里面传来翻东西的声音。
我飘过去,透过门缝看见麻醉科的李医生正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瓶杜冷丁,
标签已经被撕掉了。我记得他,上周有个老人做阑尾炎手术,本来很简单的手术,
却在麻醉后再也没醒过来。当时医院说老人有心脏病,是意外,但我在U盘里看到,
老人的名字后面写着“供体合格”,而李医生的名字,就在“麻醉记录”那一栏。
他拧开杜冷丁的瓶盖,倒了一点在注射器里,正要往胳膊上扎。我飘进值班室,
猛地撞向他的手肘,注射器里的药液“哗啦”一声洒在地上,在瓷砖上留下一道湿痕。“谁?
”他吓了一跳,猛地回头,看见空无一人的房间,脸色有点发白,“别装神弄鬼的!
”他弯腰去擦地上的药液,我趁机掀翻了桌上的水杯。水顺着桌面流进插座,“滋啦”一声,
电流火花溅出来,落在他手背上。他“啊”地叫了一声,手背上立刻起了个水泡,他甩着手,
往后退了一步,撞倒了身后的药柜。药瓶“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有几瓶摔碎了,
药液混在一起,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其中一瓶氯化钾滚到他脚边,标签朝上,
上面的“氯化钾注射液”几个字特别显眼。他盯着那瓶药,脸色突然变得惨白。
我记得U盘里的记录,上次那个老人,就是被他用过量氯化钾“意外”致死的,
对外说是心律失常。我绕着他飘了一圈,值班室的窗户突然自己打开,冷风灌进来,
吹得桌上的病历纸哗哗作响,最后停在那张伪造的死亡证明上——上面写着老人的名字,
还有李医生的签名。他伸手想去捂病历,我却缠住他的手腕。我的手没有温度,
像冰一样贴在他的皮肤上。他“啊”地叫了一声,像被烫到一样甩开手,踉跄着往后退,
撞在墙上。“有鬼!真的有鬼!”他大喊着,跌跌撞撞地跑出值班室,
走廊里传来他的脚步声,还有东西被撞倒的声音。我飘到窗边,看见他撞在护士站的推车上,
氧气瓶“咚”地砸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护士站的护士被惊醒,跑出来看情况。
李医生指着值班室的方向,声音发颤:“里面……里面有鬼,还碰我手,冷冰冰的!
”护士皱着眉,走进值班室看了看,出来时一脸疑惑:“什么都没有啊,
就地上有水和碎药瓶,你是不是太累出现幻觉了?”李医生盯着值班室的门,脸色惨白,
说不出话来。我飘在他身后,轻轻吹了口气,他打了个寒颤,突然蹲在地上,抱着头,
嘴里不断重复着:“我不是故意的……是主任逼我的……别找我……”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他的恐惧,会慢慢吞噬他。3 第二个目标——销毁证据的护士长第二天凌晨,
医院里静悄悄的,只有清洁工推着车在走廊里打扫。我飘到护士站,
看见护士长正坐在电脑前,手里拿着鼠标,屏幕上是医院的文件管理系统。
她是帮凶里最细心的一个。我偷U盘的那天,就是她发现我在翻主任的抽屉,
偷偷告诉了主任,才让我没机会把U盘带出去,只能吞进肚子里。而且U盘里的很多记录,
都是她帮忙修改的,比如把“器官移植”改成“常规手术”,把“供体”改成“病人”。
她盯着电脑屏幕,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似乎在删除什么文件。我飘到她身后,
看见屏幕上是我的病历,她正在把“高处坠落”改成“意外摔倒”,还想删掉我住院的记录。
我轻轻碰了碰鼠标,鼠标突然往旁边移了一下,点到了“保存”按钮旁边的“另存为”。
她皱了皱眉,骂了句“什么破鼠标”,伸手去调鼠标,我又碰了碰键盘,“回车”键被按下,
文件突然保存到了医院的公共文件夹里,所有医生和护士都能看到。她脸色一变,
赶紧去删文件,可不管她怎么点“删除”,文件都删不掉,反而弹出一个窗口,
上面写着“文件正在被使用,无法删除”。她急得额头冒汗,拿起旁边的电话,
想打给电脑维修部,我却吹了口气,电话听筒“啪”地掉在桌上,线也被扯断了。
“搞什么啊!”她烦躁地站起来,想去隔壁办公室找电脑,刚走到门口,
我把护士站的抽屉打开了。抽屉里放着一叠文件,都是她帮忙伪造的死亡证明,
还有几张银行卡——U盘里写着,每次器官交易,她都能拿到一笔钱,就存在这些银行卡里。
她看见抽屉开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赶紧走过去想关上。我却把抽屉里的文件全吹了出来,
散落在地上。路过的清洁工看见了,走过来问:“护士长,你怎么把文件扔地上了?
”她赶紧蹲下来捡文件,手忙脚乱的,把几张银行卡也带了出来,掉在地上。
清洁工弯腰去捡,她赶紧抢过来,塞进兜里,脸色通红:“没……没什么,不小心弄掉的。
”清洁工疑惑地看了她一眼,推着车走了。她蹲在地上,看着散落的死亡证明,
突然哭了起来,嘴里念叨着:“我只是想多赚点钱……我不想死啊……”我飘到她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