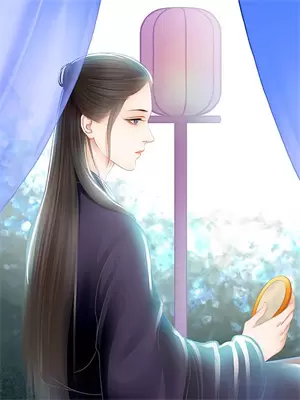序章:跑马灯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眼,我绝不会选择躲进这片吞噬一切的黑暗。他们说,
人在濒死前,一生会像走马灯般闪过。我的走马灯,
最终定格在那扇缓缓合上的门缝外——那张和我挚友一模一样的脸上,
那双我从未读懂过的、冰冷的眼睛。原来,从一开始,和我玩这场致命躲猫猫的,
就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别丢下我了……”这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句无声的哀求。
第一章:风,起于青萍之末在我有限的、二十几年的人生认知里,“告别”应该是盛大的,
至少是清晰的。它应该发生在洒满阳光的机场闸口,
伴随着用力的拥抱和“保持联系”的承诺;或者是在散伙饭的餐桌上,混着酒气和眼泪,
定格在合照里一张张通红的脸。我从没想过,我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告别,
会开始得那么无声无息。它伪装成一次寻常的日落,一句心不在焉的“再见”,
甚至是一个……我并未察觉的替身。时间,得拨回那个一切都还来得及的下午。
手机屏幕还停留在我发的那条朋友圈页面上——一张P过的裸辞信截图,
配文是:“江湖路远,本侠女先去躲个清静!”底下很热闹。几个高中好友在插科打诨,
说我任性又潇洒。简宁,我最好的闺蜜,回了个夸张的“牛逼”表情包。我笑着锁上屏幕,
看向对面小口啜饮着拿铁的汤怡心,哦不,在英国时我们都叫她汤瑄。“决定了?
”她抬起眼,笑容温婉,带着一点点的担忧,“真就一点都不留恋?”“留恋什么?
留恋无休止的改稿,还是留恋上司那张更年期的脸?”我舒展了一下身体,
像只终于挣脱了笼子的猫,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瑄宝,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我得去撒点野了。”她就是我的“轨道”,按部就班,温柔娴静。
而我是那匹一心只想冲向“旷野”的马。我们如此不同,却又如此亲密。
是在伦敦阴冷的雨天里,唯一会给我送伞的人;也是在我用蹩脚英语跟人据理力争时,
会默默站在我身后的人。“好好好,说不过你。”她无奈地笑,
“那你接下来打算去哪片‘旷野’?”“眼前就有一片。”我压低声音,
带着点分享秘密的兴奋,把手机推到她面前。屏幕上是一个模糊的群聊界面,
隐约能看到“城市躲猫猫”、“高额奖金”、“刺激”几个关键词。“又玩这个?
”她皱了皱眉,“那种废弃的地方,不安全吧。”“放心啦,都是同好,
而且这次场地在湿地公园旁边,听说是个废弃的别墅区,范围大,藏身点多,奖金这个数!
”我比划了一下,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惊诧,“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就这周末。
”她迟疑着,手指摩挲着温热的杯壁:“我……我好像有点感冒了,那天不知道能不能行。
”一丝失望刚冒头,就被我按了回去。“没事儿,到时候看嘛。你要是来不了,
我就自己去探险!”我说得轻松,心里却打定主意,就算拖也要把她拖去。这种刺激的时刻,
怎么能少了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我们又在咖啡馆坐了一会儿,聊着无关紧要的琐事。
窗外的阳光一点点变得柔和,给她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离开时,
我们在门口分手。她朝地铁站走去,我看着她略显单薄的背影汇入人流,像一滴水融入大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真正的汤怡心。如果我知道的话,那天下午,
我一定会用力地、再用力地抱一抱她。还有我的外婆……风,就是从那个看似平静的午后,
开始悄然转向的。它穿过城市的楼宇缝隙,掠过湿地公园荒芜的草丛,最终,
在那栋山腰别墅虚掩的木门前,凝滞成一道冰冷的、带着死亡气息的墙。而我,
这只自以为奔向自由的鸟,正一无所知地,朝着那张早已张开的网,奋力飞去。
第二章:影子的邀请日子在焦灼的期待与一丝不安中,滑向了周末。
我给汤怡心发信息确认状态,回复总是慢半拍,字里行间透着挥之不去的虚弱。
“头还有点晕。”“我再休息一下,应该没问题。”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语气过于平淡,
少了点她特有的温度。也许是病的,我对自己说,
心里那点因为强拉病号参赛而产生的愧疚感,又加深了一层。周五傍晚,天色阴沉。
到了湿地公园,我检查着背包里的装备:强光手电、能量棒、一瓶水,
还有一小卷深色遮挡布——这是“躲猫猫”高级玩家的必备道具,
能在废墟中创造出完美的视觉死角。手机电量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三十几,我啧了一声,
想起由于裸辞,在家里竟忘了充电,不过游戏通常也就2个来小时,不耽搁,
我就没拿充电宝,选择了轻装上阵。我们约在湿地公园外围。我到时,
那个穿着米色风衣、戴着帽子和口罩的身影已经在了。她把自己裹得很严实,
几乎融入了暮色里。“瑄宝!”我小跑过去,语气里带着歉意和兴奋,“实在不舒服的话,
我们现在就打道回府。”她摇了摇头,帽檐下的视线扫过我,很快移开。“不用。
”声音隔着口罩,沙哑得厉害,“来都来了。”“够意思!”我松了口气,
随即兴致勃勃地拍了拍背包,“放心,跟着我,保证让你躺赢!我带了‘秘密武器’。
”她只是微微颔首,没有接话。一种微妙的距离感横亘在我们之间。往常,
她至少会回我一个无奈又纵容的微笑。前往废弃别墅区的路上,她异常沉默,
跟在我身后半步,像一道安静的影子。我几次试图活跃气氛,谈论策略,
她都只是用简单的“嗯”、“好”回应。病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吗?我心底泛起怜惜,
不再叨扰她,将注意力转向了前方那片在暮色中轮廓狰狞的建筑群。穿过栅栏缺口,
荒草的气息混杂着潮湿的土腥味扑面而来。那栋主别墅像一头沉默的巨兽,
黑洞洞的窗口是它盲了的眼。庭院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影,
组织者压低声音强调着规则:“……利用环境和自己带的道具隐藏,
范围是这栋别墅及周边五十米,‘鬼’半小时后出动……安全第一!”参加比赛的人群里,
有个男子好像英国留学时同校不同班的凯文,本来想要打招呼,但随着主办方说开始,
只好作罢。光线昏暗,人影绰绰,一种混杂着刺激与紧张的电流在空气中窜动。“走了!
”我碰了一下“怡心”的手臂,感觉到她细微的躲闪。没时间细想,我带着她,
随着人流涌入别墅内部。空旷、破败、灰尘弥漫。手电光柱像探照灯,
扫过断壁残垣和废弃的家具。“我们去楼下!”我当机立断,地下室通常更复杂,
藏身点更多。她跟在我身后,走下通往地下室的狭窄楼梯,脚步很轻。下面的空气更冷,
霉味更重,还夹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陈旧气息。空间里堆满了建筑垃圾和破损的家具,
形成许多天然的遮蔽物。我快速搜寻着,光柱掠过一堆石膏板,一个空荡荡的旧书柜,最终,
定格在最里面角落——那里有一扇厚重的、带有雕花装饰的旧木门,门虚掩着,
里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我快步上前,侧身往里照了照。空间不大,
像是以前的衣帽间或者储藏室,里面空荡荡,正好能容一人藏身。“找到了!
”我压抑着兴奋,回头对身后的“影子”低语,心脏因找到绝佳位置而雀跃,“完美!
就这里!”我快速解释我的策略,眼睛因兴奋而发亮:“你就在地下室找个地方藏好,
别太隐蔽。这就是‘卖一藏一’!‘鬼’找到你,大概率就觉得完事了,
不会想到最里面的密室还藏着一个!这样我就能赢到最后!”这是我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用她做诱饵,确保我的绝对胜利。她站在我身后,沉默地看着那扇门,又看看我,
昏暗的光线下,眼神难以分辨。“快,你自己也找地方!”我催促道,
一边从背包里拿出那卷深色布,准备钻进那个小房间做些简单的伪装,
让它看起来更像一堆杂物。在我转身踏入那片黑暗前,我像往常一样,
对她露出了一个充满信任和鼓励的笑容,用我们之间最习惯的依赖语气说:“躲猫猫,
可千万别丢下我了哦!”然后,我侧身,挤进了那片散发着陈腐气味的、绝对的黑暗之中。
第三章:打不开的门身后的木门合拢,将外面手电筒的微弱余光彻底隔绝。
世界骤然被压缩成一片绝对的黑暗,以及一种令人耳膜发胀的死寂。我深吸一口气,
那股浓重的、陈腐的灰尘味直冲肺叶。我摸索着,从背包里掏出那卷深色遮挡布,
借着从门底极细微缝隙透入的一丝几乎可以忽略的光,开始小心翼翼地布置这个狭小的空间,
试图将它伪装成一堆无关紧要的杂物。就在我即将完成伪装,
准备靠墙坐下等待胜利时——门外,毫无征兆地传来一声清晰、短促、令人牙酸的摩擦声。
“噌——咔!”那声音异常刺耳,绝不是脚步声,更像是……某种粗糙沉重的物体,
被用力拖拽,然后死死抵在门板上发出的、充满决绝意味的声响!什么声音?!
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浑身的血液仿佛倒流。“……瑄宝?”我试探着,
声音因突如其来的惊悸而带着一丝颤抖。门外,是比之前更甚的、令人心慌的死寂。
一种冰冷的预感,像藤蔓一样迅速缠绕住我的心脏。我猛地扑到门前,
用肩膀抵住厚重的门板,用力向外推——门,纹丝不动。不是卡住的感觉,
而是被某种巨大的力量从外面抵死的感觉!恐慌如同冰水,瞬间淹没头顶。“汤怡心!开门!
”我改用拳头砸向门板,声音因恐惧而拔高,在狭小的空间里发出沉闷的回响,“别闹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开门!!”门外,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我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屏幕亮起的光芒刺得我眯了下眼。屏幕顶端——无服务的标识像一个冰冷的嘲笑。紧接着,
我的目光死死钉在右上角——那代表电量的图标,竟是刺目的红色!10%!
绝望感开始像潮水般上涌。“怡心……怡心可能是暂时离开了一下……或者,
她也被‘鬼’抓住了,没办法回来……”我蜷缩在门后,紧紧攥着发烫的手机,
徒劳地为自己找着借口,也为门外的“她”找着理由。我甚至开始担心起她的安危来。
我竖起耳朵,拼命捕捉门外的任何一丝声响。只有一片虚无的死寂。
和我自己越来越粗重、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空气,似乎正在变得粘稠,
每一次吸气都愈发费力。手机屏幕的光芒,开始变得不稳定。
电量不足5%……提示框无情地弹了出来。不!我手忙脚乱地将屏幕亮度调到最低,
徒劳地想要延长这一点可怜的光明。这微弱的光,是我对抗无边黑暗和恐惧的唯一武器。
屏幕剧烈地闪烁了几下,最后顽强地亮起,映亮了我满是冷汗的脸。然后。屏幕,
在我眼前猛地一黑。电量0%最后的光源,熄灭了。
最后一点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微弱可能性,连同我为“怡心”找的所有借口和残存的希望,
一起被这浓得化不开的黑暗与死寂,彻底地、无声地……吞没了。
第四章:窒息袭来绝对的黑暗。不是闭上眼睛的那种黑,而是某种具有重量和质感的实体,
压迫着眼球,堵塞着耳膜,甚至试图从毛孔钻入,占据整个躯体。
手机屏幕最后一丝光芒熄灭的瞬间,我仿佛听见了自己理智断裂的细微声响。
“呼……呼……”我自己的呼吸声,在这狭小、密闭的空间里,被放大了无数倍,
粗重得像破旧的风箱。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更浓重的灰尘和陈腐气味,它们不再仅仅是难闻,
更像是有生命的毒素,一点点麻痹着我的神经。我猛地想起我的背包!能量棒!水!
我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疯狂地在黑暗中摸索,将背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
手指急切地分辨着——强光手电筒已经没用了、那卷深色布……没了。能量棒和水呢?
记忆像闪电般劈开混乱的脑海——在地下室布置伪装前,我为了减轻负担,
把能量棒和水瓶随手放在了那堆石膏板旁边!一瞬间,
巨大的悔恨和更深的绝望如同两只冰冷的手,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我为什么要拿出来?
为什么!不甘心驱使着我,我再次用身体撞向那扇门,肩膀和手臂的疼痛早已麻木,
只有沉闷的撞击声回应着我,证明着这扇门的坚固和无情。喉咙干得发疼,像有砂纸在摩擦,
连呼喊都变得嘶哑微弱。“……开……门……”声音出口,微弱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清。
我徒劳地摸索着,拾起地上的强光手电筒,疯狂地按着开关。
“咔哒……咔哒……”开关徒劳地响着。突然!“啪——”一道刺眼的白光猛地亮起,
如同濒死前的回光返照,瞬间驱散了黑暗,将狭小空间里每一寸绝望都照得清晰无比!
光柱颤抖着扫过斑驳的墙壁,扫过我因恐惧和缺氧而扭曲的脸,
最后定格在那扇厚重的、决定我生死的门上。但这光明只持续了短短几秒。
“滋啦……”光线猛地闪烁,急剧变暗,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喉咙。
“不……不要……”我徒劳地拍打着它。手电筒最后挣扎着发出一点昏黄、微弱的光晕,
随即——彻底熄灭。最后一点人造的光明,消失了。黑暗,
比之前更加浓稠、更具吞噬性地涌了上来。“……嗬……嗬……”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
胸口像是被压上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每一次起伏都需要耗费巨大的力气。头晕目眩,
视线即使在黑暗中也开始出现模糊的斑点,像是坏掉的电视机屏幕。我知道,这不是疲惫。
是空气。这里的空气正在被我消耗殆尽。每一次呼气,吐出二氧化碳;每一次吸气,
吸入的氧气却越来越少。我开始感到恶心,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得像要炸开。
意识像一艘进水的小船,开始逐渐下沉。纷乱的念头和清晰的记忆碎片不受控制地涌现。
底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难道……你真的……那个被我死死压住的、最恐怖的猜想,
终于随着意识的模糊,浮出了水面。
不……不可能……剧烈的头痛和窒息感淹没了这最后的挣扎。我支撑不住身体,
沿着冰冷的墙壁滑倒在地。蜷缩在门后,像一只被遗弃的小兽。力气正从四肢百骸迅速抽离,
连抬起一根手指都变得无比艰难。视野完全被黑暗占据,连那些模糊的斑点都消失了。
呼吸变得极其微弱,间隔越来越长。最后一丝清醒的意识,像风中残烛,摇曳着。
好……冷……黑暗……彻底的…………外婆……小宁……对……不……起……意识的弦,
终于彻底崩断。一切感知,归于虚无。第五章:黑暗中的走马灯意识,
像暴露在空气中的胶片,在彻底曝白与断续显影间,进行着漫长而痛苦的拉锯。
第一次从虚无中挣扎出来,是被一种超越干渴的、内脏焚烧般的剧痛拽回的。
喉咙和鼻腔里塞满了滚烫的玻璃碴,每一次微弱的呼吸都带着血腥气的灼痛。
身体里的水分似乎已被彻底榨干,皮肤紧贴着骨头,像一件不合身的、皱巴巴的衣物。
“水……”声音出口,是破碎的气音,连自己都听不真切。绝对的黑暗,剥夺了时间,
放大了感官,却又混淆了一切。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一小时?一天?还是仅仅几分钟?
缺氧像无形的潮水,一次次漫过头顶,带来阵阵眩晕和恶心。意识在下沉,
沉向一个更黑、更冷的深渊。而就在这沉沦的边缘,一些画面,却带着不合时宜的清晰,
猛地浮现在这片意识的废墟上。走马灯,开始了。最先闪现的,不是光,是气味。
是老房子厨房里,外婆熬的玉米粥那甜丝丝、暖融融的香气。父母离婚时我还太小,
他们各自组成新家庭后,我就是跟着外婆在这味道里长大的。那味道是“家”唯一的注脚。
然后,是画面。高中操场,烈日灼人。 我和简宁在红色跑道上追逐,她累得弯下腰,
气喘吁吁地指着我:“莫岚……你跑起来……真像一阵风,谁也抓不住!” 我回头,
得意地大笑,阳光洒了满身,以为青春和自由永无止境。切换。英国,偌大的阶梯教室。
空气凝滞。讲台上,那位享有盛誉的教授,用带着怜悯的伦敦腔调说:“……不得不承认,
部分中国学生在学术上表现‘优异’,或许与他们……嗯,
在某些方面的‘灵活性’有关……” 教室里响起几声尴尬的、附和的低笑。
我看到身边几个中国同学低下了头。一股热血猛地冲上头顶。我“唰”地站了起来,
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所有目光聚焦过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用苦练了无数个夜晚的、流利而精准的英语,清晰地、一字一句地反驳,条理分明,
引据经典,不卑不亢。那一刻,我看到教授眼中闪过的错愕,也看到许多原本低垂的头,
重新抬了起来。切换。伦敦,阴冷潮湿的后巷,傍晚。 垃圾桶散发出馊味。
几个高大的印裔学生将汤瑄那时她还不叫汤怡心堵在墙角,充满恶意的笑声,
夹杂着带有浓重口音的、侮辱性的词语。汤瑄缩在那里,脸色惨白,
像一只被暴雨打湿、瑟瑟发抖的麻雀,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是我,
像一团被点燃的火焰冲了进去,用同样强硬流利的英语厉声呵斥,毫不犹豫地张开手臂,
将她死死护在身后,直面那些不怀好意的、挑衅的目光。那一刻,我的背影,
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她在异国他乡唯一的光。切换。图书馆通明的灯火下。
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时,离我毕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年前,父亲刚因意外去世。
接连的噩耗几乎将我击垮。但我不能倒下。外婆只有我了。我像疯了一样,
把自己埋进堆积如山的书籍和文献里,用高强度的学习麻痹自己。一个接一个的Essay,
一场接一场的Presentation (Pre),我咬着牙,
几乎是榨干自己最后一丝精力,拼命地把GPA学分修到了毕业要求。我提前结束了学业,
用最快的时间飞回了国。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是我心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切换。
回国后的生活。 和简宁,和那几个高中挚友,我们依然亲密,但生活轨迹已然不同。
我们偶尔见面,更多的时候是做网友,在微信里分享搞笑的短视频,
吐槽各自工作上遇到的奇葩,约着下次一起吃饭旅行,有时甚至几个月才联系一次。
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都可以来日方长。最后,
定格在一张温和却带着一丝愁容的脸上。 是汤怡心。我们坐在“半糖”咖啡馆里,
阳光很好。她搅拌着咖啡,忽然轻声说:“岚岚,小染她……好像有点羡慕我们的生活。
”我当时正沉浸在某个搞笑的段子里,闻言头也没抬,随口笑着回应:“是吗?
那下次带她一起出来玩呀?” 隔了一会儿,没有听到预想中的附和,我才抬起头。
只见怡心只是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无奈的,甚至可以说是……欲言又止的笑容。
那个笑容……那个无奈的、欲言又止的笑容……当时只觉得是她对妹妹的宠溺和些许无奈,
未曾深究。现在,在这濒死的、绝对寂静的黑暗里,那个笑容被无限放大,
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可怕。难道……?一个冰冷、模糊却带着尖锐棱角的猜想,
如同水下潜伏已久的怪物,终于冲破意识的冰层,猛地攥住了我最后的心跳。
不是怡心……是……小染……?门外的……从一开始就是……汤染?!
所以那个笑容……是怡心早已察觉却无法言说的……预警吗?我想嘶喊,想质问,
想用尽最后力气去撞击那扇门。但,太晚了。身体像被掏空的壳,
连抬起眼皮的力气都已消失。意识如同断线的风筝,向着无尽的黑暗深处飘去。
最后一丝光亮,从思维的尽头熄灭。一切,重归于…………死寂。终章:无解的谜题身体,
像一块被彻底耗尽的电池,再也无法向任何一块肌肉发送任何有效的指令。
冰冷的地面不再传来坚硬的触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虚浮的、仿佛悬浮在虚空中的失重感。
连那折磨人的、烧灼般的内脏疼痛,也渐渐淡去,
变成一种遥远的、与“我”无关的背景噪音。听觉,是最后消失的吗?或许吧。
在一片粘稠的、包裹着意识的死寂中,我似乎……听到了什么。是……光的声音?
荒谬的念头浮现的瞬间,我仿佛真的“看”到了——就在我身后,
那扇将我囚禁于此、坚不可摧的门扉底部,一道极其细微、却无比清晰的光束,如同利剑般,
骤然刺破了这永恒的黑暗!那么亮,那么真实,带着某种……希望的暖意。是有人来了吗?
是怡心……回来了吗?是她终于找到人,来救我了吗?!巨大的、几乎是本能的求生欲,
像微弱的火星,试图点燃我早已冰冷的血液。我想起身,想回头,
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触碰那道光,去拍打门板,去发出一点声音——动啊!快动啊!
我在心里无声地嘶吼,命令着这具已经不属于我的躯壳。可是,没有用。
身体如同被浇筑在水泥里,连抬起一根手指,转动一下眼球,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我只能维持着蜷缩的姿势,背对着那道光,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凝固的雕像。那道光,
静静地停留在那里,带着无声的嘲弄。它照亮不了我的生路,只是清晰地映照出我的末路。
最后一点挣扎的力气,也随着这徒劳的尝试,彻底消散了。意识,像退潮的海水,
迅速从四肢百骸抽离,缩回到大脑最核心、最柔软的一隅。
纷乱的念头和画面开始不受控制地翻涌,又迅速平息。最后定格下来的,不是父母模糊的脸,
不是外婆哀伤的眼,不是伦敦的雨,也不是教授的课堂。是简宁。是那个在阳光下,
指着我说“你像风一样抓不住”的简宁。
小宁……一个极其微弱的、带着无尽遗憾和依恋的念头,如同叹息般,
在我彻底沉寂的意识中,
次躲猫猫啊……这次……我一定不藏那么久了……我一定……让你一下子就找到我……念头,
断了。那束想象中的光,熄灭了。最后一点听觉,消失了。
线、所有的思绪、所有的爱与恨、疑惑与不甘……都归于……永恒的、无边无际的……寂静。
至死,我都没能解开,“挚友汤怡心”为何要背叛我、将我遗弃在这黑暗中的……无解谜题。
全文完作者的话番外篇说明:写完上一篇故事《致命躲猫猫:是谁关上了门?》,
意犹未尽,于是有了莫岚视角的这篇故事。写完之后,又想到出现过的人物,
想他们的于是写几篇番外吧。 也请读完这篇的朋友,也支持,我上一个故事,诚挚感谢!
邬铭渊、汤怡心、汤染、丁工 高文师 登场于《致命躲猫猫:是谁关上了门?
》番外一:邬铭渊 —— 无法剪辑的素材他们都说,我的镜头有种天生的冷漠。
我不否认。透过取景器看到的世界,被框成一幅构图精准的画面,光线、色彩、线条,
一切都可以被量化,被调整。我迷恋这种掌控感。城市的喧嚣、人群的悲欢,
一旦被收录进存储卡,就都成了我指尖可以随意剪切、拼接、调色的"素材"。
直到我拍下了那条改变一切的Vlog。现在回想起来,那片废弃别墅区,
确实是个出"大片"的好地方。荒凉、破败,带着被时代遗忘的颓唐美学。
我的频道需要这种刺激。那天,我和团队像往常一样,带着设备,准备去"征服"这片废墟。
然后,是那股味道。不是普通的霉味,是一种更深层、更令人作呕的,
属于生命彻底腐败后的甜腻与腥臭。它像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住了你的胃。再然后,
是那个地下室。手电光柱在灰尘中徒劳地挥舞,最终定格在那扇虚掩的、厚重的木门上。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推开那扇门时,指尖传来的冰冷触感,
和门轴发出的、如同垂死者叹息般的"吱呀"声。后面的画面,
成了我无法删除的、永久的"原始素材"。虽然成片里只有摇晃的镜头和同伴变调的惊呼,
但我的大脑,我的眼睛,替我记录下了全部。那些被剪辑掉的、最直接的恐怖,
成了我私密的、无法摆脱的梦魇。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直视任何肉类,
无法进入任何密闭空间,那味道和画面,总会在不经意间闪回。视频发布后,
我收到了一个叫简宁的女孩的私信。她说自己是逝者的朋友,想了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