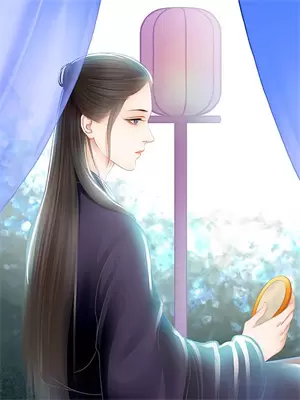七月十五,晌午的日头明晃晃悬在头顶,毒得很,晒得人皮肤发烫。
长途巴士把我扔在镇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逃似的开走了,卷起一阵掺着黄土的热风。
我拖着行李箱,轮子在坑洼的石板路上磕磕绊绊,发出单调的“咕噜”声,敲打着死寂。
镇子静得吓人,往常这时候,该有狗叫,有小孩哭闹,有麻将牌摔在桌面的脆响,可现在,
只有头顶蝉鸣,嘶哑得像是用砂纸在刮喉咙。路两边的门窗大多紧闭着,偶尔有几扇虚掩的,
后面似乎有眼睛在窥探,可我望过去,只有一片片浓得化不开的阴影。不对劲。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了,越收越紧。我说不上来,只是一种本能的不安,像冰冷的蛇,
顺着脊椎往上爬。越往家走,那寒意越重。直到路过镇中心那口废弃的老井,
我看见井台边站着隔壁的王婶。她直挺挺地立在那里,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
手里还拎着个菜篮子。目光下意识地往她脚下一扫——我猛地顿住脚步,
浑身血液仿佛瞬间冻住。没有。青石板路面被阳光照得白花花一片,
清晰得连石头的纹路都看得清。王婶的脚就在那里,布鞋,裤腿,可是……她脚下,
空空如也。本该蜷缩在她脚边的那团黑影,不见了。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头顶。
我僵硬地转动脖子,看向街对面另一个摇着蒲扇的老头。同样,
阳光毫无阻碍地落在他坐着的小马扎周围,将他枯瘦的身形勾勒出来,唯独,没有影子。
没有,全都没有!视线所及,每一个在户外活动的人,男女老少,他们的脚下,
都只有光秃秃的地面。阳光灿烂得近乎残忍,将这些缺失映照得无比清晰,无比诡异。
我几乎是跑起来的,行李箱的轮子发出更加急促而凌乱的噪音,撞在石板上,哐哐作响。
胸口堵得厉害,几乎要喘不上气。老家那扇熟悉的黑漆木门敞开着,像一张沉默的嘴。
院子里挤满了人,大多是镇上的老街坊,他们穿着素色的衣服,三五成群地站着,
低语声嗡嗡的,像一群扰人的苍蝇。可我一踏进门槛,所有的声音霎时停了。
几十道目光齐刷刷地钉在我身上。那些目光麻木,空洞,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审视。
我强迫自己不去看他们的脚,心脏却在胸腔里疯狂擂鼓。灵堂设在堂屋,
奶奶的遗照摆在正中央,那是她去年生日时拍的,穿着簇新的藏蓝色褂子,笑得一脸慈祥。
香烛的味道浓郁得呛人,混合着老旧家具散发出的霉味,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气息。
父亲就跪在灵前,佝偻着背,穿着宽大的麻布孝服。他听到动静,缓缓转过头来看我。
几天不见,他像是老了十岁,眼窝深陷,脸色蜡黄。“爸……”我哑着嗓子叫了一声。
他没有应,只是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有悲痛,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焦灼。
他猛地站起身,踉跄着朝我冲过来,干燥发烫的手像铁钳一样攥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
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走!”他从牙缝里挤出声音,喉咙里带着风箱般的杂音,
“听着,天黑前……天黑前必须离开这!一刻也别停!”他浑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恐惧几乎要溢出来。“为什么?奶奶她……”我试图挣脱,却被抓得更紧。
“你奶奶就是不肯走才……才这样的!”他低吼着,声音嘶哑扭曲,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走!现在就走!别回……”话还没说完。他的声音戛然而止。眼睛猛地凸出,
整张脸瞬间扭曲成一种极度惊恐的形状。他的嘴巴徒劳地张合着,却发不出任何一个音节,
像是被一只完全看不见的手死死捂住了口鼻,另一股无形的巨力勒住了他的身体,
猛地将他往后拖拽!“爸!”我惊骇欲绝,下意识地想抓住他,
可指尖只擦过他粗糙的孝服布料。他双脚离地,身体以一种极其不自然的姿势,
被飞快地拖向堂屋后方那深不见底的黑暗里,速度快得只留下一道残影。
周围那些麻木站立的吊唁客,对此毫无反应,连眼神都没有波动一下,依旧静静地站着,
像一具具立在阳光下的苍白纸人。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跑!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字。
我丢开行李箱,转身就往外冲,撞开几个挡在门口的人影,他们的身体冰冷而僵硬。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只知道沿着来时的路,拼命地向镇口方向狂奔。耳边是呼啸的风声,
还有自己粗重如破锣的喘息和心跳。肺叶火辣辣地疼,腿软得像面条,可我不敢停。
那些没有影子的居民,有的站在门口,有的在街边窗前,他们静止不动,
只有眼珠随着我奔跑的身影缓缓转动。镇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就在眼前!希望刚刚燃起,
下一秒,一个穿着宽大黑色袍子的人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从槐树后转了出来,
恰好挡在了我的必经之路上。收势不及,我整个人重重地撞了上去。
预想中的碰撞感没有传来,更像是撞进了一团冰冷、粘稠的雾气里。
一股难以形容的腐朽气息直冲鼻腔,呛得我连连后退,差点摔倒。那黑袍人佝偻着背,
脸完全隐藏在宽大的兜帽阴影里,看不清面容,只能感觉到一种非人的苍老。他缓缓弯下腰,
枯瘦得像鸡爪的手,从地上拾起了一样东西。那是我刚才狂奔时,
从怀里掉出来的——奶奶的遗照。木质相框摔裂了一角玻璃。黑袍人用指尖摩挲着照片,
发出沙沙的轻响。他抬起头,兜帽下的阴影深处,似乎有两点微弱的光芒亮起,注视着我。
一个干涩、嘶哑,仿佛两块生锈铁片在摩擦的声音,慢悠悠地响了起来,
每个字都带着冰冷的寒意:“想活命……”他顿了顿,将那照片朝我稍稍递近。
“……就找回你奶奶藏起来的剪刀。”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他手中的照片上。照片上,
奶奶原本慈祥微笑着的脸,不知何时变了。她的嘴角垮了下来,一双眼睛里,
竟然缓缓渗出了两行粘稠的、暗红色的液体,正沿着相框的玻璃,蜿蜒而下。那是血泪。
黑袍人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像是讥讽又像是叹息的声音,宽大的黑袍一拂,像融入阴影般,
瞬间消失在老槐树后。我僵立在原地,浑身冰冷,动弹不得。只有那张流淌着血泪的遗照,
被随意地扔在我脚边的尘土里。奶奶浑浊的血泪,还在顺着碎裂的玻璃,慢慢往下淌。
而那把能救我命的剪刀,又在哪里?我死死盯着脚边的遗照。
奶奶的血泪在粗糙的黄土上洇开一小团暗色,像一只逐渐睁开的、不祥的眼睛。
冰冷的恐惧沿着尾椎骨一节节爬上来,几乎要冻结我的血液。可黑袍人的话,
还有父亲被拖走时那绝望的眼神,像两根烧红的针,刺穿了我的麻木。
找回剪刀……奶奶藏起来的剪刀……我猛地弯腰,
几乎是抢夺般从地上抓起那张变得粘腻湿冷的照片,看也不看地塞进裤兜。不能留在这里!
镇口是出不去了,那黑袍人就像个守门的恶鬼。现在,唯一可能找到线索的地方,
只剩下——奶奶的老宅。我转过身,重新面向那条贯穿小镇的死寂街道。阳光依旧炽烈,
将每一块青石板、每一片瓦砾都照得纤毫毕现,
也将在户外寥寥几个“人”脚下那诡异的空缺,映照得无比清晰。
他们依旧维持着固定的姿势,像橱窗里的假人,只有眼珠随着我的移动而缓缓转动,
带着一种非人的专注。我咬紧牙关,不再看他们,埋头朝着镇子深处,
那栋我从小长大的老宅冲去。这一次,我的脚步不再像刚才逃命时那样慌乱,
而是带着一种沉甸甸的、被逼到绝境的决绝。鞋底敲击石板的声音,
在过分安静的空气里显得格外突兀,仿佛在敲打着死亡的节拍。老宅的黑漆木门依旧敞开着,
像一张噬人的巨口。院子里,那些前来吊唁的“人”还站在原地,姿势几乎没变,
连低语的嗡嗡声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我冲进院子,他们齐刷刷地转过头,
几十张麻木的脸,几十双空洞的眼睛,无声地聚焦在我身上。我无视了他们,径直冲向堂屋。
灵堂里,香烛快要燃尽了,烛火摇曳,将熄未熄,投下大片晃动不安的阴影。
供桌上奶奶的遗照不见了,空出一块,只留下一个相框形状的浅浅印痕。
父亲刚才跪着的地方,只剩下两个浅浅的膝盖凹痕,
以及……几道凌乱的、仿佛被强行拖拽留下的刮擦印记,一直延伸向通往后院的黑暗门廊。
我的心狠狠一抽。后院……奶奶生前最后几年,就住在后院那间小小的偏房里。
她说那里清静,能晒到太阳。我深吸一口气,
那混合着香烛、霉味和某种若有若无腐朽气息的空气呛得我喉咙发痒。我迈过门槛,
踏入了通往后院的走廊。光线瞬间暗了下来。前院灼热的阳光被隔绝在外,走廊里阴冷潮湿,
墙壁上糊的旧报纸泛黄卷边,散发出陈年的气味。越往里走,温度越低,
裸露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奶奶的房门虚掩着,留着一道缝。我伸手,轻轻推开。
“吱呀——”老旧的木轴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房间不大,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
一张老式雕花木床,挂着洗得发白的蚊帐;一个掉了漆的衣柜;靠窗摆着一张梳妆台,
椭圆形的镜子模糊不清,映出我苍白失措的脸。哪里?剪刀会被藏在哪里?
奶奶是个极其念旧且谨慎的人,重要的东西,她绝不会放在明面上。我先是冲到梳妆台前,
胡乱拉开抽屉。里面只有一些零碎的针线、顶针、几枚古旧的铜钱,没有剪刀。
我又去翻衣柜,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散发着樟脑和老人身上特有的、淡淡的气味,
依旧一无所获。汗水顺着我的鬓角流下来,不是因为热,
而是源于一种时间流逝带来的巨大压力。天色,正在一点点暗下去。窗户纸外透进来的光,
已经带上了些许昏黄。必须在天黑前找到!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环顾这个我无比熟悉的房间。奶奶会把东西藏在哪里?床底?我蹲下身,撩开垂落的床单,
看向床下。只有几只落满灰尘的旧木箱。我费力地拖出一只,打开,
里面是些我小时候的玩具和旧课本。没有,都没有!绝望像冰冷的海水,开始淹没我的脚踝。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靠墙的那张老旧梳妆台。台面靠墙的位置,
放着一个黄铜的烛台,烛泪堆积,凝固成诡异的形状。烛台旁边,
是一个小小的、黑白色的相框,里面是爷爷奶奶年轻时的合影。
相框……我猛地想起裤兜里那张正在“流血”的遗照。鬼使神差地,我伸出手,
拿起了那个小相框。相框后面,紧贴着墙壁的地方,似乎有什么东西。我的心跳骤然加速。
我用指甲抠住相框边缘,小心翼翼地把它从紧贴的墙面上挪开。
就在相框原来位置下方的墙面上,有一个极其不起眼的、颜色略深的木质结节。我试探着,
用指尖按了下去。“咔哒。”一声极轻微的机括响动从梳妆台下方传来。我连忙蹲下,
看向梳妆台底部靠近墙根的位置。那里,一块原本严丝合缝的木板,
此刻微微弹开了一道缝隙!暗格!奶奶的梳妆台里,竟然有一个暗格!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几乎要撞破肋骨。我颤抖着伸出手指,抠住那道缝隙,用力一扳。
一块巴掌大小的木板被取了下来,露出后面一个黑黢黢的小空间。里面,
静静地躺着一把剪刀。不是现代常见的不锈钢剪刀,而是老式的,铁质的,
手柄处缠绕着暗红色的丝线,因为常年使用,丝线已经有些发黑磨损。剪刀的尖端,
在从窗户透进来的昏黄光线下,闪烁着一点幽冷的、令人不安的寒芒。就是它!我屏住呼吸,
伸手将它取了出来。入手一片冰凉,沉甸甸的,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质感。
几乎就在我指尖触碰到剪刀的瞬间——“咚!”“咚!”“咚!”沉重而缓慢的敲击声,
从前院的方向传来,一声接着一声,不疾不徐,像是用什么东西在敲打着院门。不,
不像是敲击院门……那声音,更像是……我猛地抬头,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起来。那声音,
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是脚步声。有什么东西,正拖着沉重无比的步伐,一步一步,
从前院,穿过堂屋,朝着后院,朝着我所在的这间偏房,走过来了!它走得很慢,
但每一步落下,都让老旧的木地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伴随着一种湿漉漉的、仿佛沾着粘液的拖沓声。我握紧了手中冰冷的剪刀,
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我死死盯着房门外那片昏暗的走廊阴影,喉咙发紧,
连吞咽口水的动作都变得无比艰难。那东西,来了。那脚步声沉重,粘腻,
每一步都像踩在腐烂的内脏上,发出令人牙酸的“咕叽”声,缓慢而执拗地穿透门板,
敲打在我的耳膜和心脏上。阴冷的气息顺着门缝钻进来,房间里的温度骤降,
我呼出的气都变成了白雾。握紧手中的剪刀,那铁质的冰冷几乎要冻结我的指骨,
上面缠绕的暗红色丝线粗糙地摩擦着掌心,带来一丝奇异的、近乎疼痛的实感。
这是我唯一的“武器”,也是唯一的生路。不能坐以待毙!我的目光急速扫过房间。窗户!
只有窗户!我猛地扑到窗边。老式的木棱窗,外面糊着早已发黄脆化的窗户纸。我用手一捅,
“刺啦”一声,脆弱的窗户纸破开一个大洞,外面是后院杂草丛生的角落,再远处,
就是镇子边缘模糊的树林轮廓。有希望!我用剪刀柄粗暴地敲掉残留的木棱和碎纸,
试图弄出一个足够钻出去的缺口。木屑纷飞,我顾不上割破的手掌,拼命扩大着洞口。
就在这时——身后的房门,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吱——嘎——”那声音干涩、扭曲,
仿佛木头的纤维正在被一股蛮力强行撕裂。我猛地回头。房门被推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
一只惨白、浮肿的手扒在门框上,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塞满了黑紫色的淤泥,正缓缓用力,
将门更推开一些。门缝后面,是浓得化不开的、蠕动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只手,
和门轴持续发出的、令人头皮发麻的噪音。它要进来了!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恐惧。
我不再去看门口,发疯似的用肩膀撞向那些顽固的木棱。“咔嚓!”一根较细的木条断裂,
洞口又大了一圈!差不多了!我毫不犹豫,先将拿着剪刀的手伸出去,然后头一低,
蜷缩着身体,拼命往那个狭窄的洞口钻。粗糙的木茬刮擦着我的后背、手臂,火辣辣地疼,
衣服被撕裂,但我顾不上了!半个身子刚探出去,
一股难以形容的、混合着河底淤泥和水草腐烂的腥臭气息,如同实质的墙壁,
从身后猛地压了过来!冰冷,湿重,几乎让我窒息。它到床边了!
我甚至能感觉到那东西带来的、几乎要凝结空气的寒意,正贴在我的脚后跟!
“呃……”一声模糊不清的、仿佛从灌满水的喉咙里发出的低吼,在我身后极近的距离响起。
我爆发出全身的力气,双脚在窗台上一蹬!“哗啦——!”伴随着最后几根木棱断裂的脆响,
我整个人从窗口摔了出去,重重砸在窗外半人高的荒草丛里。落地瞬间,
巨大的冲击力让我眼前一黑,五脏六腑都错了位,腥甜的铁锈味涌上喉咙。
但我一秒也不敢停留,手脚并用地从潮湿泥泞的地上爬起来,紧紧攥着那把救命的剪刀,
头也不回地朝着镇外树林的方向狂奔。身后,老宅的方向,
传来一声沉闷的、仿佛什么东西重重砸在墙上的巨响,随后,
是一种被激怒的、如同无数水泡破裂般的嘶鸣。我不敢回头,把所有的力气都灌注在双腿上。
杂草抽打着我的小腿,荆棘划破了皮肤,冰冷的夜风灌进我被扯破的衣服,
但我感觉不到疼痛,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几乎要炸开。冲进树林的瞬间,
光线骤然暗淡。月光被茂密的枝叶切割得支离破碎,在地面投下晃动扭曲的光斑。
林子里比外面更冷,空气里弥漫着落叶腐烂和湿土的气息。我靠在一棵粗糙的树干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冰冷的空气刺痛了喉咙和肺叶。直到这时,我才敢稍微回头,
望向来的方向。奶奶的老宅静静地矗立在镇子边缘,在渐浓的暮色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
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我逃出来的那个窗口,黑黢黢的,看不到任何动静。它……没有追出来?
还是说,它被什么限制在了那栋老宅里?稍微平复了一下几乎要跳出喉咙的心脏,
我才感觉到浑身无处不在的疼痛。手掌被木茬和剪刀柄划破了好几道口子,
火辣辣地疼;后背和手臂被刮擦的地方也传来阵阵刺痛;刚才摔那一下,
右脚踝似乎也扭到了,一动就钻心地疼。我借着稀疏的月光,摊开一直紧握的左手。
那把老式剪刀静静地躺在掌心。铁质的表面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幽冷的光泽,
缠绕手柄的暗红色丝线颜色深沉,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剪刀的尖端异常锋利,看着它,
就能想象到它轻易划开皮肉、剪断生命的场景。奶奶为什么会藏着这样一把剪刀?
那个黑袍老人为什么要我找到它?这把剪刀,到底有什么用?仅仅是拿着它,
就能对付那些没有影子的“东西”,还有老宅里那个恐怖的存在吗?无数疑问盘旋在脑海里,
但没有一个答案。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似乎捕捉到剪刀的尖端,极其微弱地闪烁了一下。
不是反射月光的那种光,而是一种更幽深、更诡异的,仿佛来自其内部的,冰冷的微光。
仅仅是一瞬间,就消失了。是我眼花了吗?还是……我死死盯着剪刀,但它再无异状。
林间的风穿过枝叶,发出呜咽般的声音,像是无数亡魂在低语。远处,小镇彻底沉入了黑暗,
没有一盏灯火,死寂得如同一座巨大的坟墓。我握紧了剪刀,
冰冷的触感不断提醒着我所处的险境。天,已经完全黑了。而我,
被困在了这个被阴影吞噬的小镇边缘,手里只有一把来历不明、用途不明的剪刀,
和一个不知是敌是友的黑袍人留下的、模糊的指令。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蜷缩在破庙腐朽的门板后,心脏在肋骨下狂跳,几乎要撞碎胸骨。
剪刀冰冷的触感深深烙进掌心,那缠绕手柄的暗红丝线仿佛活物,正随着我的脉搏微微搏动。
庙外,那粘稠的拖动声停了。死寂。连风穿过破洞的呜咽都消失了。空气凝固成沉重的胶质,
压迫着耳膜。月光被厚厚的乌云吞没,只有香案上那点将熄未熄的暗红火星,
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眼睛。它就在外面。我知道。那种被什么东西隔着门板贪婪舔舐的感觉,
冰冷又湿腻,顺着脊椎往上爬。我死死攥着剪刀,指甲掐进肉里,
用那点微弱的痛感强迫自己保持清醒,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呼吸被压到最轻,
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浓重的灰尘和霉菌味道,
还有一丝……从门缝渗进来的、若有若无的河底腥臭。“咚。”一声极轻微的敲击,
落在门板上。不是撞击,更像是指甲……或者别的什么坚硬之物,轻轻点了一下。
我浑身一僵,血液倒流。它在试探。冷汗瞬间浸透了我本就破烂的衣衫,粘腻地贴在皮肤上,
带来一阵阵寒颤。我死死盯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眼睛酸涩也不敢眨一下。“咚。
”又一声。位置比刚才高了一点,靠近门栓。老旧的门栓,只是一根横着的木条,
看起来脆弱不堪。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外面的东西极有耐心,
它不再发出声音,但那无处不在的、冰冷的窥视感并未消失,反而更加浓郁,如同水银,
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它在等什么?等我自己崩溃?等这破门自己倒下?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再次落到手中的剪刀上。幽暗的光线下,它沉默着,
尖端那一点寒芒似乎比刚才更清晰了些。奶奶……你用这把剪刀,到底对抗过什么?
突然——“嘶啦……”一种细微的、令人牙酸的刮擦声,从门板底部响起。
像是什么坚硬的东西,正在缓慢地、锲而不舍地刮着门下的木头。木屑,极其细微的木屑,
从门底的缝隙里飘了进来,落在积满灰尘的地面上。它在挖洞!它想进来!
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不能再等下去了!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
我的目光疯狂扫视着黑暗的庙堂。除了正门,还有哪里可以逃?窗户都被木板钉死了,
后墙似乎有个破洞,但被坍塌的杂物堵着大半……刮擦声持续着,
门板底部已经被刮出了一道浅浅的凹痕。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它就能弄出个缺口!
拼了!我猛地吸了一口气,压下喉咙里的腥甜。与其等死,
不如……一个疯狂的念头窜入脑海。我回忆起刚才黑影被剪刀逼退的场景。这把剪刀,
似乎对它们有某种克制作用。那么,外面那个东西呢?我慢慢挪动身体,调整姿势,
半蹲在门后,右手反手握紧剪刀,将锋利的尖端朝外,
左手则轻轻、轻轻地搭在了那根老旧的门栓上。心跳如擂鼓,汗水流进眼睛,又涩又疼。
我死死咬住下唇,屏住呼吸。刮擦声还在继续,专注于门板底部。就是现在!
我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将门栓往旁边一拉,同时身体向后急退!“哐当!
”门栓落地的声音在死寂中如同惊雷!几乎在门失去束缚的同一瞬间,
一股巨大的、夹杂着浓郁腐臭的力量从外面狠狠撞在门上!“砰!!
”腐朽的木门根本不堪一击,瞬间向内爆裂开来!木屑纷飞中,
一个庞大、臃肿的黑影裹挟着刺骨的寒意和令人作呕的腥风,猛地挤了进来!
借着一闪而过的、从破门涌入的微弱天光,
我看到了它模糊的轮廓——像是一个被水浸泡到巨人观的尸体,皮肤惨白浮肿,
滴滴答答往下淌着粘稠的黑水,四肢不成比例地粗大,头颅几乎缩进了肩膀里,看不到五官,
只有一片模糊的、蠕动的黑暗。它进来了大半个身子,带着一股要碾碎一切的恐怖气势!
就是现在!我没有逃跑,反而迎着那扑面的恶臭和寒意,将全身的力气和所有的希望,
都灌注在握着剪刀的右手上,朝着那挤进门内的、臃肿庞大的黑影,狠狠地刺了过去!
“噗嗤!”一声怪异沉闷的声响,像是刺破了装满湿泥的皮囊。
剪刀的尖端毫无阻碍地没入了那惨白浮肿的躯体,直没至柄!“嗷——!!!
”一声绝非人类能发出的、凄厉到极点的尖啸,猛地从那个没有头颅的躯干里爆发出来!
那声音尖锐刺耳,仿佛能撕裂灵魂,震得整个破庙都在簌簌发抖!被我刺中的地方,
没有流血,而是猛地爆开一团浓稠如墨的黑气!那黑气翻滚着,扭曲着,
发出“滋滋”的腐蚀声响,仿佛被无形的火焰灼烧!那庞大的黑影触电般剧烈地抽搐、挣扎,
撞得庙里的破桌椅四处飞溅!它想要后退,想要逃离插在身上的那把剪刀!有效!
剪刀真的有效!狂喜和更大的恐惧同时攫住了我。我死死握着剪刀柄,不敢松手,
身体被它巨大的挣扎力量带得左摇右晃,脚下踉跄。“滋啦——!”又一声怪响,
剪刀刺入的地方,那团爆开的黑气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剪断了?
像是一根无形的、绷紧的线?随着这声怪响,那黑影的挣扎猛地一滞。然后,
在我惊骇的目光中,它那臃肿庞大的身躯,就像被戳破的气囊,或者阳光下的冰雪,
开始迅速地消融、塌陷!大量的黑水从它体内涌出,汩汩地流淌在地上,
散发出更加浓烈的恶臭。那惨白的皮肉萎缩、干瘪,几个呼吸之间,
就化作了一滩不断冒着气泡的、粘稠的黑色淤泥,只剩下几缕破烂的、看不出原貌的布料,
浸泡在其中。插在它“尸体”上的剪刀,“哐当”一声掉落在黑泥边缘,幽冷的锋刃上,
一丝黑气正缓缓消散。我脱力地后退几步,背靠冰冷的墙壁,滑坐在地,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都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看着门口那滩逐渐停止冒泡的、散发着恶臭的黑泥,一阵强烈的虚脱和反胃感涌了上来。
我……我干掉它了?用奶奶的剪刀?还没等我缓过神,掉落在黑泥边的剪刀,
突然毫无征兆地再次亮起!这一次,不再是微光。那幽冷的光芒骤然变得强烈,
甚至有些刺眼,将剪刀周围一小片区域都映照成一种诡异的青白色。光芒吞吐不定,
仿佛在呼吸一般。与此同时,剪刀本身开始发出一种低沉、持续的嗡鸣声,
手柄上缠绕的暗红丝线,颜色似乎也变得鲜艳了一些,隐隐发烫。它……在渴望着什么?
我惊疑不定地看着这异象,不敢上前。突然,剪刀的嗡鸣声变得急促起来,
尖端猛地指向——庙堂深处,那尊倒塌了一半、布满蛛网的神像方向!光芒也随之转向,
如同一道青白色的探照灯,笔直地打在神像基座后方,那片最浓重的阴影上。
就在那片被光芒照亮的阴影里,一个原本绝不可能被注意到的东西,
清晰地显现出来——那是一个小小的、用同样暗红色丝线系着的、褪了色的旧护身符,
歪歪斜斜地挂在神像基座一块突出的残破石棱上。护身符的样式很古老,
像是本地庙宇里曾经常见的那种,上面用墨笔画着早已模糊不清的符文。
剪刀的嗡鸣声在指向那个护身符时,达到了顶点,光芒也稳定地聚焦在那里,不再移动。
它在……指引我?奶奶的剪刀,在指引我,去找那个护身符?我撑着发软的双腿,
艰难地站起身,警惕地看了一眼门口那滩逐渐凝固的黑泥,然后一步一步,
小心翼翼地朝着神像基座走去。越靠近,
越能感觉到从那护身符上传来的一种极其微弱的、却与剪刀隐隐共鸣的波动。很微弱,
但确实存在。我伸出手,指尖触碰到那个冰凉、布满灰尘的护身符。就在我解开丝线,
将它握入手中的刹那——“铛!!!!!”一声巨大、沉闷,仿佛来自地底深处的钟鸣,
毫无预兆地,响彻了整个死寂的小镇!这钟声恢宏、苍凉,带着一种古老而沉重的力量,
震得破庙屋顶的灰尘簌簌落下,也震得我心神剧颤!我猛地抬头。
钟声……是从小镇中心的方向传来的!那个方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镇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所在的位置附近!几乎在钟声响起的同时,
我手中那把剪刀的光芒和嗡鸣,瞬间消失了,恢复了之前那种沉默冰冷的铁器状态。
而刚刚得到的那个旧护身符,却在掌心传来一丝微弱的暖意。门外,
那令人窒息的、被窥视的感觉,如同潮水般退去了。远处小镇的死寂也被打破,
隐约传来一些……细微的、难以分辨的骚动声响。我握紧剪刀和护身符,心脏沉了下去。
这突如其来的钟声,意味着什么?是警钟?是召唤?还是……某种更可怕东西苏醒的前兆?
黑夜,还远未结束。那口钟的余韵还在潮湿的空气里震颤,像一块投入死水的巨石,
激起的无形涟漪正粗暴地搅动着这座活死人墓般的小镇。我紧贴着破庙冰冷潮湿的墙壁,
手中紧紧攥着那把刚刚“饱饮”了邪恶的剪刀和来历不明的护身符。钟声过后,
死寂被打破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令人心悸的声响。远处,小镇的深处,
传来了模糊的、拖沓的脚步声,不止一个!还有低沉的、仿佛梦呓般的絮语,
夹杂着某种……木质家具被缓慢移动的摩擦声。它们不再隐藏,不再静止,
仿佛那声钟鸣是一个信号,唤醒了所有蛰伏在阴影里的东西。不能待在这里!庙门已破,
那滩冒着泡的黑泥就是最醒目的坐标。我的目光落在掌心那个刚刚得到的旧护身符上。
它由暗红色的丝线编织而成,样式古朴,上面用墨笔描绘的符文已经褪色模糊,
边缘磨损得厉害。此刻,它正散发着一丝极其微弱、却持续不断的暖意,
与剪刀冰凉的触感形成奇异的对比。它在指引?还是仅仅在……共鸣?钟声是从小镇中心,
老槐树附近传来的。那是黑袍老人出现的地方,也是我最初进入这噩梦的起点。必须去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