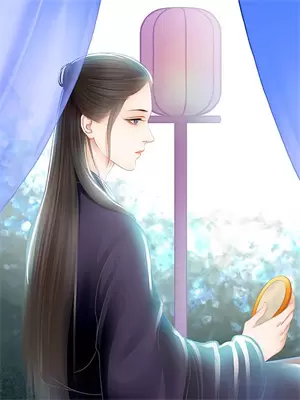我爸是镇上最后一个刽子手。这行当传到我这辈,算是绝了根。我没接手,不是因为嫌弃。
是因为爸临死前盯着我的眼睛说:“咱家这手艺,有三不砍。记住了,死规矩。
”“一不砍孕妇。“二不砍戏子。三不砍……”话没说完,他就咽了气。第三样是啥,
成了我心里一根刺。我没敢问妈,她恨透了这行当。说要不是爸干这个,
我哥也不会跑得没影。1我哥大我五岁,叫陈青。十年前说是去省城找活干,一去就没回来。
妈哭瞎了只眼,从此不准家里提“刽子手”三个字。我在镇上的木材厂干活,日子本来平静。
直到那天中午,厂里来了个生面孔。“陈师傅在吗?”来人穿着体面,像是城里人。
工友推我一把:“找你的。”那人递过来一张照片。是我哥,穿着戏服,脸上画着浓彩,
正对着镜头笑。“陈青先生委托我来一趟。”那人压低声,“他遇着麻烦了,
需要家里帮把手。”我心跳得厉害,十年没音信,一来就是麻烦?“什么麻烦?
”那人却不直说,只道:“他人在省城吉祥戏院,指名要见你。说是……家里老规矩,
他沾了边。”我心里咯噔一下。老规矩?爸说的三不砍,第二就是戏子。我当晚就辞了工。
妈知道后,把碗摔了:“不准去!你哥自己选的路,死活自己担着!”但我还是走了。
心里那根刺扎得太深——我想知道爸没说完的第三样是啥,更想见我哥一面。
2省城比镇上热闹百倍。吉祥戏院气派得很,红墙金瓦,
门口贴着大幅海报:当红武生陈青领衔主演《林冲夜奔》。我找到后台时,戏正散场。
班主听说我是陈青弟弟,脸色就变了。“你来晚了。”班主搓着手,
“陈老板他……三天前就没了。”我愣在那儿,耳朵嗡嗡响。“怎么没的?
”班主支支吾吾:“演戏出了意外,从台上摔下来……后事都办完了。
”他递过来个布包:“这是陈老板留的东西,指名要交给你。”包里是套戏服,叠得整齐。
我抖开一看,是件白底绣蓝纹的武生行头,心口处一团暗红,洗不干净的血渍。还有封信,
我哥的字迹潦草:“小弟,爹说的三不砍,我沾了第二样,怕是躲不过。你若收到这信,
我已去了。戏服留给你,千万烧掉,别穿也别留。”我捏着信纸,手指发颤。我哥是戏子,
我是他血亲——这算沾了哪条规矩?3回到旅店,我一夜没合眼。快天亮时,有人敲门。
是个姑娘,二十出头,穿着素净,眼睛红肿像是哭过。“您是陈青先生的弟弟?
”她声音抖着,“我叫小月,是陈先生的……戏迷。”我让她进屋。她盯着那包戏服,
眼泪就下来了。“陈先生不是意外。”她突然说,“是有人害他。
”我猛地抬头:“你说什么?”“那晚我就在台下。”小月攥着衣角,
“陈先生唱到《夜奔》那段,本该空翻落地,可他却突然僵住,
直挺挺摔了下去……像是看见什么吓人的东西。”她压低声:“更怪的是,他摔下去后,
台上凭空多了个人影,穿着黑衣,拎着把斧头……就一闪,没了。
”我后背发凉:“别人看见没?”“都说我眼花了。”小月苦笑,“可我知道不是。
陈先生前几天就说过,他惹了不该惹的人,怕是逃不过。”“陈先生留了话,说要是他出事,
就让他弟弟穿上这套戏服,替他唱完最后一场。”我愣住:“我?我不会唱戏。
”“他说你不用真唱,就穿戏服走个过场。“他说这样才能送他安心走,否则……怨气不散,
会成祸害。”我想起我哥信里的话——明明让我烧掉戏服。可看着小月通红的眼睛,
又想起我哥死得不明不白,鬼使神差点了头。“就当送他一程。”我想。4第二天晚上,
我瞒着班主,偷偷溜进戏院后台。戏服比想象中沉,缎面冰凉贴肉。我对着镜子系扣子,
镜里的人渐渐不像自己了。油彩没画脸,可那身段那行头,活脱脱另一个陈青。
小月在幕布后等我:“等下幕拉开,你从台左走到台右,鞠个躬就成。我安排了人叫好,
不会露馅。”幕布缓缓拉开。台下黑压压一片,锣鼓点敲得急。我深吸口气,迈步上台。
灯光刺眼,我看不清台下,只依言往前走。走到台中央时,头顶灯突然闪了闪。
一股冷风刮过后颈,我打了个哆嗦。余光瞥见台侧立着个人影——黑衣,高瘦,
手里拎着件长家伙,用布裹着看不清。我心跳漏了拍,想起小月说的黑衣斧头人。
锣鼓声突然停了。台下死寂一片。我僵在台上,进退不是。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很轻,
却一步一响敲在我心上。没等我回头,脖领子一紧,被人拽向后台。幕布哗啦落下,
隔开台下视线。拽我的是个老头,干瘦得像柴禾,眼睛却亮得吓人。“不要命了?
”他嗓子嘶哑,“穿死人的戏服上台,嫌命长?”我喘着气,说不出话。
老头指着戏服心口那团暗红:“这血是谁的,你问清楚没?
”我愣住:“我哥的……摔死时的血。”老头冷笑:“你哥摔的是后脑,这血渍在心口。
”我低头看,那团暗红果然正中心脏位置。“那是谁的血?”我声音发干。老头没答,
反问道:“你姓陈?陈金魁是你什么人?”陈金魁是我爸的名字。“我是他儿子。
”老头眼神一变:“怪不得……那你哥死前,是不是碰过刽子手的家什?
”我猛然想起——爸死后,他用的那把鬼头刀不见了。妈说是扔了,可我哥离家前夜,
曾偷偷去过老屋……老头看我表情,心里明白了七八分:“小子,你哥穿了戏服又碰了刀,
犯了两重忌。“你现在穿他的血衣上台,是嫌那东西找不着你?
”我头皮发麻:“那东西是什么?”老头刚要开口,后台门砰地被撞开。小月冲进来,
脸色白得吓人:“不好了!台下……台下死人了!”我和老头赶到台前,观众已乱作一团。
台正下方躺着个男人,心口插着把短斧,血淌了一地。5警察很快来了,封锁现场。
我问小月:“死者是谁?
”小月嘴唇发抖:“是戏院的老板……唯一不同意给陈先生办最后一场的人。
”我脊背发凉:“你让我上台,不是为了送我哥?
”小月眼泪掉下来:“陈先生说……只有他弟弟穿这身戏服走一趟,才能引出害他的人。
”我忽然明白,我哥信里为什么让我烧掉戏服——他早知道这衣服不干净。警察盘问到我这,
我说不清道不明,差点被当嫌疑人扣下。还是那老头作证,说我一直后台,没作案时间。
折腾到半夜,我才脱身。回到旅店,我掏出那套戏服,心口血渍越发刺眼。我爸说的三不砍,
第二是戏子,第三是至亲。我哥既是戏子,又是我至亲。他碰了刽子手的刀,
穿了带血的戏服。而现在,我也穿了同一件戏服。窗外忽然传来敲击声,不紧不慢,
像有人用指甲抠玻璃。我猛地转头——窗外空空荡荡,只有夜色浓重。敲击声又响起来,
这次是在门上。哆,哆,哆。每一声,都敲在我心上。6我屏住呼吸,
手指紧紧攥着戏服冰凉的缎面。敲门声停了,走廊里传来拖沓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冷汗顺着脊梁滑下来。我猛地想起那老头——他好像知道些什么。第二天一早,我直奔戏院。
果然,那老头就蹲在后门抽烟,眯着眼晒太阳。“就知道你会来。”他吐出口烟圈,
“陈金魁的儿子,逃不掉的。”我蹲到他旁边:“您认识我爸?”“何止认识。”他冷笑,
“当年一个头磕地上的交情。你爸没跟你说过刘三刀?”我摇摇头。爸从不提往事。
刘三刀咂咂嘴:“也难怪。刽子手这行当,见不得光。你爸金盆洗手早,
我是吃到最后一碗饭的。”他撩起衣襟,露出腰间一道狰狞的疤:“看见没?
最后那趟活儿给的纪念。刀口偏一寸,我就见阎王去了。
”我盯着那道疤:“我爸说的三不砍……”“孕妇、戏子、至亲。”刘三刀接得顺溜,
“孕妇肚里是两条命;戏子扮相欺神瞒鬼;至亲血脉相连,刀下去损阴德。
”他忽然盯住我:“你哥碰刀了?”我喉头发干:“他离家前夜,我爸的鬼头刀不见了。
”“作死!”刘三刀一拍大腿,“刽子手的刀是凶器,沾过多少血?怨气重得很!
你哥不但碰了,还带着刀去唱戏——双忌临头,阎王都救不了!
”我想起戏服心口的血渍:“那我哥到底怎么死的?”刘三刀眼神躲闪:“警察不是说意外?
”“您知道不是。”我盯着他,“那晚台下死人了,凶器是短斧。
小月说看见黑衣拎斧头的人。”刘三刀猛吸一口烟,烟雾缭绕里他的脸模糊不清。“小子,
有些事不知道为好。”“那是我哥!”我声音发颤,“死得不明不白,现在有人敲我门,
穿戏服的就死人——我得知道真相!”刘三刀沉默良久,终于叹气:“你哥惹的不是人。
”我愣住:“什么意思?”“刽子手这行当,世代相传的不仅是手艺,还有债。
”“每把刀都欠着血债,债主会找上门来。你爸的刀沾过戏子的血——那是个名角,
唱武生的,心口中刀而死。”我后背发凉:“什么时候的事?”“四十年前。
”刘三刀吐出烟蒂。“那会儿你爸刚出师,接了个私活儿——有人花钱买那戏子的命。
后来才知道,那戏子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至亲加戏子,我爸一口气犯了两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