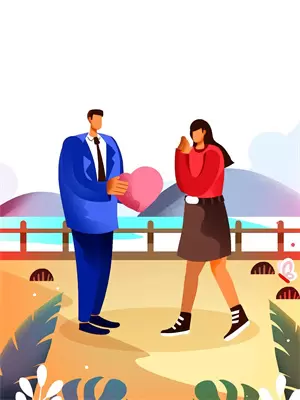
庆功宴上,顾衍冷眼看着我修复的传世苏绣被合伙人踩碎:“旧东西早该进博物馆。
”我将染血的绣片捡进包中,当晚便签好了离婚协议。三个月后AI帝国陷入侵权丑闻,
他落魄回国,却在机场大屏看见前妻的苏绣直播。“匠人精神yyds!
”百万弹幕淹没了画面。他匿名拍下我的《涅槃》小稿,备注:“请好好飞。
”后来我的工作室遭AI工厂围剿,
他熬红双眼黑进我工作室的服务器:“别让垃圾脏了你的路。”故宫特展开幕那夜,
我一针一线绣出的金线凤凰在恒温柜中流光溢彩。他混在人群里安静记笔记,
抬头时却只换来我一个疏离的颔首,爽了。---冷。
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像个巨大的冰窖。冷光玻璃折射着全息投影的蓝色数据流,
在顾衍“灵晷”AI 4.0发布的庆功宴上流淌。
空气里是香槟的甜腻和电子元件特有的、干燥的金属气味。
我抱着那个蒙着素白丝绢的梨花木绣框,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缝隙里穿行。丝绢下,
是我用八个月心血,将外婆陪嫁的、碎成十二片的苏绣《百鸟朝凤》残片,
一针一线重新补羽、接翎、赋予新生。指尖的薄茧在光滑的木框上留下细微的摩擦声,
那是属于我的时间日记。我终于挤到人群中心。顾衍被簇拥着,一身剪裁完美的深灰色西装,
像一尊被数据点亮的完美雕塑,额角那道月牙疤在冷光下也显得锋利。他正和人谈笑,
侧脸的线条绷得很紧。“顾总!”一个带着醉意的粗嘎嗓门传进来,是合伙人赵鸣。
他挺着微凸的肚子,金边眼镜滑到鼻梁上,袖口昂贵的金属袖扣晃眼,“哟,嫂子也来啦?
还抱着您那传家宝呢?”他凑近一步,浓重的酒气喷过来,
手指大大咧咧地就要去撩那层遮着的丝绢,“这老物件,费这老鼻子劲!
够咱‘灵晷’跑十万张高清矢量图喽!哈哈!”我下意识侧身想护住绣框。晚了。
赵鸣醉醺醺地一挥手,沉甸甸的袖口猛地扫在梨花木框上!“哗啦——!
”刺耳的碎裂声炸开。蒙着的丝绢滑落。玻璃保护层四分五裂,尖锐的碎片溅落一地。
更刺目的是,一只意大利手工皮鞋,正不偏不倚,
狠狠踩在绣面上那只引颈欲鸣的金线凤凰头颈处!金线崩断,翠羽碾污。
那只浴火重生的凤凰,瞬间身首异处。时间凝滞了一秒。周围虚伪的谈笑像被掐断的电流,
静得可怕。无数道目光,或惊愕,或好奇,或幸灾乐祸,钉子一样钉在我身上。我没动,
抱着破损的绣框,指尖冰凉。顾衍的目光终于落了过来。没有惊怒,没有心疼,
只有一种程序调试日志般的平静漠然,扫过地上狼藉的碎片和被踩踏的绣面。他蹙了蹙眉,
像是被打扰了重要运算的进程。“赵总喝多了。”他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死寂,
像冰冷的代码注入空气,“旧工艺,早该进博物馆了。”他转向我,
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既定事实,“青瓷,别扫大家的兴。收起来吧。”旧东西。扫兴。
呵呵,原来我珍爱之物在你们眼里是扫兴的东西。我缓缓地蹲了下去。
昂贵的晚礼服裙摆拖在冰冷的地板上,沾上香槟渍和碎玻璃渣。我伸出苍白的手,
小心翼翼地去拾那些染了污渍、沾了玻璃的残片,锋利的碎片边缘轻易划破了指尖。
一滴鲜红的血珠,迅速凝聚,饱满,然后滚落。嗒。血珠不偏不倚,
落在那片被踩得最污浊的翠羽上。浓烈的红,瞬间洇开一小片,
像古画上点下的最后一滴绝望的朱砂,刺目惊心。我强忍着没有哭。
甚至没有抬头去看顾衍或者赵鸣一眼。长长的睫毛垂着,在眼下投出小片阴影。
只是指尖控制不住地细微颤抖着,固执地、一片一片,将那些破碎的锦绣,
捡回自己随身的帆布包里。冰冷的宴会灯球旋转着,把惨白的光打在我的脸上,如霜雪一般,
但更寒冷的是我的心。一切都该结束了。凌晨两点。智能门锁感应开启,
柔和的光带无声地亮起,勾勒出玄关冰冷的线条。顾衍扯松了领带,
带着一身酒气和夜晚的寒气走进来。皮鞋踩在光洁的地板上,发出空旷的回响。
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开放式餐厅长桌另一端的我。我没有换衣服,
还穿着那身沾了污迹的晚礼服,背脊挺得很直。餐桌上,一份摊开的文件静静躺在那里。
旁边,是那个梨花木绣框,里面是缝到一半的凤凰翅膀,金线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与文件上“离婚协议书”几个黑体字形成讽刺的对比。“我已经签好了名。
”顾衍的脚步顿住,随即扯出一个近乎好笑的弧度,走到桌边,手指在光滑的桌面上敲了敲,
目光扫过那破损的绣框。“就为一块破布?”他松了松领带结,
语气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不解和淡淡的嘲弄,“青瓷,现实点。
‘灵晷’能把全球纹样数据库一天迭代三百次,你的针脚再密,再熬通宵,
也追不上算力的一个零头。何必?”我抬起头,脸上没有泪痕,只有一种近乎透明的平静,
眼底深处却像淬了冰的深潭,死寂,又透着孤注一掷的决绝。“我追的不是算力,顾衍。
”她的声音很轻,像最细的蚕丝在风里飘,却清晰地钻进他耳朵里,“我追的是时间,
是人心。”指尖轻轻拂过绣框上那半只挣扎着要飞起的翅膀,“我外婆用了整整三年,
才绣好一对凤凰翅膀。每一针,都带着对我外公平安的祈愿。那三年,是她的命。
”我的目光直直刺向他,“你把它,叫做破布?”顾衍嘴角那点虚假的笑意彻底消失了。
他盯着我,像在看一个运行出错的陌生程序。他就是这样,仿佛眼里的所有人都是程序代码。
“签字吧。”我把那叠协议往他面前推了推,声音斩钉截铁。顾衍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脸上瞬间覆上一层薄怒和荒谬感。他嗤笑一声,像是觉得我幼稚得可笑。
他猛地拔开那支万宝龙钢笔的金色笔帽,龙飞凤舞地在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力透纸背。
“行。”他丢下笔,金属笔身撞击桌面发出脆响,“沈青瓷,你硬气。离开我,
你那小破工作室,靠这些‘时间’和‘人心’,撑不过三个月。别到时候哭都找不着调。
”我站起身,动作干脆利落,拿起那份签好的协议,小心地收进帆布包里。转身时,
我顺手“哐当”一声合上了那个装着残破凤凰的绣框。沉重的声音在寂静的豪宅里回荡,
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黄铜大锁,狠狠落下,彻底封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关系,
结束了那令我作呕的婚姻。“那就三个月后再见。”我头也不回,厚重的门在身后无声合拢。
第二天上午,阳光透过老弄堂狭窄的窗户,
斜斜照进一间小小的、堆满各色丝线和绣架的屋子,
空气里有淡淡的蚕茧和木质绣架混合的气味。我坐在一张老旧的榉木工作台前,
桌上摊着昨夜捡回的、染着血污的《百鸟朝凤》碎片,像一座小小的、悲壮的山丘。
拿起手机,点开二手平台,找到列表里那块顾衍曾送我的百达翡丽星空腕表。
冷光蓝的表盘上,星辰流转,曾经代表永恒的时间,如今只剩讽刺。
我毫不犹豫地标了个远低于市场价但足够急用的价格,确认上架。三小时后,
手机提示音清脆响起——成交。钱款到账的数字,足够支付这间小小工作室半年的房租。
我轻轻吁了口气,放下手机。
一枚小巧的素银顶针——那是用那枚曾象征婚姻承诺的钻戒熔铸而成——稳稳套在无名指上。
冰冷的金属触感奇异地带给了我一种踏实的力量。昏黄的台灯光线下,
我拿起一枚细如牛毛的绣花针,穿起一根比发丝还细的金线。
指尖抚过绣片上凤凰断裂的颈项边缘,动作轻柔得像怕惊扰一个沉痛的旧梦。“外婆,
”我对着空气,也对着满桌破碎的锦绣,声音轻得像叹息,又带着破土而出的坚定,
“这一次,我只为‘无用’而活。”窗外,弄堂里传来模糊的市井人声。窗内,
针尖刺透丝帛,发出极其细微的“噗”声。一缕金线,
开始艰难地缝合我那道代表屈辱的裂痕。而此刻,三万英尺高空,飞往硅谷的航班头等舱内。
顾衍靠在宽大的座椅里,面前的平板电脑屏幕亮着,
幽蓝的光映着他略显疲惫却依旧冷硬的脸。
屏幕上是他引以为傲的“灵晷”AI核心模型架构图,无数参数节点如星辰闪烁。
他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随意滑动,精准地点中其中一个被标注为“家庭”的参数模块。
没有丝毫犹豫,指尖一划,那个模块被他干净利落地拖拽出来,
丢进了屏幕边缘一个名为“废弃冗余参数”的虚拟回收池里。图标闪烁了一下,彻底消失。
他合上眼罩,隔绝了外界的光。仿佛丢弃的,不过是一段运行不畅、需要优化的旧代码。
---三个月后。浦东国际机场。巨大的落地窗外,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
酝酿着一场迟来的大雨。顾衍拖着登机箱,脚步有些滞重地汇入抵达的人流。
他眼下一片浓重的青黑,像被人狠狠揍了两拳。昂贵的西装起了褶皱,
行李箱里塞满的不是礼物,而是来自欧盟的律师函副本——冰冷、厚重,压得他透不过气。
“灵晷”因训练数据侵权被调查,市值像被戳破的气球,瞬间蒸发了17%。
疲惫几乎刻进骨头缝里。他揉了揉刺痛的太阳穴,
额角那道月牙疤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更加突兀。广播里温柔的女声播报着航班信息,
在他听来只是无意义的噪音。忽然,前方一片巨大的LED广告屏切换了画面。
柔和的光线倾泻而下,瞬间吸引了他的目光,也攫住了他疲惫的神经。
屏幕上是B站直播间的实时推送:非遗复兴|72小时极限挑战!
苏绣up主@青瓷有光 直播绣制《涅槃》。画面中,是我沈青瓷。
我坐在一张古朴的绣架前,侧脸对着镜头。一盏专门用于精细工作的柔光灯从侧面打过来,
专注的眉眼、微抿的唇角被镀上了一层近乎圣洁的柔焦光晕。
我戴着那个素银顶针的无名指稳定地捏着细针,指尖翻飞,快得几乎带起残影。
金线、翠羽如同被我赋予了生命,一点点汇聚成一只浴火凤凰的轮廓,
每一根翎羽都透着不屈的张力。屏幕下方,弹幕疯狂滚动,层层叠叠,
像一场无声的雪崩:“卧槽!这手速!这耐心!匠人精神yyds!”“给大佬跪了!
凤凰要活了!”“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AI画的那是什么垃圾!”“青瓷大大看我!
求开课!”“泪目了…这就是传承的力量吗?”“守护最好的青瓷老师!
”顾衍像被施了定身咒,僵立在行李转盘旁。周围喧嚣的人声、滚轮摩擦地面的噪音,
瞬间被抽离。他的世界里只剩下那块巨大的屏幕,和屏幕上那双翻飞的手。那双手。
那双手曾在他清晨出门前,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替他抚平衬衫领口细微的褶皱,
系好领带。指尖的温度似乎还残留在他颈间的皮肤上。如今,这双手在万千陌生人的注视下,
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和沉稳的力量,正为一只即将涅槃重生的凤凰,点染最璀璨的睛。
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一片惨白,像被抽干了所有血液。行李转盘嗡嗡作响,
传送带不断循环,像他此刻空转的大脑。他忘了去拿自己的箱子,只是死死盯着屏幕,
直到那个直播推送的画面结束,切换成机场的广告。一股尖锐的、从未有过的刺痛,
毫无预兆地狠狠扎进心口。比欧盟的律师函更冰冷,比连轴转的谈判更疲惫。
他几乎是踉跄着走向出租车候客区。坐进车里,隔绝了外面的嘈杂,他立刻掏出手机,
手指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微颤,点开B站,搜索“青瓷有光”。
一个又一个视频跳出来顾衍机械地刷着。
工作室日常:青瓷大大教一个染着雾霾蓝短发的年轻女孩林杏劈丝,动作耐心细致。
作品展示:《洛神赋图》局部,水波浩渺,衣袂飘飘,针法繁复精妙得令人窒息。
签约新闻:官方文旅账号转发,盖着大红印章的“非遗示范基地”合作函。
粉丝数量:那个代表关注度的数字,已经突破两百万,还在不断跳动上涨。
订单排期:置顶公告里,一行小字清晰写着:“工期已排至后年,感谢厚爱。”然后,
他的目光死死定格在一个直播回放的截图上。镜头拉近,
那是摄像师给了我捏针的手一个特写。那枚素银顶针,在灯光下泛着温润内敛的光泽,
稳稳地套在她左手的无名指上。空空如也。那枚象征着他、象征着我们曾经关系的铂金婚戒,
早已消失不见,被这枚冰冷的工具彻底取代。手机屏幕的光,映着他失神的瞳孔。
车窗外的雨终于落了下来,密集的雨点打在玻璃上,被雨刷器粗暴地刮开,
留下道道模糊扭曲的水痕,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此刻混乱不堪的心绪。
一种前所未有的、名为“失去”的实质感,混合着迟来的钝痛和荒谬的空虚,
密密麻麻地啃噬着他。顾衍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喉结艰涩地滚动了一下。
“原来……”他对着冰冷的车窗,对着外面模糊的雨幕,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被留下的,是我。”当晚,某知名线上艺术品拍卖平台,
一件名为《涅槃·小稿》的苏绣作品悄然上架。尺寸不大,却是那只完整凤凰的精华缩影,
金翠交织,神采飞扬,带着直播间里那种破茧而出的生命力。起拍价不菲。
拍卖过程静默无声,却在最后几分钟掀起波澜。一个匿名ID突然杀入,以近乎碾压的姿态,
连续加价。最终,成交。成交价:六位数。订单生成。匿名买家只在快递备注栏里,
留下三个字:请好好飞。---梧桐掩映的法租界深处,一扇斑驳的旧木门安静地立着。
门槛边散落着几束素色的蚕丝线,在午后的微风里轻轻拂动。门楣上挂着一块小小的木牌,
刻着四个清秀的字:“青瓷有光”。顾衍站在门前。一身昂贵的极简灰西装,
手里提着一个印着烫金logo的硬质文件袋,
为诚意满满的投资计划书——用最前沿的AI配色算法、大数据市场分析、智能化生产管理,
想要“赋能”我的传统工艺。顾衍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挂着老式铜风铃的木门。
“叮铃——”清脆的铃声在安静的工作室内响起。室内光线柔和,
空气中弥漫着蚕丝和植物染料的淡香。顾衍进来时我正伏在宽大的绣架前,
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放大目镜,神情专注得近乎神圣。左手稳定地托着绣绷,
右手用一把细长的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根几乎肉眼难辨的1/16丝线,
正试图将其精准地压入水波图案的特定位置。动作稳定,呼吸轻缓。听到铃声,我并未抬头,
只是从目镜上方抬起眼皮,目光精准地扫向门口,又迅速落回手中的丝线,
声音平淡无波:“取拍品请左转前台。”顾衍喉头发紧,向前一步:“青瓷,
我们能不能谈谈?”他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可靠,像过去无数次在谈判桌上那样。
“顾总,”我手里的镊子稳稳地将那根细若游丝的线压入水面纹理,动作没有丝毫停顿,
“前台右转有AI客服,24小时高效服务,能解答您一切商业咨询。”冰冷,高效,
拒人千里。像一道无形的防火墙,瞬间将他隔绝在我的世界之外。他精心准备的说辞,
他引以为傲的“解决方案”,在我这堵无形的墙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
他只能僵立在那里,看着我继续操作。最终顾衍忍不住开口,
试图打破这种让他窒息的沉默和“低效”:“青瓷,你这工期太长了。
如果接入我这边最新的AI配色算法,自动生成最优方案,至少能把工期缩短一半!
效率提升,订单就能接更多,何必……”镊子尖,悬停在那片即将完成的碧波之上。
我被气到了,缓缓抬起了头。摘下了放大目镜,直直的看着他。我的声音不高,
甚至没什么起伏,却像最光滑的冰丝滑过冰冷的瓷胎,带着一种能割裂空气的锐利:“顾衍。
”我清晰地叫出他的名字。“你的钱,救不了濒死的文化。”我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像冰锥,
“就像你的AI,永远理解不了人心的温度。”顾衍像是被无形的针扎了一下,
眉头猛地拧紧。“我的‘慢’,不是低效。”我的目光扫过他手中的文件袋,
像扫过一堆垃圾,“是敬畏。是对每一根丝线、每一次下针、每一份传承的敬畏。
”我微微倾身,目光如刀锋般锁定顾衍,“而你的‘快’,顾衍,除了制造焦虑,
还剩下什么?”空气凝固了。顾衍只觉得脸上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火辣辣的疼。
他引以为傲的“快”,他用以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尺,在她口中,只剩下一文不名的“焦虑”。
“离我的世界远点。”她最后下了判决,声音里是不容置疑的驱逐。话音刚落,我便抬手,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工作台下方一个不起眼的按钮。
嗡——沉重的电动卷帘门发出低沉的启动声,从门楣上方开始,迅速、坚决地向下滑落,
金属叶片摩擦着轨道,发出刺耳的噪音。像一个巨大的灰色马赛克格子,
冷酷地在他与她之间落下,与顾衍——我的前夫,彻底隔绝。顾衍下意识想伸手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