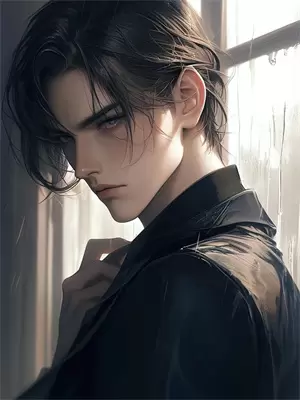
那晚,社长陈浩在活动室里撕碎毕业合照的声音,像某种脆弱的东西被彻底碾碎,
尖利地刮过我的耳膜。碎片雪片般在昏黄的灯光里纷飞,落到积着薄灰的木质桌面上,
落到我冰凉的手背上。他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像个突然被戳破的气球,干瘪而惊惶。
“假的…都是假的!这照片有问题!”他声音嘶哑,眼睛死死瞪着桌上的碎片,
仿佛那里盘踞着一条毒蛇。活动室里死寂一片,只有他粗重的喘息在回荡。其他人面面相觑,
最终是副社长李峰皱着眉,带着点安抚又有点不耐烦的语气开口:“浩哥,冷静点,
不就是相机又抽风了嘛?又不是第一次了。历年合照不都这样,多个人影,模糊不清的,
老传统了。”他走过去,试图拍拍陈浩的肩膀,却被对方猛地甩开。陈浩抬起头,
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过我们每一个人,那眼神里翻涌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几乎要溢出来。
他最终死死盯住了我,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溺水者般的绝望:“苏晓…你…你也看到了,
是不是?不是模糊的…这次不是模糊的!是林晚!是她!”林晚。
这个名字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一圈冰冷而沉重的涟漪。
那个三年前因抑郁症退学,最终消失在所有人视野里的学姐。
我强迫自己看向桌上那些散落的碎片。一块稍大的碎片上,恰好是照片的边缘。
社长陈浩僵硬地站在前排中央,而在他的身后,
在照片那诡异的、仿佛被刻意虚化过的角落里,清晰地站着一个女生。
不再是往年的模糊轮廓。她穿着一件旧式的、水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连衣裙,样式简单,
裙摆却显得异常沉重。及腰的长发没有像过去那样遮住脸庞,而是清晰地分在两侧,
露出一张苍白但轮廓分明的脸。我的心跳骤然停了一拍,紧接着疯狂地撞击着胸腔。
那张脸…尽管只在校史馆模糊的旧合照里见过一次,但我绝不会认错——是林晚!
退学的林晚学姐!她的眼睛空洞地望着镜头,嘴角却似乎凝固着一丝极淡、极冷的弧度。
更让我浑身血液都冻住的是,照片里,她就站在陈浩的身后,近得几乎贴着他的背脊,
那双空洞的眼睛,仿佛穿透了相纸,直直地落在陈浩的后颈上。寒意顺着脊椎猛地窜上头顶。
活动室里老旧空调发出的微弱嗡鸣,此刻听起来像极了某种遥远而不祥的哀嚎。
陈浩刚才那撕心裂肺的“是她”,还有那句如同诅咒般压在我心头的——“别跟她对视,
尤其是她站在你身后时”。那是我刚加入民俗社时,上一任老社长,
一个眼神浑浊、总是沉默寡言的老头,在交接时唯一反复叮嘱的话。
当时只觉是某种古怪的社团传说,甚至带着点黑色幽默的意味。如今,
这句话带着冰锥般的寒意,狠狠扎回我的记忆里。“行了行了,”李峰用力挥了挥手,
像要驱散某种看不见的阴霾,也像是在说服自己,“都什么年代了,还疑神疑鬼的。
肯定是图像处理的时候出了bug,把哪张老照片里的人影给叠加上去了。别自己吓自己!
散了散了,明天毕业聚餐,都收拾好心情!”他不由分说地开始收拾桌上的碎照片片,
动作有些粗暴,仿佛那些纸片烫手。其他人也如梦初醒,纷纷附和着李峰,
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轻松气氛开始收拾东西,互相打趣着离开。没人再看陈浩一眼,
也没人再碰那些散落的照片碎片。恐惧像一层无形的油膜,隔绝了彼此。陈浩依旧僵在原地,
失魂落魄,眼神空洞地望着那些碎片,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我最后一个离开,
轻轻带上了活动室那扇沉重的木门。门合拢的瞬间,
我似乎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压抑的、如同困兽般的呜咽,又或许,只是老旧门轴发出的呻吟。
走廊的声控灯应声熄灭,黑暗瞬间吞噬了身后的一切,只留下那扇紧闭的门,
像一块冰冷的墓碑。---回到宿舍,身体陷进椅子里,
心却还在活动室那片狼藉的照片碎片上漂浮。林晚那张清晰的脸,陈浩崩溃的嘶吼,
老社长那句如附骨之疽的低语……混乱的碎片在脑子里疯狂碰撞。不对劲。
不仅仅是那张照片。我猛地坐直身体,
手指有些发颤地点开电脑里名为“民俗社归档”的文件夹。
里面按年份分门别类存放着社团历年活动的照片、通讯稿和记录。我深吸一口气,
点开了“毕业合照”子目录。从2015年开始,一年一张。鼠标滚轮滚动,
屏幕的光映着我越来越苍白的脸。2015年,社团初创,照片里只有寥寥七八个人,
背景是旧图书馆的爬山虎墙。就在照片最右侧靠近边缘的地方,
紧挨着一个当时戴着眼镜的瘦高男生,有一小块区域色调明显不对。那不是模糊,
更像是一团被强行涂抹、试图掩盖的污渍,但仔细分辨,隐约能看出一点蓝色的裙角痕迹,
突兀地悬在那里,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2016年,照片在校园湖畔拍的。
这次清晰了一些,但依旧刻意处在焦外。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身影,
侧身站在人群最后方柳树的阴影里,长发垂落,完全遮住了脸,只能看到一只苍白的手,
扶着粗糙的树干。2017年,合照地点是教学楼天台。那个蓝裙身影的位置更靠前了一点,
站在了队伍斜后方的角落。风似乎吹起了她的长发,照片像素不高,但能感觉到发丝缝隙间,
似乎有一线冰冷的目光透出来,正看向前排中央——那时担任社长的人,
正是后来退学的林晚学姐。我的鼠标停在了2018年的合照上。照片里,前排中间的位置,
原本应该属于林晚学姐的地方,空了出来。她退学了。而那个蓝裙身影,
如同一个无声的填补者,悄然移动到了后排,
正站在当时刚接任社长的陈浩身后一步之遥的位置。长发依旧遮面,但身体前倾的姿态,
带着一种无声的压迫感。冷汗顺着额角滑落。我几乎是屏着呼吸,点开了2019年的合照。
照片背景是学校大礼堂。前排,属于一位名叫张锐的学长的位置,空空如也。
他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蓝裙身影的位置再次向前移动,几乎与后排社员平行,这次,
她直接站在了陈浩的正后方,距离近得仿佛她的裙摆已经贴上了陈浩的裤脚。2020年,
2021年,2022年……每一张毕业合照,都对应着一个“缺席者”。因病休学的学姐,
家中突发变故紧急退学的学弟……他们的名字和空位,
在每年的社团通讯稿里被轻描淡写地提及,如同被橡皮擦轻轻抹去。而那个蓝裙的身影,
如同一个沉默的、步步紧逼的幽灵,在每一年的合照中,位置都悄然向前挪动一小步,
距离前排中央的社长陈浩越来越近。她的轮廓在相机技术进步下似乎“清晰”了,
但那张脸始终被浓密的长发覆盖,像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又像是一把悬在头顶、缓缓落下的铡刀。直到2023年,也就是今年。她的脸,
终于毫无遮挡地暴露在镜头下——林晚。
一个冰冷、残酷、不容置疑的规则在我脑海中轰然成型:民俗社每年的毕业照,
必须缺席一个人。而那个蓝裙的“她”,则踏着这一个个被抹去的名字和空位,
如同踏着一级级无形的阶梯,一年,一步,终于走到了陈浩的身后。
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紧心脏。这绝非巧合,更不是什么相机故障!这是一种仪式,
一场以毕业照为祭坛、以社员生命为牺牲的、缓慢进行的献祭!而陈浩,
这个一直站在前排中央的人,他显然是知情者!他恐惧的不是照片本身,
而是照片里“她”的位置!当“她”最终站在了他身后,清晰露出林晚的脸时,
他彻底崩溃了。老社长那句“别跟她对视,尤其是她站在你身后时”,
根本不是什么古怪的告诫,而是用血写就的警告!是幸存者用尽最后力气发出的哀鸣!
“她”来了。她站在了陈浩的身后。那么,接下来呢?规则之下,
今年“缺席”的位置已经确定。那个位置,属于陈浩。
---档案室在行政楼最偏僻的西翼尽头。厚重的橡木门推开时,
一股混合着陈年纸张、灰尘和霉菌的气息扑面而来,呛得我咳嗽了几声。
头顶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光线惨白而冰冷,勉强照亮一排排顶天立地的铁灰色档案柜,
投下重重叠叠、如同牢笼栅栏般的阴影。空气沉滞得如同凝固的胶水,
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荡,显得格外刺耳。
管理员是个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伏在门口的旧木桌上打盹。
我报出民俗社的编号,她头也没抬,浑浊的眼珠从镜片上方瞥了我一眼,慢吞吞地拉开抽屉,
摸出一把铜钥匙丢在桌上,发出“当啷”一声脆响。“B区,第三排,最底下那个柜子。
自己找,别弄乱了。”她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看完放回原处。”“谢谢老师。
”我抓起那把冰凉沉重的钥匙,快步走向档案柜的深处。B区的灯光似乎更加昏暗,
第三排柜子紧挨着墙角,散发着阴冷的潮气。我蹲下身,钥匙插入最底层那个柜子的锁孔,
转动时发出艰涩的“咔哒”声。柜门弹开,一股更浓重的霉味涌出。柜子里塞满了牛皮纸袋,
积着厚厚的灰尘。我借着手机微弱的光,
袋侧面的标签上快速划过:“民俗社活动记录…采风报告…经费申请…”年份标签模糊不清。
我耐着性子,屏住呼吸,一份份抽出来粗略翻看。灰尘在惨白的光束里狂舞,钻进鼻腔,
引发一阵阵痒意。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指尖被粗糙的纸边磨得生疼,
除了常规的会议记录和活动照片,一无所获。关于2015年的记录,
尤其是那场关键的山村采风,像是被刻意抹去了一般。
就在烦躁和失望像冰冷的潮水快要淹没我时,指尖触到一个异常厚重的纸袋。
它被塞在柜子最深处,被其他文件遮挡着。用力抽出来,沉甸甸的。纸袋是深褐色的,
比其他文件袋更旧,边角磨损得厉害,没有贴任何标签。封口处缠绕着几圈粗糙的麻绳,
打着一个死结。直觉像电流一样窜过脊背。我心跳加速,手指有些颤抖地开始解那个死结。
麻绳粗糙,勒得指腹生疼。就在绳结即将松开的刹那——啪嗒。一滴冰冷黏腻的液体,
毫无征兆地滴落在我的手背上。我猛地缩回手,手机的光束下意识地向上扫去。
档案柜顶部的阴影里,一片浓得化不开的漆黑,什么都看不见。
但那滴液体残留在我手背上的感觉异常清晰——不是水,
带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土腥味和若有若无的腐烂气息,冰冷刺骨。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头顶。
档案室里死寂无声,头顶日光灯的嗡嗡声不知何时消失了,
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和自己的心跳声在耳边轰鸣。刚才那是什么?漏水?不可能,
档案室干燥得如同沙漠!我死死盯着手背上那点浑浊的痕迹,
一股强烈的、被窥视的感觉从头顶那片黑暗中传来,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后颈上,
让我头皮发麻。顾不上许多了!恐惧反而给了我一股蛮力。我咬着牙,手指用力一扯,
终于将那个死结扯开。纸袋口敞开了。里面没有成叠的文件,只有一张折叠起来的泛黄报纸,
边缘已经脆化。还有几张用旧式胶卷相机拍摄、色彩严重褪变的照片。我抖开那张报纸。
是2015年8月28日的《临州日报》。社会新闻版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用简短冰冷的铅字印着:“本报讯:前日,我市青岩山区突降暴雨,引发局部山体滑坡。
据悉,XX大学中文系某学生社团在青岩村采风期间遭遇意外。
其中一名林姓女生20岁在暴雨中与队伍失联,疑失足坠崖。
当地救援队及村民连日搜寻,因地形复杂、天气恶劣,至今未发现失踪者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