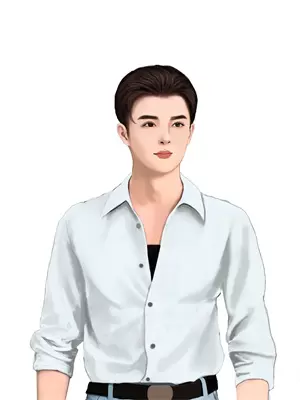
越野车碾过最后一道山梁时,林溪终于憋不住了,扭头问副驾驶座的外婆雪儿:“您总说爷爷当年用块药棉就能治病,那是真的吗?”
老人正望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桃林出神。四月的桃花开得泼泼洒洒,粉白花瓣簌簌落在她肩头,像一层柔软的雪。鬓角的银丝被山风拂起,在晨光里泛着细亮的光。每年的清明节她都会在家人的陪伴下看望他的山哥哥。
“傻丫头,”雪儿回过神,嘴角牵起浅淡的笑,“那是带状疱疹,用药棉一烧病毒就烧死了。你爷爷说“古时候没凡士林,就采些蜘蛛网糊上,一点燃病就好了”。你爷爷手巧,撕药棉都跟绣花似的。”
林溪吐了吐舌头。从小就听外婆念叨,她对爷爷的故事了解的不少——赤脚医生、艾灸治病、带村民种果树种药材,还办起农业公司、有机肥厂,甚至盖学校、搞旅游餐饮。她喜欢听外婆讲那些过往,暖暖的,像晒过太阳的棉布,温暖且有力量。
“爷爷的爸爸,您说的那位二爷,真的是军医吗?”林溪放慢车速。前方岔路口立着块指示牌,“桃花峁村史纪念馆”八个红漆大字在桃林中格外醒目。
雪儿没立刻回答,推开车门走了下去。她望向远处最高的山峰,山顶云雾缭绕,思绪像是回到了几十年以前:“二爷年轻时在战场上救过好多人,子弹从耳朵边擦过去都不眨眼。”
林溪跟着她踏上“守山步道”。石板路是景区特意修缮的,路边每隔一段就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守山当年行医和带领村民创业的故事。
雪儿的脚步有些慢,却很稳:“二爷本名叫啥,我也记不清了,村里人都这么喊他。”她的声音如春风沐浴般轻柔:“他年轻时有个相好的,叫春杏,是邻村的教书先生。那年头打仗,民不聊生,二爷想挣钱买一对银镯子下聘礼,就跟着部队走了,临走前跟春杏说,等打完鬼子就回来娶她。”
老人停下脚步,扶着石刻望向山下:“春杏姑娘等了三年,后来听说二爷所在的连队,攻打鬼子炮楼时……全军覆没了。”
山风突然大了些,几片粉红的花瓣落在雪儿银发上,像停落的蝶翼。
“春杏姑娘不信啊,揣着二爷临走给的手帕,步行几百里去了战场。”雪儿的声音有些放低,“战场啥样?尸横遍野,好多人都辨不清模样。她找了三天三夜,没找到二爷的尸体,只在被炸塌的战壕里,捡到顶印着二爷名字的军帽——原本磨得发亮的帽徽,被血染成了褐红色。”
林溪的心猛地一揪。她听妈妈说过,二爷回村后,腰上总别着顶旧军帽,谁也不让碰。
“她以为二爷没了,回来就病倒了,没熬到冬天就走了,临终了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顶帽子。”雪儿蹲下身,捡起一片完整的桃花瓣,“后来二爷活着回来了,穿着打满补丁的军装。听说春杏没了,他就把那顶帽子挂在腰上,再也没取下过。往后谁提娶亲,他就把人往门外推。”
林溪这才明白,景区那棵千年老槐树旁,为啥立着“望夫槐”的石碑。那是二爷坟头自己长出的一棵国槐,树冠没有长成圆形,倒像顶翠绿的军帽,帽檐正对着春杏所在的村子。原来传说里,藏着这么一段让人揪心的过往。
“有人说二爷傻,劝他再找个媳妇,他总说‘我命里有个孩子’。”雪儿站起身继续往上走,“他懂中医,还会些奇门遁甲,给自己卜了一卦,说命里有个孩子。大家都当他想春杏想糊涂了,谁能想到,那年冬天他上山采药,真在雪窝里捡到了你爷爷。”
石板路尽头是片平整的空地,中间立着座朴素的石碑,刻着“守山之墓”四个字。碑前放着束新鲜桃花,显然是今早刚有人来过。雪儿走上前,用衣角轻轻擦去碑上的浮尘,动作温柔得像在抚摸一件珍宝。
“你爷爷刚出生就被爹妈扔了,因为小儿麻痹。”她的声音带着哽咽,“二爷把他抱回来,用草药擦身子,喂汤药,硬是把你爷爷从鬼门关里拽了回来。后来,背着他上山认药草,教他把脉识病,开方救人。你爷爷聪明,二爷教的一学就会,尤其是针灸,手指头比姑娘绣花还准。”
林溪看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男人笑得温和,眼神里有种让人安定的力量。
雪儿望着照片,轻轻叹了口气:“你爷爷把一辈子都给了桃花峁。”她指向山下:“以前村里不是窑洞就是土坯房”。如今已成了热闹的景区,民宿、农家乐错落有致,白墙灰瓦在桃林里若隐若现。
阳光穿过桃林,在墓碑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雪儿从布包里拿出一小捆晒干的艾草放在碑前,艾草的清香混着桃花的甜香,在山风里慢慢弥漫开。她坐在坟前,掏出手绢擦拭着照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目光落在碑角那行小字上——“爱妻雪儿敬立”。山风又起,吹动她鬓角的银丝,也吹动了碑前那束桃花,花瓣簌簌落下,像一场无声的祭奠。
雪儿坐在守山坟前,掏出手绢轻轻擦拭着守山的照片,陷入了深深地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