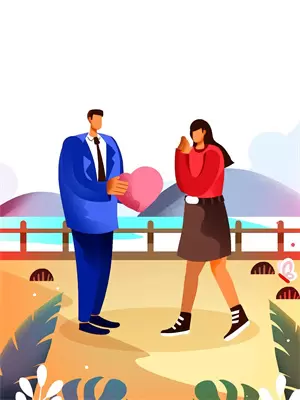
婆家拆迁款下来那天,我被告知一分钱也没有。我没争没吵,默默租了套公寓,
离开了那个家。他们以为我走了就一了百了,再无瓜葛。谁知婆婆急性病发入院,
小姑子火速打来电话。“嫂子,妈没人照顾,你快回来啊!”她语气焦急又理所当然。
我盯着手机,任由它响了一遍又一遍。我享受着这份久违的清净,丝毫不为所动。
01客厅里的空气是凝固的,带着一股陈年家具和人心算计混合在一起的腐朽味道。
墙上那台老旧的挂钟,秒针每一次跳动,都像是在我紧绷的神经上敲击一下。
我坐在沙发最靠边的角落,一块磨损到露出线头的区域,
这里是我在这个家八年来的专属位置。婆婆王秀清了清嗓子,那双浑浊的眼睛扫过每一个人,
最后停留在我身上,带着一种审判般的高高在上。“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为了拆迁款的事。
”她端起面前那只印着红牡丹的搪瓷杯,杯沿磕碰得斑斑驳驳,就像她这个人,
外表看着传统,内里全是算计。“这老房子,是我和你爸一辈子的心血,是老陈家的根。
”“现在拆迁了,这笔钱,自然也该是我们老陈家的人分。”她顿了顿,那句话终于来了,
像一把淬了毒的钝刀,直直插进我的胸口。“小琴,你一个外人,嫁进来也没生个一儿半女,
这钱,你就别想了。”她的语气那么平淡,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可每一个字,都砸得我头晕目眩。我下意识地看向我的丈夫,陈伟。他坐在婆婆身边,
那个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位置,此刻却把头埋得很低,专注地研究着自己运动鞋上的一个污点,
仿佛那里藏着宇宙的奥秘。他不敢看我。坐在他对面的小姑子陈娜,
嘴角已经抑制不住地向上扬起,那双画着精致眼线的眼睛里,全是幸灾乐祸的光芒。
她甚至冲我挑了挑眉,那是一种胜利者的炫耀。胸口闷得发慌,
像被一整块潮湿的水泥板压住,呼吸都变得困难。八年。整整八年。我嫁进陈家,
带来的三十万嫁妆,填了他们家买这套老破小欠下的窟窿。我每个月的工资,
一半以上都用作了家庭开销。王秀隔三差五的头疼脑热,是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
陈娜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两年,一日三餐是我变着花样伺候。
就连那个不争气的赌鬼小叔子陈雷,在外面欠了钱被追债,也是我拿出自己存的私房钱,
帮他还了一次又一次。我以为我捂热了这块石头。
我以为我用八年的付出演成了一个“模范儿媳”。到头来,在三百万拆迁款面前,
我只是一个“外人”。一个连名字都不配出现在分配协议上的外人。
我没有像他们预想中那样哭闹、争吵、撒泼。没有。在极致的背叛面前,
一种诡异的平静笼罩了我。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窗外马路上汽车开过的声音,
邻居家小孩的哭闹声。世界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清晰,唯独他们一家人的嘴脸,
在我眼前开始模糊。我只是很轻地开口,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客厅里的每个人都听见。
“陈伟,你也是这个意思吗?”我的声音很稳,稳到我自己都感到陌生。
陈伟的身体僵了一下,他终于抬起头,但视线却飘忽着,就是不落在我脸上。
“小琴……妈……妈说得对。”他的声音含混不清,像嘴里含着一团棉花。
“这钱……确实……确实跟外人没关系。”“外人”两个字,从我丈夫的嘴里说出来,
比从婆婆嘴里说出来,还要锋利一万倍。它彻底斩断了我心中最后一丝摇摇欲坠的期望。心,
在那一瞬间,彻底死了。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爱了十年,嫁了八年的男人,
他脸上的懦弱、躲闪和愧疚,交织成一张让我无比恶心的面具。“好。”我只说了一个字。
“我明白了。”说完,我站起身,没有再看他们任何一个人,径直走回了我们的卧室。身后,
客厅里短暂的沉默被打破。王秀得意的声音传来:“看吧,她也知道自己没理,闹不起来。
”陈娜兴奋地尖叫:“妈!三百万啊!我们快商量商量怎么花!我要买那个最新款的包!
还要去欧洲旅游!”“你这孩子,就知道花钱!你哥还没说话呢!”“哥,你想干嘛?
换辆好车?”他们的欢声笑语,像无数根烧红的针,透过门缝刺进我的耳朵。但奇怪的是,
我感觉不到疼了。心死了,就不会疼了。我打开衣柜,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是的,
我早有预感。在这个家里,当利益大到一定程度时,我这个外人,一定会被第一个牺牲掉。
我只收拾自己的东西。我买的衣服,我买的书,我买的化妆品。那些我为这个家添置的,
大到冰箱彩电,小到一双碗筷,我一件都没碰。就当是喂了狗。我提前在外面租好了公寓,
不大,但干净,属于我自己。深夜,我拖着行李箱,客厅里已经没了动静,
只有此起彼伏的鼾声。他们做着发财的美梦,沉沉睡去。我没有开灯,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付出了八年青春的地方。没有留恋,只有厌恶。
我轻轻带上门,门锁“咔哒”一声,像是为我的过去,画上了一个句号。转身的瞬间,
我没有回头。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我深吸一口气,
肺里充满了自由的空气,仿佛卸下了压在身上八年的千斤重担。李琴,你的人生,
从这一刻起,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我对自己说。抵达新公寓,我打开所有的灯,
把小小的空间照得通亮。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很硬,但很安心。没有眼泪,
只有一种久违的轻松与解脱。我发誓,从今往后,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践踏我的尊严。
02新生活的头三天,是极致的清净。我的世界里,第一次只剩下我自己的声音。
早上七点自然醒,阳光透过没拉严的窗帘洒在脸上,暖洋洋的。我不用再像个陀螺一样,
冲进厨房准备一家四口的早餐。我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烤了两片吐司,坐在小小的阳台上,
看着楼下车水马龙,慢悠悠地吃完。这种感觉,奢侈得不像话。我换了一份新工作,
是我一直想去的行业,薪水比以前翻了一倍。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对我的专业能力很认可,
那份久违的自信,一点点回到了我的身体里。我开始重新打扮自己,
穿上以前被王秀念叨“太暴露”的裙子,化上精致的妆容。镜子里的那个女人,眼神清亮,
面带微笑,陌生又熟悉。这三天,陈家没有一个人联系我。我猜,在他们眼里,
我大概只是在闹脾气,耍性子。他们笃定,像我这样逆来顺受惯了的女人,
在外面撑不了几天,就会自己灰溜溜地滚回去,继续当他们的免费保姆。
这种被彻底无视的感觉,非但没有让我难过,反而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离开,
是多么正确。第四天下午,我正在公司处理一份紧急的报表,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
我皱了皱眉,按了接听。“嫂子!”是小姑子陈娜,她的声音尖锐又急促,
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命令口吻。“妈急性胰腺炎住院了!你快回来啊,医院里没人照顾!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一点,掏了掏被她刺痛的耳朵。我甚至想笑。“哦?
”我语气平静无波,“跟我有什么关系?”电话那头明显愣住了,足足沉默了五秒钟。然后,
是陈娜气急败坏的咆哮:“李琴!你还是不是人!妈都这样了你还说风凉话!你有没有良心!
”“良心?”我轻轻笑出声,“我的良心,在你们宣布拆迁款没我份的时候,
就被你们全家合伙拿去喂狗了。你忘了?”“你……你……”陈娜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
我没兴趣再听她尖叫,直接挂断了电话,顺手将这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世界,
瞬间又清净了。我低头继续看报表,可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王秀,急性胰腺炎。
这种病我知道,可轻可重,重起来要人命,而且需要人寸步不离地照顾。
以陈家那几个人的德性,陈伟是个妈宝男,但指望他端屎端尿,恐怕比登天还难。陈娜呢,
更是个被惯坏的成年巨婴,油瓶倒了都不会扶的主。至于那个小叔子陈雷,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赌鬼,不来添乱就不错了。所以,他们是真的没人了。
在需要一个免费劳动力的时候,他们才想起了我这个“外人”。真是讽刺。
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陈伟的电话。我看着“老公”那两个字在屏幕上跳动,觉得无比刺眼。
我直接按了静音,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任由它执着地亮起,暗下,再亮起。
我享受着这种掌控感。以前,是他们的电话催着我回家做饭,催着我给他们办各种事。现在,
轮到他们求我了。晚上回到公寓,我洗了个热水澡,敷上面膜,窝在沙发里看电影。
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弹了出来。“小琴,是我,陈伟。”“妈真的病得很重,
医生说需要人寸步不离地照顾。我知道那天是我不对,是我混蛋,你回来吧,
家里……家里真的离不开你。”他的语气软了下来,开始打感情牌。我看着这条短信,
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王秀平日里对我颐指气使的嘴脸,
浮现出陈娜把换下来的内衣都扔给我洗的理所当然,
浮现出陈伟在拆迁款分配会上那冷漠逃避的侧脸。一幕一幕,都像是在提醒我,
我曾经活得有多卑微。我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带着一丝冰冷的嘲讽。我拿起手机,
慢悠悠地敲下一行字。“陈家不是有你,有你妈,有你妹三个人吗?
”“三百万拆迁款都分完了,照顾老人的责任,也该你们自己分清楚了。”发送。然后,
关机。世界彻底安静了。我靠在沙发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种把所有烦恼都隔绝在外的感觉,真好。03第二天,我的手机像是被设置了呼死你。
各种陌生号码轮番轰炸,我猜是陈家发动了他们所有的亲戚关系。电话接通,无一例外,
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指责。“小琴啊,我是你三姑姥姥,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婆婆病了,
做儿媳的哪有不伺候的道理?”“李琴,我是你大伯,你这样是要被戳脊梁骨的!太不孝了!
”“弟妹,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别闹脾气了,赶紧回医院吧,你婆婆都念叨你呢。
”我一概不回话,听完就挂,然后拉黑。我的内心平静得像一口古井,他们的唾沫星子,
激不起半点涟漪。对一群早就把我当外人的人讲孝道,简直是本年度最好笑的笑话。下午,
我正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买咖啡,一个熟悉的身影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是陈娜。
她眼眶通红,头发凌乱,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
“李琴!你终于肯露面了!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她一开口,
就吸引了咖啡馆里所有人的目光。“我妈在医院里躺着,生死未卜,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喝咖啡!你把我们全家拉黑,你安的什么心!”她声泪俱下,
演得那叫一个情真意切,仿佛我才是那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冷冷地看着她拙劣的表演,
任由周围的人对我指指点点。我缓缓地,一根一根地,掰开她的手指。然后,我用不大,
但足够让周围几桌人都听清的音量,平静而清晰地开口。“陈娜,第一,
我已经准备和陈伟离婚了,从法律上讲,我很快就不是你们陈家的儿媳了。”“第二,
你们家三百万拆迁款,一分钱没给我,就把我这个‘外人’扫地出门。怎么,
现在需要免费保姆了,又想起我这个‘外人’了?”“第三,王秀是你妈,不是我妈。
谁生的谁养,谁拿钱谁负责。天经地义。”我的话,像三记响亮的耳光,
狠狠地扇在陈娜的脸上。她的脸色瞬间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精彩纷呈。她没想到,
一向温顺隐忍的我,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家丑掀了个底朝天。周围的议论声,
风向立刻就变了。“哇,原来是这样啊,独吞了人家儿媳的拆迁款,
现在还想让人家回去伺候?”“这家人也太不要脸了吧。”“这姑娘做得对,凭什么啊!
”鄙夷的目光,像针一样刺向陈娜。她站在原地,手足无措,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
我端起我的咖啡,轻轻抿了一口,享受着这种反转带来的微妙快感。就在这时,
陈伟也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看到这副场景,脸色一变,上来就想拉我的胳膊。“小琴,
你别这样,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我后退一步,巧妙地避开了他的碰触,眼神冰冷。
“家?陈伟,我没有家了。在我被你们当成外人扫地出门的那一刻,就没有了。
”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只能低声下气地求我:“小琴,算我求你了,跟我去医院看看妈吧,
她情况真的很不好。”我从他的话里,捕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急切。仅仅是没人照顾,
不至于让他这么低三下四。我了解到,王秀的病情比他们说的要严重得多。急性重症胰腺炎,
并发了多器官功能衰竭,每天的住院费、治疗费就是个无底洞。而那个不争气的陈雷,
又在外面欠了一屁股赌债,把主意打到了拆迁款上。我开始暗中调查,
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他们那么急切地把我赶走,似乎不仅仅是为了独吞那笔钱。一天,
我无意中听到公司两个拆迁区的同事在议论。“听说了吗?最近有个‘拆迁款理财’的骗局,
好几个村的人都被骗了,投进去的钱血本无归!”“是啊,说是利息特别高,
结果就是个庞氏骗局,卷了钱就跑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
我立刻开始收集证据。我翻出结婚时的嫁妆清单,三十万,每一笔都有银行转账记录。
我找出这些年补贴家用的转账截图,零零总总加起来,也有二十多万。
我甚至找到了当初帮陈雷还赌债时,那个债主给我写的收条。
我还联系上了一个在拆迁办工作的远房亲戚,旁敲侧击地打听陈家拆迁款的事。我意识到,
他们现在急需我回去,除了照顾王秀,恐怕还有更深层,更致命的原因。
一个与拆迁款本身有关的,巨大的黑洞。我决定将计就计。等着他们,
自己把底牌送到我面前。04陈家的攻势,在碰壁几次后,变得更加疯狂。
他们甚至找到了我们村里的几个长辈,德高望重的那种,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电话里,
老村长语重心长:“小琴啊,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王秀再不对,
也是你婆婆,是长辈。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她不管啊。回头是岸,别让全村人戳你脊梁骨。
”我听着电话,只觉得可笑。当初他们一家人开“分赃大会”的时候,
怎么没有一个长辈出来说句公道话?现在他们家出事了,倒想起来用孝道来绑架我了。
我客气地回绝了老村长,然后通过一个律师朋友,仔细咨询了我的情况。律师明确告诉我,
我与陈伟已经事实分居,且我并未在最终的拆迁协议上签字,他们想告我“遗弃”,
根本不成立。有了法律当靠山,我的底气更足了。一个深夜,我正准备睡觉,
一个陌生的匿名电话打了进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那头,
是一个苍老又有些犹豫的声音。“是……是小琴吗?”我听出来了,是村里的老会计,
以前我帮他弄过几次孙子的电脑,对我印象不错。“张叔,是我。”“小琴啊,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谁听见,“张叔多句嘴,你可得小心。你们家那笔拆迁款,
好像……好像出了点问题。”我的心猛地一跳。“张叔,出什么问题了?”“唉,
”老会计叹了口气,“你那个婆婆王秀,真是被猪油蒙了心!她把大部分拆迁款,
都拿给你那个小叔子陈雷去还赌债了。结果你那个弟弟,不是个东西啊!他还了赌债,
剩下的钱又被人忽悠去投了个什么‘高回报项目’,结果……全被骗光了!”“现在,
钱没了,外面还欠着一屁股高利贷!那些放贷的,可都是些亡命之徒啊!”我握着手机,
手心冰凉。原来是这样。原来那三百万,根本就没在王秀手上捂热乎,
就已经被陈雷那个无底洞给败光了!他们现在不仅没钱给王秀治病,还惹上了高利贷的麻烦!
这才是他们火烧眉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我找回去的真正原因!他们需要的,
不是我的照顾。是我的钱!或者,是我的名义!我立刻想起来,当初看拆迁协议草案的时候,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除了房屋补偿款,还有一笔三十万的“家庭成员安置补贴”。这笔钱,
需要户口本上所有成年家庭成员共同签字,才能领取。而我,因为被他们提前“开除”了,
所以,我没有在那份最终的协议上签字!那三十万,就卡在了那里。这笔钱,
就是他们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想通了这一切,我只觉得一阵反胃。这一家子,
从根上就烂透了。第二天,陈伟又来了。他直接找到了我的公寓楼下,整个人憔悴得脱了形,
胡子拉碴,眼窝深陷。他看到我,再也绷不住了,几步冲上来,声音里带着哭腔。“小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