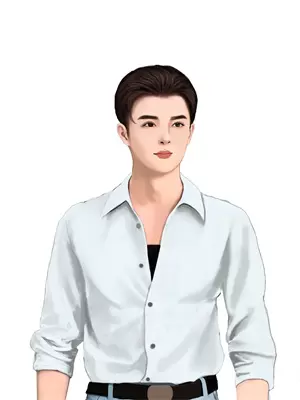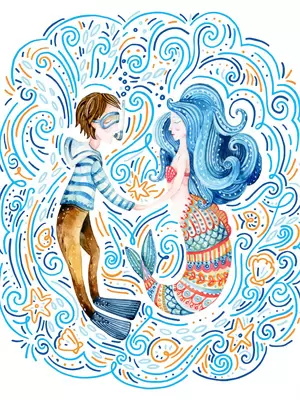
长信宫的烛火摇曳,将沈砚之的影子投在朱红廊柱上,瘦而挺,像株经冬不凋的竹。
他刚为太子讲完《资治通鉴》,正准备辞驾,却被内侍拦下:“太傅留步,陛下还有位‘小先生’要托给您。”
沈砚之眉峰微蹙。他身为帝师,除太子外从不收徒,陛下这是……
正思忖间,殿外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混着雪粒落在青砖上的簌簌声。
一个穿着月白襕衫的少年走了进来,身形单薄,墨发用根简单的木簪束着,碎发垂在颊边,遮住了半张脸。他规规矩矩地行礼,声音清越如玉石相击:“学生谢临,见过太傅。”
沈砚之的目光落在他露在外面的那只眼睛上。
那是只极漂亮的眼,瞳仁是浅琥珀色,眼尾微微上挑,带着点未脱的少年气,却又藏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锐气。像雪地里受惊的小兽,警惕,却又勾人。
“抬起头来。”沈砚之的声音平淡,听不出情绪。
谢临迟疑了一下,缓缓抬起头。
这下,沈砚之看清了他的全貌。左脸一道浅疤从眉骨延伸到下颌,破坏了原本的清俊,却奇异地添了几分桀骜。他的另一只眼似乎不太方便,被半垂的眼睑掩着,只能看到浓密的睫毛微微颤抖。
“陛下说,谢小郎君通史书,擅策论,只是无人指引。”内侍在一旁笑道,“太傅是国之柱石,定能教好这孩子。”
沈砚之没接话,只盯着谢临:“可知我授徒的规矩?”
“学生知晓。”谢临的脊背挺得笔直,“不问出身,只看资质;不徇私情,只论对错。”
“既知晓,便随我来吧。”沈砚之转身往外走,玄色官袍扫过地面,带起一阵冷香。
谢临默默跟上,落在他身后半步的距离。廊下的雪光映进来,照亮他垂着的眼,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太傅府的书房暖烘烘的,地龙烧得正旺。
沈砚之坐在紫檀木书桌后,看着站在对面的谢临。少年身形尚显单薄,却站得极稳,像株在寒风里扎了根的树。
“今日先考你《左传》。”沈砚之随手抽出一卷书,“‘多行不义必自毙’,出自何篇?讲的是何事?”
谢临几乎没有迟疑:“出自《郑伯克段于鄢》。说的是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相争,庄公纵容共叔段多行不义,最终一举除之。”
“哦?”沈砚之抬眸,“你觉得郑庄公此举,是仁,还是伪?”
这问题刁钻,寻常学子只会答“伪”,却难免落了俗套。
谢临沉默片刻,浅琥珀色的眼看向沈砚之,带着点探究:“学生以为,是权。”
“权?”
“是权衡之术。”谢临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庄公若早加约束,恐落得不容亲弟之名;若一味纵容,又恐养虎为患。他步步为营,看似不仁,实则是为郑国安靖。所谓‘仁’与‘伪’,不过是后人附会罢了。”
沈砚之握着狼毫的手指微微一顿。
这论调,竟与他年轻时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他当年藏在心里,从未宣之于口。
这少年,倒是胆大。
“有点意思。”沈砚之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再问你,若你是庄公,会如何做?”
谢临的眼亮了一下,像是找到了棋逢对手的乐趣:“学生不会等他‘多行不义’。在他请制邑时,便以‘制邑险隘,乃先王死地’为由拒之,再赐他京邑。京邑虽大,却无险可守,且离新郑更近,便于掌控。”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在空处比划,浅琥珀色的眼里闪着光,连那道疤痕都仿佛柔和了几分。
沈砚之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书房里的暖意,似乎都聚集到了这少年身上。
他教书多年,见惯了或拘谨或谄媚的学子,像谢临这样,既有才思,又带锋芒的,还是第一个。
“明日卯时,来书房早读。”沈砚之收回目光,重新看向书卷,声音恢复了惯常的清冷,“今日便到这里。”
“是,学生告退。”谢临行礼,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沈砚之一眼。
沈砚之恰好抬眸,两人的目光撞在一起。
少年的眼里带着点狡黠,像只偷看到糖的猫。而沈砚之的心头,竟莫名地漏跳了一拍。
他迅速移开目光,指尖在书页上用力按了按,才压下那点异样。
不过是个有点资质的学生罢了。
他这样告诉自己。
***谢临走后,沈砚之独自坐在书房,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簌簌地落着,像要把整个世界都埋起来。
他拿起谢临方才站过的地方的一支笔,是支极普通的狼毫,笔杆上还带着点少年的温度。
沈砚之的指腹摩挲着笔杆,目光落在窗外的雪地里。
方才谢临转身时,他分明看到,少年被遮住的那只眼,并非不便,而是……瞳仁的颜色比另一只更浅,像块蒙了雾的琥珀,在雪光下泛着奇异的光。
还有他腰间的玉佩,看着不起眼,却是前朝皇室才能用的和田暖玉。
这谢临,身世定然不简单。
沈砚之将笔放下,眸色沉沉。他向来不喜欢麻烦,可不知为何,竟对这满身秘密的少年,生出了几分探究的兴趣。
他起身走到窗边,看着雪地里那道渐行渐远的单薄身影,玄色的襕衫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却始终没有弯腰。
沈砚之的指尖无意识地收紧,心里那点异样再次翻涌上来,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漾开圈圈涟漪。
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那点不该有的心思。
沈砚之,你是太傅,他是学生。
仅此而已。
可雪地里那道身影,却像生了根,牢牢地刻在了他的眼底。
这一夜,沈砚之睡得并不安稳。梦里总有双浅琥珀色的眼,带着少年的锐与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他知道,有些东西,似乎从这个雪夜开始,变得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