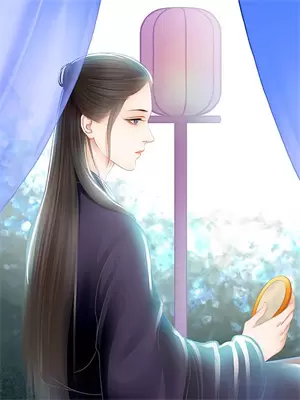第一章:冰柜里的月亮林知夏发现冰柜异常时,窗外的白玉兰正落得满地狼藉。
那是台老式双门冰柜,淡蓝色外壳早被油烟熏成灰调,
是丈夫陈砚声十年前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彼时他们刚搬进这老城区的一楼,
墙皮斑驳得能看见建国初期的砖缝,陈砚声却蹲在冰柜前笑得眉眼弯弯:“知夏,
以后咱们的夏天,都冻在这儿了。”此刻林知夏的指尖抵在冰凉的柜门上,指节泛白。
冰柜运行的嗡鸣声比往常低了半分,像人被捂住口鼻的闷哼。她刚从医院回来,
白大褂口袋里还揣着那张写着“胃癌晚期”的诊断书,油墨字迹被手心的汗洇得发皱。
本想取块冻好的杨梅缓解胃里的灼痛,却在打开柜门的瞬间,
被一股陌生的寒气裹住——不是冰块融化的湿冷,是带着金属锈味的、像冬夜河面的冷。
冰柜上层的隔板被动过了。她记得自己上周整理时,把速冻饺子排在最左边,
冻玉米垒成小堆放在中间,而现在,那片区域空出了半格,露出底下暗褐色的污渍。
更反常的是下层冷冻室,原本用来冻肉的抽屉被推得歪斜,她伸手去拉,
指尖触到一团裹着保鲜膜的硬物,形状细长,像根放大的骨头。心脏在那一秒停跳了半拍。
她扯着保鲜膜的一角往外拽,透明薄膜下透出的不是肉色,是米白色的布料,
沾着几点已经发黑的暗红。那布料的纹理她太熟悉了——是去年她给婆婆买的羊绒围巾,
婆婆总说扎脖子,却在冬至那天围着它去菜场,再也没回来。警方当初定性为走失,
说老人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症,顺着河边走丢了。陈砚声在河边守了三天三夜,
眼睛红得像要滴血,林知夏陪着他一遍遍看监控,画面里最后出现婆婆的身影,
就是围着这条米白色围巾,站在菜场出口的路灯下,像个迷路的孩子。可现在,
这条围巾裹着的东西,正沉在冰柜最底层,借着冰雾散发出若有若无的腥气。
林知夏的胃突然绞痛起来,她扶着柜壁蹲下去,额头抵在冰凉的金属上,
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冰柜里的灯是暖黄色的,却把那团东西照得像块结了冰的月亮,
冷得灼人。“知夏?”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陈砚声的声音带着惯常的温和,
还沾着点外面的烟火气,“我买了你爱吃的糖糕,刚出锅的。”林知夏猛地站起来,
手忙脚乱地把那团东西塞回冷冻室,抽屉没关好,露出一道缝隙。她转身时,
陈砚声正好走进来,手里提着油纸袋,热气从袋口冒出来,在他鼻尖凝了层薄汗。
他穿的还是那件灰色衬衫,袖口卷到小臂,
露出手腕上的旧手表——那是婆婆送他的三十岁礼物,表盘里的碎钻掉了两颗,
他却总舍不得换。“怎么站在冰柜这儿?”陈砚声走过来,自然地揽住她的腰,
手指碰到她冰凉的手背时皱了皱眉,“手怎么这么冷?是不是又胃疼了?”他的掌心很暖,
带着糖糕的甜香,可林知夏却像被烫到一样往后缩。她看见陈砚声眼底的疑惑,
那疑惑像根细针,扎在她的心上。她张了张嘴,想问“你把妈藏在哪儿了”,
想问“冰柜里的东西是什么”,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句轻飘飘的:“没什么,
想拿点冰的。”陈砚声笑了笑,伸手打开冰柜,林知夏的心跳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他熟稔地拿出冻杨梅,放在她手心:“少吃点,凉的对胃不好。
”他的手指掠过那个没关好的抽屉,随手推了推,缝隙消失在黑暗里。“今天医院怎么样?
”陈砚声拿起一块糖糕,递到她嘴边,眼神里满是关切,“医生说什么了?
”林知夏含着杨梅,冰凉的甜味压不住舌根的苦涩。她看着陈砚声的眼睛,
那双眼曾让她觉得是全世界最温柔的地方,此刻却像深不见底的潭水。她突然想起结婚那天,
陈砚声在誓词里说:“林知夏,我会永远对你坦诚,像对我自己的心脏一样。”可现在,
他的心脏里,藏着一个冰柜大小的秘密。第二章:褪色的寻人启事林知夏开始失眠。
夜里陈砚声的呼吸很轻,均匀地洒在她的后颈,像羽毛拂过,可她却觉得那呼吸里裹着寒气,
从脊椎一直窜到头皮。她不敢翻身,怕看见他熟睡的脸,
更怕自己忍不住问出那个盘旋在脑海里的问题。她开始留意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阳台的旧纸箱里,婆婆的衣服还整整齐齐地叠着,
毛衣上的起球被她用剃毛器处理得干干净净;客厅的茶几下面,压着婆婆织到一半的围巾,
毛线是宝蓝色的,是她特意选的,说要给陈砚声当新年礼物;就连冰箱门上,
还贴着婆婆写的便签,字迹歪歪扭扭:“砚声爱吃的红烧肉,冰糖要放两勺。
”一切都像婆婆只是出门买个菜,随时会推门进来,喊一声“知夏,我回来了”。
可冰柜里的那团东西,像个幽灵,总在她闭眼时浮现。她开始偷偷观察陈砚声,
看他上班前是否会检查冰柜,看他做饭时会不会避开那个冷冻抽屉,看他提到婆婆时,
眼底的悲伤是不是真的。周三下午,陈砚声说要去公司加班,林知夏看着他出门的背影,
转身冲进厨房,打开了冰柜。这次她没有犹豫,直接拉开那个抽屉,把那团东西抱了出来。
保鲜膜裹了三层,她一层层地撕,手指被冰冻得发麻。当最后一层保鲜膜落下时,
她倒吸一口凉气——那不是她想的“尸体”,是一件叠得整齐的羽绒服,米白色的,
正是婆婆失踪时穿的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她伸手去掏,摸出一个老旧的钱包,
里面夹着婆婆的身份证和一张皱巴巴的寻人启事,就是去年他们贴遍整个城区的那张。
寻人启事上的照片,婆婆笑得很慈祥,眼角的皱纹里都透着暖意。可钱包最里面,
还夹着一张纸条,是陈砚声的字迹,她太熟悉了——“妈,对不起,我不能让你毁了知夏。
”林知夏的手指颤抖着,纸条上的字迹像是活过来一样,钻进她的眼睛里,刺得她眼泪直流。
她突然想起去年冬至前的那天,婆婆突然把她叫到房间里,塞给她一张银行卡,说:“知夏,
这是妈攒的养老钱,你拿着,赶紧跟砚声离婚。”她当时愣住了,问婆婆为什么。
婆婆的眼睛红得吓人,说:“他不是好人,他心里藏着事,会害了你的!”她还想说什么,
陈砚声就推门进来了,笑着问她们在聊什么,婆婆立刻闭了嘴,眼神躲闪着,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那时候她只当婆婆是年纪大了,胡思乱想,还安慰陈砚声,
说妈只是太担心他们了。可现在,看着这张纸条,她才明白,婆婆说的是真的。
羽绒服的袖口上,沾着一块深色的污渍,她凑近闻了闻,是汽油的味道。
她突然想起去年冬至那天,城郊的废弃工厂着了场大火,新闻里说火势很大,烧了整整一夜,
没有人员伤亡。当时陈砚声还跟她说:“还好没人,不然太可怜了。”林知夏抱着羽绒服,
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冰凉的瓷砖透过薄薄的家居裤,冻得她骨头疼。
她想起陈砚声的反常——婆婆失踪后,他从不去城郊;家里的汽油桶,总是放在车库最里面,
用布盖得严严实实;他手机里的相册,关于婆婆的照片,从去年冬至后,就再也没更新过。
胃又开始疼了,比之前更剧烈,像有把刀在里面搅。她摸出医生开的止痛药,
倒了两粒塞进嘴里,没喝水,干咽下去。药片卡在喉咙里,苦得她直皱眉。“知夏?
”门口传来陈砚声的声音,林知夏吓得手一抖,羽绒服掉在了地上。她慌忙站起来,
想把羽绒服塞回冰柜,可已经来不及了——陈砚声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提着刚买的菜,
看见地上的羽绒服,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陈砚声的声音发颤,
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慌乱,“你怎么把它拿出来了?”林知夏看着他,
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陈砚声,妈到底在哪儿?”陈砚声的身体晃了晃,他放下手里的菜,
一步步走近,想伸手抱她,却被林知夏推开了。她后退一步,
指着地上的羽绒服:“这衣服上的汽油味,还有你写的纸条,城郊的大火……陈砚声,
你告诉我,妈是不是不在了?”陈砚声的肩膀垮了下来,他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
发出压抑的呜咽声。那声音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绝望又痛苦。林知夏看着他,
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得喘不过气。“是,”陈砚声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
“妈不在了……去年冬至,她就不在了。”第三章:火里的秘密陈砚声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杯冷水,却没喝。他的脸色还是很白,眼底的红血丝像蜘蛛网一样蔓延。
林知夏坐在他对面,手里攥着那张纸条,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去年冬至前,
妈查出了肺癌,晚期,”陈砚声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医生说,
最多还有三个月。她不想治,说浪费钱,还说……还说要跟你说件事。
”林知夏的心一紧:“什么事?”“她说,她年轻的时候,跟一个男人好过,生了个孩子,
”陈砚声的声音有些颤抖,“那个孩子,不是我。”林知夏愣住了,她看着陈砚声,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砚声是独生子,这是她从结婚那天就知道的,婆婆也总说,
陈砚声是她的命根子。“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陈砚声苦笑了一下,眼底满是自嘲,
“妈说,那个男人是个赌鬼,后来欠了高利贷,跑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没办法,
就把孩子送了人,然后嫁给了我爸。我爸不知道这件事,一直以为我是他的亲生儿子。
”林知夏张了张嘴,想问什么,却被陈砚声打断了。“妈说,她送人的那个孩子,
后来找到了她,”陈砚声的声音沉了下去,“那个孩子叫张强,是个混社会的,
知道妈有积蓄,就来要钱。一开始是几千,后来是几万,妈把养老钱都给了他,他还不满足,
说要找你,找我们家的麻烦。”林知夏的后背冒出一层冷汗,她想起去年秋天,
有个陌生男人在医院门口拦住她,问她是不是陈砚声的老婆,眼神里的恶意让她很不舒服。
当时她以为是医闹,没在意,现在想来,那个男人就是张强。“妈怕他伤害你,
”陈砚声看着林知夏,眼底满是愧疚,“她跟张强约在城郊的废弃工厂见面,
说要给他最后一笔钱,让他以后别再来找我们。我不放心,偷偷跟了过去。
”他的声音开始发颤,像是在回忆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