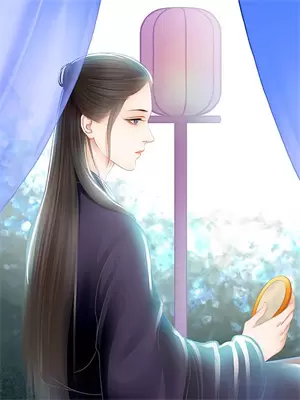死者是一名3个月大的女婴,发现尸体的地方就在他们家旱厕的粪池。我赶到的时候,
孩子的父母和外婆泣不成声,一旁聚满了看热闹的人,不远处,
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躲在大人身后,投来好奇的目光。很久以后再次回忆这幅画面,
我仍会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杀死女婴的真凶当时就在我的眼前,还骗过了所有人!
那时候我还是个愣头青,带我的师傅是个老民警,姓吴,我叫他吴叔。报警的女人叫赵兰,
家住核桃峪村,村子嵌在秦岭余脉的山沟里,四周全是高高低低的山,
一条窄路顺着山根绕进村里。赵兰的家在山腰的平地上,周边稀稀拉拉住着几户人家,
房子多是土坯墙加木梁顶,墙根爬满青苔,看着就有些年头。这里太偏了,
虽说前两年通了电,但自来水管道还没铺过来,家家户户只能接着用旱厕。所谓旱厕,
就是在地底下埋个半人高的粪缸,上面搭两块裂了缝的旧木板,勉强能站人。没法冲水,
也没下水道,粪缸里常年堆着污秽,夏天招满苍蝇,冬天冻成黑硬块,开春化冻后,
腥臭味能飘出半里地,蛆虫在里面钻来钻去,看得人头皮发麻。女婴的尸体,
就是从这样一口粪缸里捞出来的。发现尸体的是孩子的母亲赵兰。10月8日晚上,
她打着手电去上厕所,灯光扫过粪池时,
突然瞥见水里漂着个亮闪闪的东西——是她给孩子打的银锁片,上面还刻着“平安”两个字。
她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赶紧找了根竹竿,在浑浊的池子里扒拉,没一会儿,
一团紫黑色的东西浮了上来。她看清那是孩子的小衣服后,
尖叫一声就昏了过去——那团发臭的东西,正是她失踪了六天的女儿。赵兰之前报过案,
说她刚满三个月的女儿不见了,怀疑是被前夫孙强拐走的。女儿失踪那天,
也就是10月2日,好赌成性的孙强找上门借钱,还放狠话说不给钱就把孩子卖到外地。
那时候村里常有陌生人晃悠,治安不算好,赵兰知道孙强混不吝,只能答应给钱。
她让母亲留下看孩子,自己去乡上取钱,可等她回来,只看见母亲坐在地上哭,
孙强和孩子都没了影。赵兰的母亲刘老太有个习惯,每天下午都要去屋后的坡地里摘菜,
来回大概10分钟。那天她想着赵兰都答应给钱了,孙强总不至于对孩子下手,
就放心去了菜地,可回来时,摇篮是空的,孙强也没了踪影。那时候抓人全靠腿跑,
再加上孙强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案子一直没进展。就在大家到处找孙强的时候,
孩子的尸体从旱厕里捞了出来,所有人都觉得是孙强干的——肯定是他没拿到钱,
或是怕被缠上,就把孩子扔进粪缸淹死了!可细想又不对,赵兰都答应给钱了,
再说“虎毒不食子”,他再混,也不至于杀自己的孩子。即便有疑点,
孙强还是成了头号嫌疑人。局里把这案子当成重点,加派了人手,我和吴叔赶到现场时,
吴叔盯着人群看了半天,突然说:“别总盯着那些看着像坏人的人,有时候,
看着越老实的人,越藏着事,凶手说不定就在这院子里。
”案子就卡在刘老太离开的10分钟里,这10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查真相,
就得把这段时间的事捋清楚。现在孩子的尸体送去过尸检了,吴叔带着我挨家问,
想找出点蛛丝马迹。眼下,赵兰还昏着没醒,刘老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只有赵兰的现任丈夫马国梁还算冷静,红着眼帮着招呼人。之前我们了解过赵家的情况,
因为赵兰一口咬定是孙强干的,所以搜查重点一直是找孙强。马国梁看着就像个老实人,
三十五岁左右,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他以前在县城的采石场干活,
后来被石头砸伤了腿,走路有点跛,就回村种玉米了。今年开春,
经人介绍认识了从外地回来的赵兰,两人都觉得合适,没多久就领了证。“马国梁,
你再说说10月2日那天,你都在哪?”吴叔递了支烟过去。马国梁接过烟,头一直低着,
眼睛盯着鞋尖,手指把烟嘴搓得变了形:“那天我一直在村西头的玉米地里收玉米,
天快黑了才回家。一进门就看见门口停着警车,赵兰趴在地上哭,后来才知道孩子没了,
警官。”我把他的话记在本子上,和上次问的一模一样。吴叔没说话,自己点了根烟,
又把打火机递给他:“抽一口吧,烟嘴都要被你搓烂了。”马国梁手一抖,接过打火机,
试了三次才把烟点着。不知道是不会抽烟,还是太紧张,他猛吸一口就呛得咳嗽,就算咳嗽,
头也没抬,眼睛一直盯着地面。没一会儿,烟就抽到了头,他抬起脚,
把烟头在鞋底使劲摁灭——上次问他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的,鞋底上还留了个黑印。
“警官,要是没别的事,我去看看赵兰醒了没。”他声音很小,透着小心翼翼。吴叔摆摆手,
马国梁松了口气,一瘸一拐地走了。吴叔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说:“他在撒谎。
”我愣了一下,没明白:“他说的和上次一样,不像撒谎啊?”吴叔抬起脚,
把自己的烟头在鞋底摁灭,指了指马国梁刚踩过的地方:“你忘了?
10月2日下午下过小雨,玉米地里全是泥,他说自己在地里收了一下午玉米,
回来的时候鞋底怎么会这么干净?”我突然反应过来,
后背一下子冒了冷汗——那天的雨虽说不大,但地里肯定泥泞,走一趟鞋底必然沾泥,
可马国梁的鞋底,干净得像刚刷过一样!2我攥着本子的手猛地收紧,
指节泛白——刚才光顾着听马国梁说话,竟没细想这茬。10月2日下午的雨虽小,
但村西头的玉米地是坡地,土黏得很,踩一脚能沾半斤泥,可马国梁的布鞋鞋底,
除了之前摁烟留下的黑印,连半点泥星子都没有。“不光是鞋。”吴叔吐了口烟,
目光扫过院子角落的柴房,“他说收了一下午玉米,你见他晒玉米的竹筐了吗?
还有身上的衣服——收玉米要钻玉米地,袖口、裤脚总会挂点玉米叶的碎渣,
他身上的褂子倒是干净得很。”我顺着吴叔的目光看去,柴房门口堆着几根枯柴,别说竹筐,
连个装玉米的麻袋都没有。再回想马国梁刚才的样子,他的蓝布褂子确实平整,
袖口连点褶皱都少,更别提玉米叶了。正说着,屋里传来刘老太的哭声,
夹杂着赵兰微弱的呻吟——看来赵兰醒了。我们刚要进屋,
就见马国梁端着一碗水从灶房出来,看见我们,手又是一抖,碗里的水溅出几滴,
落在他的布鞋面上。他慌忙用袖子去擦,眼神躲闪:“吴警官,你们还没走啊?赵兰刚醒,
说想喝水。”吴叔没接话,反而盯着他的手:“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弄的?”我这才注意到,
马国梁的右手虎口处有一道浅疤,结着新痂,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划的。
马国梁下意识地把右手往身后藏,声音低了几分:“没、没什么,
收玉米的时候被玉米杆划到的。”“玉米杆划的?”吴叔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沉了些,
“玉米杆的茬子是钝的,划不出这么尖的伤口。倒像是……被竹筐的篾条划的?
”马国梁的脸“唰”地白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吴叔又指了指他的鞋:“10月2日下午,你到底去哪了?
别跟我说玉米地——村西头的老王家,那天也在收玉米,他说从早到晚没见着你半个影子。
”这话像块石头砸在马国梁身上,他踉跄着后退一步,靠在了灶房的门框上,脸色从白转青。
刘老太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看见马国梁这副模样,突然尖叫起来:“是你!
是你把娃藏起来的是不是?!”马国梁猛地抬头,眼神里满是慌乱,却还想辩解:“我没有!
你别胡说!”“胡说?”吴叔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半片撕碎的蓝布,
“昨天我们在旱厕旁边的草从里捡到的,这布的料子,跟你身上穿的褂子一模一样。
还有这上面的污渍——法医说,是粪缸里的污水渍。”吴叔的话像根针,扎得我后颈发紧。
马国梁的脸瞬间没了血色,端着碗的手晃得更厉害,水顺着碗沿往下滴,
在青石板上砸出一小片湿痕。他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完整的话:“老、老王看错了吧?
我……我那天确实在玉米地,就是换了块地,没在他旁边……”“换了块地?
”吴叔往前挪了半步,目光像钉一样锁在他身上,“村西头就那两片玉米地,
除了老王家旁边的,另一块上个月就收完了,秸秆都还在地里堆着。你倒是说说,
你去哪块地收的玉米?”马国梁的喉结滚了滚,眼神往院门外瞟,
像是想找机会脱身:“我、我记不清了……那天头有点晕,可能记错了……”“记不清了?
”吴叔突然提高了声音,“你媳妇的娃丢了,你说你收玉米记不清地?
你手上的伤也记不清了?”这话一落,马国梁猛地攥紧了碗,指节泛白。
刘老太从屋里跑出来,看见这架势,哭着扑过来拉马国梁:“警官,国梁是老实人,
他不会干坏事的!肯定是你们弄错了!”马国梁借着刘老太拉他的劲,往后退了一步,
顺势把碗放在旁边的石磨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吴警官,我真没撒谎,
那天我就是在地里忙活,可能回来的时候换了双鞋,所以鞋底干净……”“换了鞋?
”我突然插了句嘴,想起刚才吴叔说的话,“那你换下来的旧鞋呢?
沾了泥的鞋总该有地方放吧?”马国梁的身子僵了一下,
眼神飘向柴房:“扔、扔柴房了……那天回来嫌脏,就换了鞋,
旧鞋还没来得及刷……”吴叔没等他说完,转身就往柴房走:“既然在柴房,那就去看看。
”马国梁脸色更白了,赶紧上前想拦:“别、别去了吴警官,柴房又脏又乱,
没什么好看的……”他的手刚碰到吴叔的胳膊,就被吴叔甩开了。我们跟着吴叔走进柴房,
里面确实堆满了枯柴和杂物,光线昏暗,一股子霉味。吴叔的目光在柴房里扫了一圈,
最后落在墙角的一堆干草上——那堆干草看着像是刚挪过,边缘还露着半截布鞋的鞋尖。
吴叔走过去,用脚拨开干草,一双沾着泥的黑布鞋露了出来。我凑近一看,
鞋底的泥是深褐色的,还沾着几根枯草——这枯草的样子,和旱厕旁边长的那种一模一样,
根本不是玉米地里的草!“这就是你换下来的旧鞋?”吴叔拿起鞋子,递到马国梁面前,
“鞋底的泥是旱厕边的黏黄土,不是玉米地的沙壤土。还有这草——你说说,
你在玉米地里收玉米,怎么会沾上旱厕边的草?”马国梁盯着鞋子,嘴唇哆嗦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刘老太在旁边看着,哭声突然小了,眼神躲闪,双手不自觉地绞在一起。
吴叔把鞋子放在地上,又看向马国梁的右手:“你说伤是玉米杆划的,可这伤口边缘整齐,
明显是被硬东西划的。旱厕旁边有个破竹筐,筐沿的篾条断了几根,
尖得很——要不要我们去比对一下,看看能不能对上你伤口的形状?”马国梁的腿一软,
差点坐在地上,全靠刘老太扶着才站稳。他的头垂得更低,
声音细若蚊蝇:“我……我……”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是村里的治保主任,
手里拿着个塑料袋:“吴警官,你们要的东西我找到了!昨天在旱厕旁边的沟里,捡到这个!
”我们走出柴房,治保主任递过塑料袋——里面装着半块蓝色的布片,布片边缘毛糙,
像是被撕扯下来的,上面还沾着点褐色的污渍。我一眼就认出来,这布的颜色和质地,
跟马国梁身上穿的蓝布褂子一模一样!吴叔接过塑料袋,举到马国梁面前:“这布片,
是你褂子上的吧?”马国梁猛地抬头,眼睛里满是惊恐,张了张嘴,却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阳光照在他脸上,能清楚地看到他额头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
3吴叔捏着塑料袋的手指轻轻摩挲,没有再追问,
反而转头对治保主任说:“麻烦你把这布片收好,等下跟我们回所里做个比对。” 说完,
他看了眼马国梁,语气平淡:“你先照顾赵兰,我们晚点再来找你。”马国梁愣在原地,
像是没料到吴叔会突然松口,直到我们走出院门,他还保持着僵立的姿势。我跟在吴叔身后,
忍不住问:“叔,怎么不接着问了?证据都快对上了。”“急什么。”吴叔往村口走,
目光扫过路边的几户人家,“现在问,他只会硬撑。咱们先去问问邻居,
看看10月2日那天,还有谁见过马国梁。”我们先去了隔壁的李家。
李婶正在院子里晒豆子,看见我们,赶紧放下手里的簸箕:“吴警官,
是为了赵家娃的事来吧?唉,真是造孽。”“李婶,10月2日下午,你见过马国梁吗?
”吴叔递过去一杯水。李婶皱着眉想了想:“2日啊……那天下午我在门口择菜,
好像看见他往村东头走了,手里还拎着个黑布包,不是去西头的玉米地方向。”“黑布包?
”我赶紧记下来,“大概几点?”“差不多两三点吧,那时候天还没阴,后来才下的雨。
”李婶补充道,“对了,他走得挺急,我跟他打招呼,他都没应,头低着就过去了。
”离开李家,我们又去了村东头的小卖部。店主王大爷说,10月2日下午三点多,
马国梁来买过一包烟,还有一捆细麻绳。“他平时不怎么买烟,那天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付了钱就走了。”王大爷回忆道,“对了,他走的时候,
我看见他往村后的坡地去了——那地方离赵家的旱厕不远。”细麻绳?我心里咯噔一下,
看向吴叔,他眼底也多了几分凝重。我们顺着村后的坡地往旱厕走,
坡上的草被踩出一条浅痕,走到一半,吴叔突然停住脚,
蹲下身拨开草丛——里面藏着一小截麻绳,颜色和王大爷说的一模一样,
绳头还有被扯断的痕迹。“这绳子不像是捆玉米用的。”吴叔捏着麻绳看了看,
“捆玉米用粗麻绳,这种细的,更适合……捆小物件。” 他没明说,但我心里清楚,
“小物件”指的是什么。我们接着往旱厕走,离着还有几步远,就闻到那股熟悉的腥臭味。
吴叔绕着旱厕转了一圈,在粪缸旁边的泥土里,
发现了半个模糊的脚印——脚印的大小和马国梁的布鞋差不多,鞋底的纹路虽然不清晰,
但能看出和他藏在柴房里的旧鞋纹路有几分相似。“回去吧。”吴叔站起身,
拍了拍手上的土,“现在证据够多了,该去跟马国梁好好聊聊了。”回到赵家院子时,
天色已经擦黑。马国梁正坐在门槛上抽烟,地上扔了好几个烟蒂。看见我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