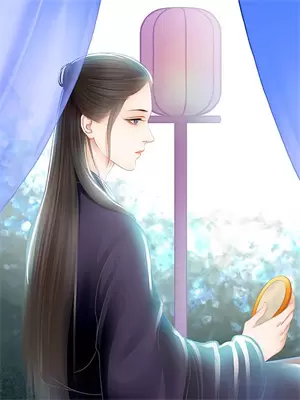作为聋哑考古学家,我受邀研究一具千年古尸。古尸的陪葬品中,
有一卷记载着“寂静之刑”的玉简。每当夜深人静,我的助听器里会传来持续不断的磨骨声。
团队里的手语翻译开始做出诡异手势,坚称是古尸在与他交流。挖掘现场陆续有人失踪,
回来后都失去了听力,只会用手语重复一句话:“祂喜欢安静,所以要剥夺所有声音。
”---陈默教授到来之前,这座位于西北边陲、深藏在黑山褶皱里的考古营地,
已经连续经历了三个反常的寂静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安静,那是一种被抽干了所有底噪,
连空气都凝固了的死寂。没有风声,没有远处戈壁滩上偶尔传来的砾石滚动声,
甚至连仪器运转时本该有的微弱嗡鸣,都消失不见了。声音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瞬间掐断,
留下的真空压得人耳膜生疼,心跳不由自主地擂在空洞的胸腔里,发出擂鼓般的巨响。
每次持续不过一两分钟,却足以让营地里最沉稳的老技工也面露惊惶,不安地四处张望。
陈默是三天前接到紧急邀请的。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先秦考古与古文字专家,更重要的是,
他是一位先天性聋哑人。邀请函来自他的老朋友,也是此次考古项目的负责人,赵启明教授。
信里的语气短促而急迫,只提到他们在黑山遗址的核心墓室,
发现了一具极为特殊的、保存完好的千年古尸,以及一批可能记载着某种失传秘仪的玉简,
急需他协助破译。信末,赵启明笔迹有些潦草地追加了一句:“此地有些……异样,
你来了务必小心,尤其是……声音。”“声音”两个字,被重重圈了起来。
陈默当时并未完全理解这警告的意味,直到他踏入这片被嶙峋山岩环抱的谷地。
营地的气氛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工作人员来往匆匆,彼此间很少交谈,
眼神接触时也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戒备。赵启明亲自来接他,几个月不见,
这位向来精力充沛的老友眼窝深陷,面色疲惫,握着他的手时,指尖冰凉且微微颤抖。
一路辛苦。赵启明用手语比划着,动作似乎也透着一股乏力,情况比预想的复杂。
陈默环顾四周,点了点头,回以手语:感觉到了。太静了。
赵启明的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引着他走向临时搭建的文物分析室。
分析室中央的恒温恒湿玻璃棺内,便是那具引起轩然大波的古尸。
即使在见多识广的陈默看来,它也堪称奇迹。尸身呈黑褐色,皮肤紧贴骨骼,
仿佛直接风干成了木质,看不出具体年代,但根据墓葬形制和伴出陶器残片,
初步断代至少在战国以前。它并非平躺,而是一种极其古怪的蜷缩姿势,双臂环抱双膝,
头深深埋下,像一个被巨大痛苦或恐惧凝固了的胎儿。面部五官模糊,
但嘴巴大张着一个黑洞,似乎死前正在无声地呐喊。最让陈默感到不适的,是古尸的双手。
那十根细长、干枯的指骨,以一种超越人体极限的灵巧姿态,在胸前交错、缠绕,
结成了一个复杂而诡异的手印。他不认识这个手印,只觉得多看几眼,
眼球便隐隐传来一阵针扎似的刺痛。我们称它为‘守寂者’。
赵启明在一旁的写字板上飞快地写下三个字,墨迹透过纸背,显出一种用力过猛的仓促。
陈默的视线很快被棺椁旁陈列台上的一批玉简吸引。玉质温润,色泽青灰,
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细如蚊足的奇异文字。这种文字结构扭曲,充满不自然的转折和弧度,
与他所知的任何先秦古文字体系都对不上号,透着一股非人的、令人心底发毛的陌生感。
他戴上白手套,拿起其中一枚保存相对完好的玉简,凑近灯光。指尖触碰到冰凉玉质的瞬间,
他似乎听到了一声极细微、极遥远的叹息,像是从地底深处,或是他自己脑海深处直接响起。
他猛地抬头,看向赵启明,后者正低头揉着眉心,毫无反应。是错觉?还是助听器故障?
他定了定神,压下心头泛起的那丝寒意,将全部注意力投入到玉简的解读中。文字虽然陌生,
但依稀能分辨出一些类似甲骨文或金文的构字元素,只是被扭曲、重组,
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他调动起毕生所学,尝试进行拆分、比对、联想。
时间在寂静中流逝。分析室里只有仪器运行的微弱指示灯在闪烁,
以及两人轻不可闻的呼吸声——赵启明的,和他自己需要通过胸腔震动才能隐约感知的。
不知过了多久,陈默终于从那扭曲的笔画中,
艰难地辨识出了几个重复出现的、令人不安的核心字词。他拿起笔,
”“剥夺……声……音……”“献……祭……”“彼……喜……静……”写到最后四个字时,
他的笔尖不由自主地顿了一下,一股寒意顺着脊椎悄然爬升。“彼喜静”。玉简记载的,
是一种名为“寂静之刑”的可怕仪式?是为了献祭给某个“喜欢安静”的存在?他抬起头,
想将初步发现告诉赵启明,却见老友不知何时已靠在椅背上,眉头紧锁,似乎陷入了浅眠,
但眼皮下的眼球却在快速转动,仿佛正经历着一场激烈的梦境。陈默没有打扰他,
目光重新落回那具蜷缩的“守寂者”身上。古尸张开的黑洞洞的口腔,和那诡异的手印,
在“寂静之刑”与“彼喜静”的解读背景下,仿佛被注入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全新含义。
第一夜,陈默是在营地临时为他安排的单人帐篷里度过的。西北昼夜温差极大,入夜后,
寒气从地面丝丝缕缕渗透进来。他摘下一侧耳廓上的助听器准备入睡——尽管他听不见,
但长期佩戴已成为一种习惯,也能通过机身细微的震动感知周围环境的低频振动。然而,
就在他摘下助听器,准备关闭电源的瞬间,一阵极其尖锐、仿佛金属刮擦骨骼的噪音,
猛地刺入他残存有微弱听觉的右耳耳蜗!那声音无法用言语准确形容,
像是有人用锈迹斑斑的锯子在缓慢地、耐心地锯着什么坚硬的东西,
又像是牙齿在疯狂地摩擦、碾碎骨头。咯吱……咯吱……声音持续不断,
带着一种冰冷的、非人的质感,直接钻进脑髓深处。陈默猛地坐起,心脏骤停了一瞬。
他下意识地捂住右耳,但那声音并非来自外部,
更像是直接从助听器的内部元件里滋生出来的。他迅速关闭了助听器的电源。
世界瞬间陷入他熟悉的、绝对的寂静。冷汗却从额角滑落。他重新打开助听器。
“……滋……咯吱……咯吱……”声音依旧,没有丝毫变化。他反复开关数次,
那磨骨声如同附骨之疽,紧紧缠绕在助听器开启的状态下。他尝试调整频道,
甚至取下助听器的电池,但那声音仿佛在他断开电源的前一秒,
就已经烙印在了他的听觉神经末梢,隐隐回响。这不是故障。他清晰地意识到。
没有任何电子故障会产生如此具象、如此充满恶意的声音。他想起了赵启明信里的警告,
想起了玉简上“寂静之刑”、“剥夺声音”的字眼。那一夜,陈默几乎无眠。
磨骨声在他重新戴上助听器后,持续不断地在他耳内响彻,直到窗外天际泛起鱼肚白,
才如同退潮般悄然消失。第二天,他顶着浓重的黑眼圈出现在分析室。
赵启明的状态似乎更差了,眼神涣散,反应迟钝。陈默犹豫再三,
还是在写字板上告知了昨夜助听器的异常,隐去了磨骨声的具体描述,
只说是持续的、无法解释的尖锐噪音。赵启明看完,瞳孔猛地一缩,脸色瞬间灰败了几分。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用力拍了拍陈默的肩膀,摇了摇头,
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一种近乎绝望的告诫。他在纸上潦草地写下一行字,
推到陈默面前:“不只是你。很多人晚上都‘听’到了……奇怪的东西。别深究,
尽量……习惯。”别深究?习惯?陈默的心沉了下去。
这不符合赵启明一贯严谨探究的学术作风。营地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
分析室的门帘被掀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是负责团队沟通的手语翻译,李河,
一个二十出头、平时总是带着阳光笑容的小伙子。但此刻,他脸上没什么表情,
眼神有些直勾勾的,动作也显得有些僵硬。陈教授,赵教授。李河比划着手语,
需要我翻译今天的初步工作安排吗?陈默点了点头。李河开始转述,他的手语流畅标准,
但陈默很快注意到了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在句子间歇,或者表达完一个完整意思后,
李河的指尖会无意识地、飞快地弹动几下,勾勒出几个极其短暂而古怪的附加动作。
那不像任何已知手语的词汇或语法成分,更像是一种……无意义的痉挛,
或者某种古老而神秘的符咒片段。起初陈默以为是自己眼花,或者李河只是手指疲劳。
但他越观察,越觉得不对劲。那些细微的、穿插在正常手语间的诡异小动作,
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和节奏,与他昨晚研究的玉简上,那些扭曲文字的笔画走向,
隐隐有着某种令人不适的相似性。更让他心底发寒的是,
在一次李河无意识做出一个快速翻腕、五指如爪般向内收缩的动作时,
陈默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恒温棺里那具古尸环抱在胸前的、结着诡异手印的手指,
极其轻微地……动弹了一下。他霍然转头,紧紧盯住古尸。
干枯的手指依旧维持着那个复杂的手印,纹丝不动,
仿佛刚才那一瞬只是灯光晃动造成的错觉。陈默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转向李河,用手语问道:李翻译,你的手是不是不舒服?我看你有些小动作不太自然。
李河愣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茫然,随即,一种近乎狂热的光芒在他眼底闪现。
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举起双手,开始主动地、清晰地比划起来,不再是正常手语,
而是一连串复杂、连贯、充满诡谲美感的未知手势,如同沉默的舞蹈。祂在教我。
李河的手指舞动着,表情带着一种虔诚的迷醉,是‘守寂者’。祂通过梦境,通过寂静,
在与我的灵魂直接交流。这些,是上古的秘传手印,是接近‘彼’的途径。
陈默的心彻底凉了下去。他看着李河沉醉于那套诡异的手势中,
仿佛在举行一场无声的降仪。赵启明在一旁重重叹了口气,用手捂住了脸,肩膀垮了下去,
显然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却无力阻止。接下的几天,营地的气氛愈发诡异。
那种吞噬一切声音的“绝对寂静”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
每当寂静降临,所有人都被迫停下手中的工作,僵立在原地,
感受着那剥夺感官的死寂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和恐惧。然后,
失踪事件开始了。先是负责夜间巡逻的两个保安。第二天清晨换班时,被发现不在岗位上。
营地组织人手搜寻,最后在距离古墓入口不远的一处背风山坳里找到了他们。
两人蜷缩在地上,身体剧烈颤抖,眼神空洞,对周围的呼喊和问话毫无反应。
人们把他们扶回营地,医生检查后,发现他们的耳膜完好无损,
但对任何声音刺激都没有了反应——他们彻底聋了。而且,他们失去了语言能力,
只会反复地、固执地用手语比划着一句话。那手语并非标准用语,
而是夹杂着李河之前展示过的那种诡异手势元素的、一种被“污染”了的混合体。
陈默挤到前面,紧紧盯着那两人舞动的手指,
安静……所以……要……剥夺……所有……声音……恐慌像瘟疫一样在营地蔓延开来。
陆续又有几人或在寂静期,或在夜晚离奇失踪,被找到后,都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失聪,
失语,只会反复比划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开始有人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营地。但更恐怖的是,试图离开的人,
要么在第二天清晨被发现昏倒在营地边缘,同样失去了听力,要么就彻底消失,
再也找不到踪迹。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所有人囚禁在了这片被山峦环绕的绝地。
营地彻底瘫痪了。日常工作完全停滞,人们聚集在最大的帐篷里,依靠微弱的应急灯光壮胆,
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赵启明试图稳定局面,
但他的安抚在接二连三的诡异事件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本人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憔悴下去,
时常对着古墓的方向发呆,眼神空洞。陈默将自己关在分析室里,
几乎是强迫症般地投入对玉简的疯狂破译。助听器里的磨骨声每晚如期而至,
且似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靠近,仿佛那个“磨牙”的东西,正从遥远的虚空,
一步步逼近他的耳边。他不敢摘下助听器,
那意味着将彻底丧失对可能存在的真实危险的预警,只能硬生生承受着这精神上的酷刑。
睡眠严重不足,精神高度紧绷,耳边是持续的噪音折磨,眼前是扭曲诡异的文字和手势,
身边是不断被“剥夺声音”的同伴……陈默感觉自己也在被一步步逼向崩溃的边缘。
他注意到,赵启明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行为。有时会看到他独自一人站在古尸前,
嘴唇无声地嚅动着,像是在进行某种对话。有时,他会模仿李河,
做出一些笨拙而诡异的疑似手印动作。有一次,
陈默甚至看到赵启明用指甲在手臂上反复刻画着玉简上那个代表“寂”字的扭曲符号,
直到皮肤渗出细小的血珠。陈默感到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和恐惧。侵蚀不仅仅来自于外部,
更来自于内部,来自于人心深处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寂静”的屈服。这天深夜,
持续的磨骨声和营地死一般的寂静交织,陈默头痛欲裂,无法入睡,决定去分析室继续工作。
他裹紧外套,走出帐篷。营地中央空无一人,只有几盏太阳能灯在黑暗中投下惨白的光晕。
他快步走向分析室所在的板房。就在他经过营地边缘那片堆放杂物的阴影时,
一阵极其细微、却清晰无比的“沙沙”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那不是风声。他猛地停下脚步,
屏住呼吸,借助微弱的灯光,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阴影里,蹲着一个人影,背对着他,
肩膀在轻微耸动。是赵启明。他蹲在地上,手里似乎拿着什么东西,正在……摩擦着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