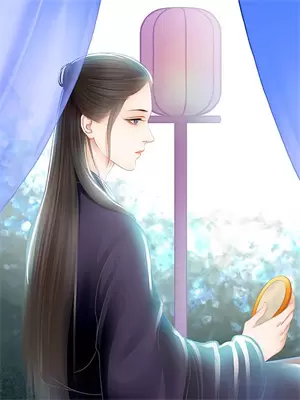1 鬼楼惊魂湘西有座废弃的百年吊脚楼,每逢月圆之夜,楼里会传出女子的哭声。三年前,
一个外地来的摄影师在楼里离奇死亡,相机里最后一张照片是个穿嫁衣的女人。我们不信邪,
组成探险小队深夜闯入。手电筒的光扫过堂屋,那口传说中的红漆棺材竟然开着。
里面躺着个面容如生的新娘子,嘴角咧到耳根,像是被人硬生生缝上去的。“你们来了,
”她突然睁开眼,针脚密布的嘴唇一张一合,“我等下一个替身,等了整整一百年。
”---月亮爬上老鸦岭的山脊时,像一块被人啃得只剩边边角角的冷烧饼,
吝啬地将一点惨白的光,投给山下那栋孤零零的吊脚楼。楼是老的,怕是有一两百年了。
木头都泛着一种霉烂的黑,不少窗棂朽坏脱落,像缺了牙的嘴。
野生的藤蔓疯了似的缠绕着柱子和栏杆,夜风一过,窸窸窣窣的,
像是无数条冰冷的蛇在暗处蠕动。本地人管这叫“鬼楼”,轻易不敢靠近,尤其月圆夜。
都说那时候,楼里会有女人的哭声,断断续续,呜呜咽咽,搅得人心里头发毛。三年前,
有个不信邪的外地摄影师,揣着他那套高级设备,非要进去拍点“有灵魂的影像”。
结果是被人抬出来的,脸色青紫,眼睛瞪得溜圆,像是活活吓死的。警察来了又走,
说是意外。只有他手里死死抱着的相机,洗出最后一张照片——模模糊糊,
是个穿着老旧嫁衣的女人身影,站在楼梯的拐角,没有脸,只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暗影。
这旧事,成了我们这次探险最好的由头。我们一行四人,我,
胆子不算大但好奇心重的;大壮,人如其名,一身疙瘩肉,号称鬼见了都绕道;小斌,
灵异论坛版主,理论知识一套一套;还有雅静,大壮的女朋友,本来不想来,被硬拉来的,
此刻小脸煞白,紧紧攥着大壮的胳膊。“我说,咱……咱真要进去啊?”雅静声音带着颤音,
望着几十米外那栋在月色下如同匍匐巨兽的黑影。“废话!来都来了!”大壮一拍胸脯,
声音在寂静的山谷里显得格外响亮,“怕什么?真有女鬼,老子正好抓回去给你做伴娘!
”小斌推了推眼镜,手里拿着个电磁场检测仪,屏幕上的数字偶尔跳动一下,他压低声音,
用一种营造氛围的腔调说:“资料记载,这楼是清末一个苗姓土司给他最宠爱的姨太太修的,
后来不知怎么起了火,那姨太太就烧死在里面,怨气不散。看这磁场波动,啧啧,
果然有东西。”我没吭声,只是调整了一下头灯,又检查了下挂在胸前的运动相机。
心里那股子不安,像藤蔓一样,越缠越紧。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木门时,
一股混合着陈年灰尘、木头腐朽和某种难以言喻的、类似草药霉变的阴冷气息,扑面而来。
所有人都打了个寒噤。楼里比外面看着更破败。
手电光和头灯的光柱在浓得粘脚的黑暗里来回切割,照亮飞舞的尘埃,蛛网,
以及角落里堆积的、辨不出原形的杂物。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板激起回响,一下下,
敲在人心上。堂屋很宽敞,但同样破落。神龛歪斜,上面的雕像早就没了踪影,
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正中央,果然停着一口棺材。大红的漆,在岁月侵蚀下变得斑驳暗沉,
像凝固发黑的血块。棺椁很大,静静地摆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威胁。
“就……就是这口棺材?”雅静躲在大壮身后,声音抖得不成样子。2 缝嘴新娘“怕啥,
一口木头盒子而……”大壮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几道光柱,此刻都不约而同地,
聚焦在那棺材盖上。那厚重的、本该严丝合缝盖着的棺盖,此刻,
竟然斜斜地滑开了一道一尺来宽的黑缝!“我……我操!”大壮骂了半句,
后半句噎在了喉咙里。小斌手里的检测仪突然发出尖锐的“嘀嘀”声,
屏幕上的数字疯狂乱跳。“能量读数爆表!有……有东西出来了?
”一股寒意从我的尾椎骨直窜上天灵盖。三年前那个摄影师的死状,瞬间闪过脑海。
相机里那张没有脸的女人照片……好奇心,或者说一种作死的冲动,驱使着我的脚步。
我咽了口唾沫,喉咙干得发疼,一步一步,朝着那道幽深的缝隙挪去。光柱颤抖着,
率先探入那棺内。首先看到的,是一抹刺目的红。是嫁衣,那种老式的新娘礼服,
金线绣着的凤凰图案在光线下反射出诡异的光。往上,是一张脸。一张女人的脸。
皮肤白得不像活人,是一种毫无生气的冷白,像上好的瓷器。五官极其精致,柳叶眉,
樱桃口,栩栩如生。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双手交叠在身前,仿佛只是睡着了。然而,
所有人的呼吸都在那一刻停滞了。她的嘴唇。那两片本该是樱桃小口的地方,
嘴角被人用粗陋的黑色线绳,硬生生地缝了起来!针脚歪歪扭扭,一直裂到接近耳根的位置,
让整张脸呈现出一种极其诡异、令人头皮发麻的笑容。“嗬……”雅静发出一声短促的抽气,
眼睛一翻,软软地往地上倒去,被手忙脚乱的大壮一把抱住。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比他妈任何恐怖片里的妆容都来得吓人!那是实实在在的,
一种施加在人体上的,残忍而古老的酷刑痕迹!死寂。楼里只剩下我们粗重而混乱的喘息声,
以及小斌那破仪器还在固执的“嘀嘀”声。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棺材里,那个穿着嫁衣,
嘴角被恐怖缝住的女人,毫无征兆地,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极其漂亮的杏眼,
瞳孔又黑又深,像两口古井,里面没有任何情绪,只有一片沉沉的死气。
她眼珠极其缓慢地转动了一下,视线,精准地落在了我们几个身上。然后,
她那被黑色线绳粗暴缝住的嘴唇,开始蠕动。线绳深深嵌入皮肉,随着她的动作,
似乎能听到细微的、皮肉被牵扯的涩响。一个清晰、冰冷,不带任何起伏的女声,
从那密布针脚的缝隙里,一字一顿地挤了出来:“你们来了,”“我等下一个替身,
等了整整一百年。”“啊——!!!”大壮发出一声不似人腔的嚎叫,
抱着昏迷的雅静踉跄后退,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小斌“哐当”一声把检测仪砸在了地上,
屏幕瞬间黑了。他本人则像被抽了骨头,软倒在地,手脚并用地往后爬。我僵在原地,
血液仿佛瞬间冻结,四肢冰冷麻木,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震得耳膜嗡嗡作响。替身?
一百年?那女尸,不,那活过来的东西,说完那句话,
嘴角那被缝出的恐怖笑容似乎更明显了些。她交叠在腹部的手,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
一根苍白纤细、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微微抬起,指向了我们。不是我们。是指着我。
“跑……跑啊!”大壮终于找回了一点神智,嘶哑着吼了一声,抱起雅静,像头发疯的野牛,
扭头就朝门口冲去。小斌也连滚带爬地跟上,期间还摔了一跤,磕破了额头,
血流了满脸也顾不得。我落在最后,不是因为不怕,
而是那双冰冷的眼睛和那根指向我的手指,像有无形的枷锁,钉住了我的脚步。
直到大壮的吼声和凌乱的脚步声远去,我才猛地一个激灵,求生本能压倒了一切,
转身没命地狂奔。冲出吊脚楼的那一刻,冰冷的山风灌入口鼻,我却觉得那是自由的空气。
不敢回头,生怕一回头,就看到那抹红色的身影,或者那张缝着嘴巴的脸,就贴在身后。
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跑下山,回到停在山脚的车上。大壮把雅静塞进后座,自己钻进驾驶位,
手抖得几次都插不进钥匙。小斌瘫在副驾,脸色比死人还难看,额头的血糊了半张脸。
车子终于发动,咆哮着冲上公路,将那座吃人的老鸦岭和山上的鬼楼远远甩在身后。一路上,
没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喘息,和雅静偶尔发出的、意义不明的呻吟。车灯劈开前方的黑暗,
却照不亮我们心头的浓重阴影。等车子开进市区,看到霓虹闪烁,人声渐起,
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才稍微缓解了一丝。“刚才……刚才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小斌用袖子擦着脸上的血,声音沙哑破碎。“鬼!还能是什么!他妈的真的见鬼了!
”大壮死死握着方向盘,指关节泛白,“那棺材里的老娘们!她活了!她说话了!
你们听到没?替身!她要找替身!”他说着,猛地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带着恐惧,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因为最后,那根手指,指向的是我。
我靠在椅背上,浑身脱力,那女尸冰冷的声音还在脑海里回荡——“等下一个替身,
等了整整一百年”。为什么是我?3 诅咒血脉回到临时落脚的旅馆,雅静醒了,只是哭,
问什么都不说,显然吓得不轻。我们谁也没提分开睡,四个人挤在一个标间里,
灯开得亮如白昼。可即便如此,一闭上眼睛,就是那张缝着嘴的诡异笑脸,
和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第二天,我们谁也没敢再提回去探查的事,几乎是落荒而逃,
各自买了最早的车票,逃离了这个诡异的小城。回到我所在的城市,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
但我清楚,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开始做噩梦。每晚,只要一闭眼,
就会回到那个阴森的堂屋,看到那口打开的红漆棺材,看到那个穿着嫁衣的女人,
用她那被缝住的嘴,对我无声地笑。有时,梦里会有模糊的片段,冲天的火光,女人的惨叫,
还有冰冷的、带着血腥味的诅咒。更诡异的是,我发现自己对某些东西,
产生了莫名的熟悉感。偶尔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关于湘西少数民族风情的纪录片,
里面出现的某种银饰图案,或者某种祭祀舞蹈,会让我心头猛地一跳。甚至有一次,
在旧书摊看到一本关于湘西巫傩文化的泛黄书籍,翻开一页,
上面画着一种奇怪的、用黑线缝住动物嘴巴的符咒,我竟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恶心想吐。
我开始查阅资料,疯狂地搜寻一切与那座吊脚楼,与那个苗姓土司,
与湘西古老习俗相关的信息。网络,图书馆,甚至托关系找了一些研究地方志的老学者。
零碎的线索,像散落的拼图,慢慢在我脑海中汇聚。苗姓,曾是当地颇有势力的土司。
清末年间,最后一代土司苗震山,娶了一位名叫阿阮的苗族女子为妾。阿阮极美,擅歌舞,
深得苗震山宠爱,却也因此遭致正室和其他姨太太的嫉恨。后来,
寨子里发生了一场诡异的瘟疫,死人无数。有巫师指控阿阮是“草鬼婆”放蛊女,
说她用邪术害人。盛怒和恐惧之下,苗震山听信谗言,
命人用最恶毒的方式——以沾染黑狗血的麻线,缝住了阿阮的嘴,防止她念动咒语,
然后将她锁在她居住的吊脚楼里,放火活活烧死,以平息所谓的“神灵之怒”。
据说阿阮临死前,穿着她最心爱的那套嫁衣,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诅咒苗家断子绝孙,
诅咒所有负心薄幸、轻信谗言之人,永世不得安宁,需世代寻找替身,承受她所受之苦。
而那场大火后不久,苗家果然迅速败落,族人死的死,散的散,那栋吊脚楼也荒废下来。
关于“缝嘴新娘”的传说,却在当地以各种隐秘的形式流传下来,只是年代久远,细节模糊,
大多被视为吓唬小孩的怪谈。直到三年前那个摄影师,直到我们……所以,棺材里的,
就是阿阮。她不是鬼,更像是一种怨念不散的……厉魄?她在等替身。
等一个能够解除她诅咒,或者……替代她承受这无尽痛苦的人。而为什么是我?资料里提到,
那种缝嘴的巫术,需要至亲之人的血浸染麻线,效果最强。而苗震山,据野史杂闻推测,
可能并非汉人,其母系一族似乎有来自更遥远神秘部落的血统。
我猛地想起家族里一个模糊的传言,说我曾祖父那一辈,似乎是为了避祸,
从湘西那边迁出来的……一个可怕的念头,如同毒蛇,钻入我的脑海。难道,我身上,
流淌着那个下令缝嘴、放火烧死阿阮的苗姓土司的血?所以,她能感应到我?所以,
她指向我?所以,那些莫名的熟悉感和噩梦?我不是随机被选中的替身。我是……她的后代,
是她诅咒最直接的对象!这个认知让我如坠冰窟。就在这时,更具体的变化开始出现。
我的嘴角,开始出现莫名的红肿和刺痛,像是皮肤要开裂。照镜子时,偶尔会产生幻觉,
看到自己的嘴角,也出现了那种歪歪扭扭的黑色针脚。虽然转瞬即逝,但那触目惊心的感觉,
却无比真实。我变得越来越恍惚,注意力无法集中。耳边开始出现若有若无的女人哭声,
和那晚在吊脚楼外听到的,一模一样。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知道,她来了。或者说,
她的诅咒,正在我身上应验。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联系了小斌,
他是我们之中对灵异这些东西最“懂行”的。电话里,他的声音很疲惫,甚至带着一丝恐惧,
他告诉我,他回来后也诸事不顺,而且他查过很多案例,被这种百年老怨灵盯上,
尤其是涉及血脉诅咒的,几乎无解。除非……“除非什么?”我急切地问。
“除非能找到她真正的尸骨,或者……完成她未了的心愿,化解她的怨气。
”小斌犹豫了一下,“但是太危险了!那地方……我们不能再去了!”必须去。我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