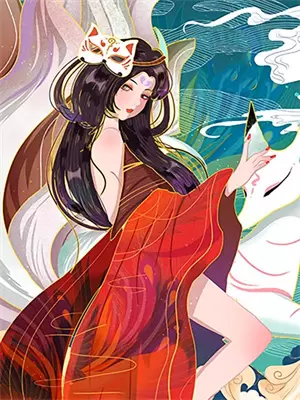光绪壬辰科状元录:张建勋七载京华路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月,
北京贡院的槐树枝桠刚抽出新绿,却被漫天黄沙打得蔫蔫的。张建勋攥着手里的蓝布考篮,
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考篮里的笔墨纸砚、素面馒头和咸菜坛子相互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
混在数千举子的喧哗里,像一粒石子落进奔涌的长河。这是他第七次踏入贡院。
从二十五岁初次应考,到如今三十二岁,鬓角已悄悄爬了几根银丝。身后,
几个年轻举子正高声谈论着去年顺天府乡试的趣事,笑声清脆,
张建勋却只觉得喉咙发紧——前六次落第的记忆,像贡院墙角的青苔,
在心底蔓延出湿冷的凉意。一、桂州寒门,萤窗苦读张建勋的老家在广西临桂今桂林,
一座被漓江水滋养的小城。父亲是个落魄的秀才,在私塾教几个蒙童,母亲操持家务,
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六岁开蒙,父亲教他读《三字经》,别的孩子还在院子里追蝴蝶,
他已能把“人之初,性本善”背得字正腔圆。十一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咳着血躺在床上,
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张家,三代没出过举人。你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功名,
不光是为自己,也为咱们桂林的读书人争口气。”那时广西地处偏远,科举向来“瘠土”,
自顺治朝以来,全省只出过两个状元,最近的一个还是乾隆年间的事。父亲去世后,
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母亲把陪嫁的银镯子当了,换了些米粮,却从不让他辍读。
张建勋白天帮着母亲喂猪、挑水,晚上就点着油灯看书。油灯的烟把鼻孔熏得发黑,
他却常常读到后半夜。有一次,油灯里的油烧完了,他就借着窗外的月光,
把《论语》里的篇章一遍遍默写,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十六岁那年,张建勋考中了秀才,
按例可以进县学读书。县学的教谕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举人,见他读书刻苦,又肯动脑筋,
便常常把他叫到书房,额外教他些应试的诀窍。“科举文章,讲究‘起承转合’,
但更要言之有物。”老教谕摸着胡子说,“你生在桂林,见惯了山水,
写文章时不妨把山水的灵气融进去,别学那些只会堆砌辞藻的酸腐文人。
”张建勋把这话记在了心里。他读书时,不光读“四书五经”,还常去漓江边散步,
看江水涨落,听渔舟唱晚。有时遇到行脚的商人、砍柴的樵夫,他也会凑上去聊几句,
听他们讲外面的世界。这些见闻,都被他悄悄记在本子上,成了文章里最鲜活的素材。
二十五岁,张建勋第一次赴京赶考。临行前,母亲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卖了,换了二两银子,
塞进他的怀里:“路上小心,考中与否,都要平平安安回来。”他背着简单的行囊,
从桂林坐船到广州,再转乘漕船北上。漕船走得慢,一路走了两个多月,
他在船上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看书。有一次,船遇到风浪,颠簸得厉害,
他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却不顾船板湿滑,赶紧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擦干上面的水渍。
可这一次,他落榜了。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从头看到尾,都没找到自己的名字。
走出贡院时,天上下着小雨,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看着那些考中的举子被亲友簇拥着,
笑逐颜开,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不敢立刻回家,怕母亲伤心,
就在北京找了个抄书的活计,一边做工,一边继续复习。此后的几年,
张建勋又接连考了五次,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归。有一次,
他的文章被房考官看中,推荐给主考官,却因为“字迹稍显潦草”,最终没能上榜。那一夜,
他在租住的小屋里,把自己写的文章一遍遍地看,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甚至想过放弃,
回桂林找个私塾教书,安稳度日。可每当想起父亲的遗言,想起母亲期盼的眼神,
他又咬牙坚持了下来。二、京华客居,砥砺初心光绪十七年1891年,
张建勋第六次落榜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回家,而是留在了北京。
他在宣武门外租了一间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夏天会开满白色的槐花。
他找了份给人批改文章的差事,挣钱糊口,之余便埋头苦读。租住的院子里,
还住着一个叫李墨卿的举子,比他小五岁,来自江苏苏州。李墨卿出身书香门第,
家里颇有财力,随身带的书都是上好的刻本,写文章时也总爱用些生僻的典故。起初,
两人只是点头之交,后来因为都爱读书,渐渐熟络起来。有一次,李墨卿看到张建勋读的书,
书页都翻得卷了边,有的地方还缺了页,忍不住问:“张兄,你怎么不买些新刻本?
这样的书读起来多费劲。”张建勋笑了笑:“旧书虽破,却能看出前人的批注,
比新刻本更有味道。再说,我手头不宽裕,能有书读就不错了。”李墨卿听了,
有些不好意思,从自己的书箱里挑了几本常用的经书,送给了张建勋:“这些书我都有两套,
你拿着用,不用客气。”张建勋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后来也常常把自己整理的应试心得,
抄录一份送给李墨卿。两人常常在槐树下对坐,一起讨论文章的写法,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过后却又相视一笑,感情越来越深。这一年,北京城里发生了不少事。先是黄河决口,
灾民纷纷涌入京城乞讨;接着又传来消息,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举行操练,
却被洋人嘲笑“船坚炮利,却无实战之力”。这些事,张建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埋头钻研应试文章,而是开始关注时政,常常买些《申报》来看,
了解国家的局势。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报道,广西巡抚在当地推行新政,开办新式学堂,
却遭到守旧派的反对。他想起自己老家那些因为贫困而无法读书的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晚上,他在灯下写了一篇文章,谈“教育为本”,主张不仅要重视科举,更要广办学堂,
让更多的人能读书识字。李墨卿看到这篇文章,连连称赞:“张兄,你这文章写得有理有据,
比那些只谈‘仁义道德’的空泛之论强多了!要是主考官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定会眼前一亮。
”张建勋却摇了摇头:“科举文章,讲究‘代圣贤立言’,这样谈论时政的文字,
怕是难入考官的眼。”话虽如此,他却没有停下关注时政的脚步。他知道,
国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一个读书人,不能只想着考取功名,更要为国家做些实事。
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春节刚过,张建勋就开始收拾行囊,
准备参加这一年的会试。李墨卿也收拾好了东西,两人约好一起去贡院报名。报名那天,
贡院门口人山人海,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络绎不绝。张建勋看着眼前的景象,
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他想起自己七年来的付出,想起母亲的期盼,暗暗在心里说:“这一次,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三、贡院三场,笔定乾坤三月初九,会试正式开始。张建勋提着考篮,
走进了贡院的号房。号房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小床,头顶是低矮的屋檐,
连站起来都要低着头。他放下考篮,先仔细检查了一遍笔墨纸砚,然后坐在椅子上,
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第一场考的是“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
题目下来后,张建勋先把题目仔细看了一遍,然后闭上眼睛,在脑子里构思文章的框架。
他想起老教谕说的“言之有物”,又结合自己这些年对时政的思考,
决定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切入,既符合“代圣贤立言”的要求,
又能融入自己的见解。他拿起笔,蘸了蘸墨,开始写起来。笔尖在纸上划过,
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写得很专注,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贡院里点起了灯笼,
昏黄的灯光透过号房的窗户照进来,映在他的脸上。他伸了伸酸痛的手臂,啃了几口冷馒头,
喝了口水,又继续埋头写作。到了半夜,贡院里渐渐安静下来,
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和翻书声。张建勋有些困了,他站起来,
在狭小的号房里来回走动了几步,又用冷水洗了把脸,让自己保持清醒。他知道,
这场考试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容不得半点马虎。第二天中午,第一场考试结束。
张建勋走出号房时,阳光有些刺眼,他揉了揉眼睛,看到李墨卿正在不远处等他。“张兄,
考得怎么样?”李墨卿笑着问。“还行,把该写的都写了。”张建勋说,“你呢?
”“我也差不多,就是那首诗,写得有些仓促。”李墨卿叹了口气。接下来的几天,
张建勋又参加了第二场和第三场考试。第二场考的是“五经”文五篇,
第三场考的是策问五道,涉及经史、时政、军事等方面。策问的题目里,
有一道是关于“如何加强海防”的,张建勋看到这道题,心里很激动。
他想起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关于北洋水师的报道,又结合自己对海防的思考,
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主张“既要购置先进的军舰,也要培养新式的海军人才,
更要改革海防制度,做到上下一心,共御外侮”。三场考试下来,张建勋瘦了一圈,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走出贡院时,他感觉浑身都要散架了,
但心里却很踏实——他已经把自己想说的、能说的,都写在了试卷上。四、金榜题名,
御笔点元会试结束后,张建勋回到了租住的小院,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每天除了看书,
就是在槐树下散步,心里既期待又忐忑。李墨卿也常常来和他聊天,
两人都默契地很少提起考试的事,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结果的在意。半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