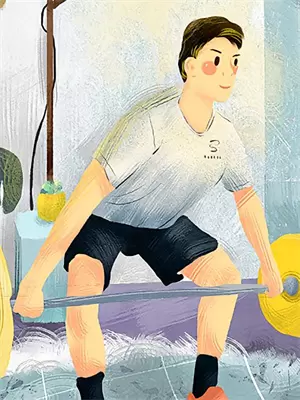
村会计赵有财每次送来烈士周志勇的抚恤金,都要抽走大半。他总说:“上头就拨了这点,
你儿子命不值钱!”直到那天,一辆军用越野车开进我们村。---雨水像是发了狠,
砸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响成一片,震得人心里发慌。屋里那股子阴冷潮气,
像无数看不见的小虫子,直往骨头缝里钻。周秀英佝偻着背,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破竹椅上,
借着窗户透进来的一点灰蒙蒙的天光,费力地辨认着手里那个小药瓶上的字。
瓶底只剩下孤零零三粒白色的药片了,圆圆的,小小的,像三颗干瘪的种子。
风湿痛又在作怪,膝盖骨里像有把钝锯子来回拉扯。她枯瘦的手指捏着瓶子,抖得厉害,
几次想旋开瓶盖,又几次放下。药快没了,钱……更没了。喉咙里堵着一团酸涩的东西,
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最后只化作一声沉得坠到泥里的叹息,融进无休无止的雨声里。
“突突突……”那阵由远而近、嚣张跋扈的摩托车引擎声,像一把烧红的锥子,
猛地刺穿了雨幕的沉闷。周秀英浑身一僵,捏着药瓶的手指骤然收紧,骨节泛出青白。
心口那点微弱的暖意瞬间被抽干,只余下冰冷的、沉甸甸的恐慌。她下意识想站起来,
膝盖却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让她又跌坐回去。“哐当”一声,
那扇摇摇晃晃的薄木板门被粗暴地推开,撞在土墙上,震落簌簌的灰土。
一个裹在劣质塑料雨披里的身影堵住了门口的光线,雨水顺着他肥厚的下巴往下淌。
正是村会计赵有财。他摘下湿淋淋的雨披,随手一甩,
泥点子就溅到了墙角那张擦拭得干干净净的烈士遗像玻璃框上。相框里,
周志勇穿着笔挺的军装,眼神明亮而坚定。“老周家的!”赵有财的声音又尖又利,
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不耐,仿佛在吆喝牲口。他踱进来,
那双沾满泥泞的皮鞋毫不客气地踩在刚扫过的泥地上,留下一个个肮脏的湿脚印。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两根手指捏着,远远地朝周秀英晃了晃,
像在逗弄什么动物。周秀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浑浊的眼睛紧紧盯着那薄薄的信封。
那是勇娃拿命换来的钱,是她活下去的唯一指望。“喏,志勇的抚恤钱!
”赵有财拖长了调子,手腕一翻,几张零散的、湿了边角的钞票飘落下来,
散在周秀英脚边的泥地上。一张五十,两张十块,几张一块的毛票。总共……七十五块。
周秀英的呼吸猛地一窒,眼睛死死盯着地上那几张可怜的票子,干裂的嘴唇哆嗦着,
几乎发不出声音:“赵……赵会计,这……这数目不对啊……上个月还有一百二,
志勇他……”她挣扎着弯下腰,想去捡那几张沾了泥水的钱,
动作迟缓得像一株即将枯死的树。“不对?”赵有财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短促地嗤笑一声,脸上的横肉跟着抖了抖。他向前逼近一步,
油腻腻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周秀英脸上,“上头就拨了这点!你当国家钱是大风刮来的?
能给你个孤老婆子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他俯下身,
那张泛着油光的胖脸凑近周秀英满是皱纹的脸,压低了声音,每一个字都淬着冰冷的恶意,
“周秀英,我告诉你,别不识抬举!再嚷嚷,我就去镇上报告,
说你儿子那点事根本够不上烈士标准,是你家骗国家补助!到时候,连这七十五块都没了!
你儿子的命,哼,也就值这点钱!”“值这点钱……”周秀英猛地抬头,
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蒙上一层血丝。赵有财最后那句恶毒的话,像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她千疮百孔的心上。勇娃扑进洪水里救出三个娃娃,
自己被冲得无影无踪……他的命,怎么就成了赵有财嘴里轻飘飘的“这点钱”?
巨大的悲愤和屈辱堵在胸口,让她眼前阵阵发黑,喉咙里咯咯作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像一尊骤然失去所有支撑的泥塑,身子晃了晃,扶着冰冷的土墙才没倒下,
只有那只攥着空药瓶的手,抖得停不下来。赵有财看着她的样子,脸上掠过一丝残忍的快意,
仿佛踩死了一只碍眼的虫子。他不再理会这瘫软的老妇,转身就往外走,
湿漉漉的鞋底再次碾过那些散落的钞票,留下一道更深的泥痕。“砰!”门被摔得山响,
震得屋顶的灰尘簌簌落下。屋里彻底暗下来,只剩下无孔不入的冷风和永不停歇的雨声。
周秀英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冰冷的地上。她伸出枯枝般的手,颤抖着,
一点点把地上那几张被泥水浸透、被踩踏过的钞票捡起来,紧紧攥在手心,
湿冷的纸片贴着皮肤,像握着几块冰。她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无声地剧烈耸动起来,
压抑的呜咽在胸腔里破碎地滚动,被外面更加狂暴的雨声彻底吞没。勇娃,
妈没用……妈护不住你拿命换来的钱……妈连自己都快护不住了……不知过了多久,
雨势似乎小了些,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连绵不断的沙沙声。周秀英扶着墙,
挣扎着站起来,膝盖的剧痛让她倒抽一口冷气。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灶台边,
那里放着早上吃剩的半个黄黑色的窝窝头,硬得像石头。她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
干涩粗糙的碎屑刮着喉咙,她费力地吞咽着,就着水缸里舀起的半瓢凉水。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不同于赵有财摩托引擎的沉稳声音。是车轮碾过泥泞路面的声音,由远及近,
最后在院门外停住。周秀英的心莫名地一紧,手指下意识地捏紧了那半个硬窝头。
是赵有财又回来了?还是……她不敢往下想。脚步声响起,沉稳、有力,踏在泥水里,
一步步走近。门板被轻轻叩响,那声音带着一种陌生的、小心翼翼的尊重。“大娘?
是周秀英大娘家吗?”一个年轻却异常沉稳的男声穿透了薄薄的门板。周秀英犹豫着,
挪到门边,颤巍巍地拉开了门闩。门外站着一个高大的年轻人,穿着笔挺的便装,
肩头被雨水打湿了一片深色。他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袋,另一只手,
紧紧攥着一个用墨绿色绒布包裹着的、方方正正的盒子。雨水顺着他轮廓分明的下颌线滑落,
他的眼神锐利如鹰,却在看到周秀英的刹那,
涌起难以抑制的波澜——那是深切的痛楚和强忍的悲怆。
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周秀英手里捏着的硬窝头,扫过她身后空荡荡、家徒四壁的屋子,
扫过墙角那张蒙了灰尘却依旧端正的烈士遗像……最后,
他的视线落在老人身上那件打满补丁、洗得发白的旧褂子上,
停在她沾着泥点、冻得通红的赤脚上。空气仿佛凝固了。
“大娘……”年轻人的声音陡然变得沙哑艰涩,仿佛每一个字都带着沉重的分量,
“我是李振国,志勇……志勇的战友。”他举起那个墨绿色的盒子,手背上的青筋微微凸起,
“我……送志勇回家。”“志勇……”周秀英浑浊的眼睛猛地睁大了,像是被这两个字烫到,
手里的半个窝头“啪嗒”一声掉在泥水里。她死死盯着那个盒子,嘴唇剧烈地哆嗦着,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抽气声,身体晃了晃,眼看着就要向后栽倒。李振国眼疾手快,
一步抢上前,丢开旅行袋,稳稳地扶住了老人单薄得几乎只剩一把骨头的手臂。“大娘!
您坐!您坐下!”他的声音急切,带着军人不容置疑的力量,
小心地搀扶着她坐回那把破竹椅。他蹲下身,仰头看着老人瞬间失去所有血色的脸,
那双锐利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深不见底的痛惜和沉重的承诺。
他用力握了握周秀英冰冷枯槁的手,声音低沉却无比清晰:“志勇不在了,大娘,
我们……都是您儿子。”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悲痛时刻,
院门外又响起了那阵刺耳熟悉的摩托车引擎声,由远及近,带着一种令人厌恶的急促。
赵有财去而复返。他那双老鼠眼隔着院墙就瞧见了那辆停在泥水里的墨绿色军用越野车,
车身上溅满了泥点,却依旧透着一股子不怒自威的硬朗劲儿。赵有财的心猛地一跳,
一种混合着惊疑和贪婪的预感攫住了他。他几乎是滚下了摩托车,连雨衣都顾不上穿,
腆着肚子,脸上瞬间堆砌起无比谄媚的笑容,三步并作两步就冲进了院子。“哎哟!首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