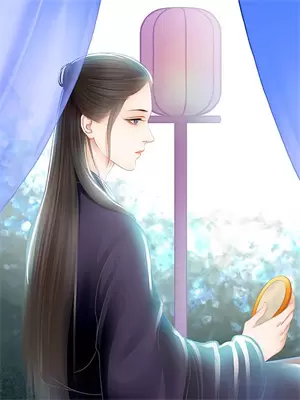1我叫阿照。我们村子世代靠山吃山,山里有个山神,年年要娶新娘。轮到我及笄这天了。
阿娘一早给我换上红嫁衣,手抖得厉害,系带子都系了三次。她眼睛肿着,不敢看我,
只反复念叨:“阿照,听话……到了山神那儿,好好伺候……”我没吭声。看着窗外,
日头还没完全升起,村子里静悄悄的。我知道,他们都躲在家里,等着送我走。
爹蹲在门口抽烟,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脸。辰时一到,族长来了。
穿着那件褪色的黑褂子,身后跟着巫祝和几个族老。“吉时到了。”族长声音干巴巴的,
像晒裂的柴火。他们把我带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树身上缠着褪色的红布条,
都是往年那些姐姐们留下的。巫祝开始念咒,声音又尖又细,像针扎耳朵。
两个妇人拿来浸过山泉的牛皮绳,把我牢牢捆在树干上。绳子勒进肉里,生疼。
村民们陆陆续续来了,围成个半圆,远远站着。没人说话,
只有小孩被捂住了嘴发出的呜咽声。日头慢慢爬高,晒得人发晕。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张婶低着头,李叔眼神躲闪,小时候带我掏鸟蛋的铁柱哥,
把脸扭到一边。我知道他们怕。怕山神发怒,降下灾祸。怕没吃的,怕野兽下山。所以,
牺牲我一个,最划算。快到正午时,林子里起了风。树叶哗哗响,人群骚动起来。“来了!
山神使者来了!”巫祝尖声叫道,扑通跪下。所有人都跟着跪下了,黑压压一片。
我挺直脊背,死死盯着林子方向。脚步声嗒、嗒、嗒,不紧不慢。然后,它走了出来。
不是我想象中的凶兽,也不是庙里画的神将。是只山羊。灰毛,黑蹄子,比寻常山羊大一圈。
可脖子上顶着的,是张皱巴巴的人脸。眼睛浑浊,嘴角往下耷拉着。它走到我面前,
那股味道冲进鼻子——像烂树叶混着陈年的血。“新娘。”它开口了,声音像砂纸磨石头。
它低头,用牙齿叼住我身上的绳结,轻轻一扯。牛皮绳应声而落。“跟上。”它说完,
转身就往林子里走。我活动了下僵硬的手腕,最后看了眼跪了满地的人。阿娘瘫在爹怀里,
肩膀抖得厉害。我转身,跟上那只山羊。山路越来越窄,树荫浓得化不开。山羊走在前头,
步子不大,但稳当。它一次也没回头,好像笃定我会跟着。我悄悄从袖袋里摸出石片。
这是我自己磨的,藏在嫁衣里带了出来。石片边缘薄而锋利。我把它夹在指缝间,
假装拢袖子,开始锯手腕上剩下的那截绳头。很慢,很小心。石片割破手心,血渗出来,
黏糊糊的。我不敢停。那山羊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我立刻僵住,手缩回袖子里。
它那双浑浊的人眼看了看我,又转回去,继续走。我松了口气,后背全是冷汗。继续锯。
一下,两下……绳子终于断了。我把断绳攥在手心,假装还被绑着,等机会。前面是个陡坡,
山羊先下去了。就是现在!我猛地转身,扑进旁边的灌木丛!“嗷——!
”身后传来尖锐的嚎叫,根本不是羊叫,像夜枭啼哭。脚步声急促起来,它追来了!
我拼命跑!树枝抽在脸上,火辣辣地疼。嫁衣被扯破,绊手绊脚。我摔了一跤,
膝盖磕在石头上,钻心地疼。爬起来继续跑!不能停!后面的声音越来越近,
那股腐臭味几乎贴到脑后。慌不择路,我一脚踩空!天旋地转,不知道滚了多久,
最后重重摔在地上,眼前一黑。……冷。刺骨的冷。我睁开眼,好半天才看清自己在哪儿。
是个山洞。不大,但深。光线从洞口藤蔓缝隙漏进来,勉强能视物。然后,
我看清了洞里的东西。白骨。到处都是人骨。有的完整,有的散架。骷髅头上黑洞洞的眼窝,
齐刷刷对着我。那些破碎的红布条,和我身上的嫁衣一个颜色。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捂住嘴,才没吐出来。这里是坟场。前头那些新娘的坟场。“醒了?”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吓得我魂飞魄散!我猛地扭头,看向山洞深处。篝火。一小堆火在跳动。火堆旁,坐着个人。
是个少年,穿着脏得看不出本色的短打,头发胡乱束着。他手里拿着根树枝,串着条鱼,
正架在火上烤。鱼烤得焦黄,油滴进火里,噼啪作响。他好像没看见我,或者看见了不在乎。
慢条斯理地翻动着烤鱼,吹了吹,咬了一口。嚼了几下,他抬眼看向我。火光映着他的脸,
挺干净,甚至算得上清秀。可那双眼睛,黑沉沉的,没什么光。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手里另一串烤好的鱼。“吃吗?”他问。声音不高,有点哑。我僵在原地,
脑子转不过弯。他等了一会儿,见我没反应,也不勉强,自顾自又咬了口鱼。“等你吃饱了,
”他嚼着鱼肉,含糊不清地说,“我教你杀回去。”2我盯着他,没动。
那条烤鱼散发着焦香,勾得我肚子咕咕叫。从早上到现在,我滴水未进。可这地方,这人,
太邪门。满洞的白骨,他坐在中间烤鱼,还说要教我杀回去?“你是谁?
”我的声音干涩发紧。他慢条斯理地又咬了一口鱼,嚼着。“过路的。
”“这里……”我环顾四周,那些空洞的眼窝让我脊背发凉,“这些骨头……”“嗯。
”他点点头,好像我问的是天气。“都是山神的新娘。有些年头了。”他说的平淡,
我却打了个寒颤。“你不怕?”我问。他抬眼看了看我,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没什么波澜。
“怕什么?死人比活人安生。”他把手里吃剩的鱼骨头扔进火堆,发出滋啦一声。
“你到底吃不吃?不吃我睡了。”我看着他真的作势要躺下,心里一急。“吃!
”饿死和毒死,我选后者。至少做个饱死鬼。我撑着身子想站起来,膝盖一阵剧痛,
又跌坐回去。这才发现,小腿和手臂上全是擦伤和淤青,刚才逃命时没觉得,现在疼得钻心。
他瞥了我一眼,没过来扶,只是把那条完整的烤鱼插在靠近我这边地面的石缝里。我挪过去,
抓起烤鱼。很烫,也顾不上,张嘴就咬。鱼肉焦香,没什么盐味,但对我饿瘪的肚子来说,
已是无上美味。我狼吞虎咽,差点噎住。他不知从哪儿摸出个竹筒,递过来。“水。
”我接过来,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清凉的山泉水下肚,人才感觉活过来一点。吃完鱼,
我把骨头也嚼碎了咽下去,连指尖的油渍都舔干净。洞里安静下来,只有篝火偶尔的噼啪声。
我看着他。他抱着膝盖,看着火堆出神,侧脸被火光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你刚才说……教我杀回去?”我试探着问。他“嗯”了一声,没转头。“怎么杀?
山神……还有那个怪物使者……”他终于转过头,上下打量我。“就你现在这样,
站都站不稳,拿什么杀?”我语塞,低头看着自己破烂的嫁衣和满身伤痕。
“那……那怎么办?”“先活下来。”他说,“把伤养好,学点保命的本事。”他站起身,
走到洞壁旁,那里堆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弯腰翻捡了一会儿,
拿回几片宽大的叶子和一坨黑乎乎的、像是烂泥的东西。“衣服脱了。
”他把东西放在我面前。我猛地抱住胳膊,警惕地瞪着他。他嗤笑一声。“想什么呢?
给你治伤。这鬼地方,你发烧死了,我还得费劲拖出去扔。”他语气里的嫌弃毫不掩饰。
我脸一热,知道自己想岔了。但这荒山野岭,陌生男人面前……“转过去。”我说。
他翻了个白眼,但还是背过身去。我咬着牙,把破烂的红嫁衣褪到腰间,
露出身上青紫交错的伤。有些地方破了皮,渗着血丝。那黑泥看着恶心,
但敷在伤口上却传来一阵清凉,火辣辣的疼痛顿时减轻不少。
他用那些大叶子帮我把伤口裹住,动作算不上温柔,但也没弄疼我。“这是什么?”我问,
指着那黑泥。“烂树根和草药捣的,止血消肿。”他简短地回答,帮我包扎好膝盖。
“好了没?”我赶紧把衣服拉好。“好了。”他转回来,又坐回火堆旁。“你叫什么名字?
”我问。总不能一直“喂”他。他拨弄着火堆,火星子溅起来。“忘了。”“怎么会忘?
”“不想记,就忘了。”他答得干脆。我看着他冷淡的侧影,知道问不出什么。“我叫阿照。
”我说。他没什么反应。沉默再次蔓延。洞外传来不知名野兽的悠长嚎叫,
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怕了?”他头也不抬。“……有点。”“怕就睡觉。
睡着了什么都不怕。”他往后一靠,闭上眼睛。“明天开始,没空让你怕了。
”我看着他就这么毫无防备地睡去,心里乱糟糟的。这个人,救了我,给我吃的,治伤,
却说不出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他的话能信吗?杀回去?谈何容易。可除了信他,
我好像也没别的路可走。我靠着冰冷的石壁,蜷缩起来。身下是硬邦邦的地面,
旁边是累累白骨。恐惧和疲惫像潮水般涌来,但我强迫自己睁大眼睛,不敢睡。火光跳跃,
映着他安静的睡颜,也映着那些森白的骨头。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我知道,
我不想死在这里。不想像那些白骨一样,无声无息地烂在这个山洞里。杀回去。这三个字,
像颗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发了芽。3天还没亮透,洞里一片灰蒙蒙。我睡得不安稳,
梦里全是那张皱巴巴的羊脸和追在身后的嚎叫。猛地惊醒,心脏怦怦直跳。篝火已经灭了,
只剩一点余烬。少年不在原来位置。我撑着身子坐起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
伤口被拉扯着疼。洞内光线昏暗,那些白骨若隐若现,看得人心里发毛。
窸窸窣窣的声音从洞口传来。我警惕地望过去,看见少年正掀开藤蔓走进来。
他手里拎着两只肥硕的山鼠,尾巴还滴着血。“醒了?”他把山鼠扔在我脚边,“处理一下。
”我看着那两只还在微微抽搐的灰毛老鼠,胃里一阵翻腾。“这……怎么吃?”“剥皮,
去内脏,烤。”他言简意赅,走到洞壁旁拿起我的石片——昨晚我掉在地上的,
开始在一块石头上磨。“还是你想饿死?”我咬着嘴唇,没动。村子里再穷,也没人吃老鼠。
他磨石片的声音刺啦刺啦响,头也不抬。“那些新娘,”他突然说,“刚送来的时候,
也跟你一样。”我猛地抬头看他。他停下动作,看向那些白骨,眼神没什么变化。“头几天,
哭,闹,不吃不喝。后来饿极了,虫子,老鼠,树皮……什么都往嘴里塞。”我喉咙发紧,
看着那些森白的骨头,仿佛能听见她们绝望的呜咽。“再后来,”他声音平淡,
“连塞东西的力气都没了,就躺在那儿,等死。”他转回头,继续磨石片。“山神不吃人,
它只取心。等她们饿得只剩一口气,那山羊就来,剖开胸口,把心挖走。”我浑身发冷,
下意识捂住胸口。想象着那些姐姐们最后的时刻,在这阴冷的山洞里,一点点耗尽生命,
然后被……“你怎么知道?”我声音发颤。他放下磨好的石片,锋利的边缘泛着冷光。
“我见过。”他没再多说,拿起一只山鼠,利落地用石片划开肚皮,剥皮,掏出内脏。
动作熟练得让人心惊。血淋淋的鼠肉扔在我面前。“学不学,随你。”他开始处理第二只。
我看着那团粉红色的肉,又看看周围的白骨。饿死的恐惧,和被挖心的恐惧,交织在一起。
我深吸一口气,抓起另一只山鼠。皮毛温热滑腻,带着腥气。我闭上眼,回想他的动作,
用石片尖端抵住鼠腹。手抖得厉害。划下去的时候,温热的血溅到我手上。我强忍着恶心,
笨拙地剥开皮,扯出那些黏糊糊的内脏。弄完时,我手上、袖口上全是血,胃里翻江倒海。
他却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他把鼠肉串在树枝上,重新生起火。烤鼠肉的味道并不好,
有一股骚味,肉质柴硬。但我一口一口,强迫自己咽下去。吃完,他站起身。“能动了吗?
”我试着活动了一下,膝盖和手臂依旧疼,但勉强能走。“跟上。”他掀开藤蔓,走了出去。
洞外天光已亮,林子里弥漫着晨雾。他走得很快,我咬牙跟着,伤口被牵动,疼得额头冒汗。
他没回头,也没放慢脚步。走到一处溪流边,他停下。“洗干净。血味会招东西。
”我蹲在溪边,用力搓洗手上的血污和腥气。冰凉的溪水刺激着伤口,我打了个哆嗦。
洗完抬头,发现他正看着我小腿上包扎的叶子。有些松散,渗出血迹。他走过来,
不由分说地扯掉旧叶子,查看伤口。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个装黑泥的皮囊,重新给我敷上,
又扯了几片新的叶子绑好。动作依旧不算温柔,但比昨晚细致了些。“今天学走路。
”他直起身,“不出声,不留痕迹的走。”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走路谁不会?他示意我跟上,
然后迈步走进旁边的灌木丛。他的脚步落下,几乎听不到声音,身体灵活地避开横生的枝杈,
像林间的影子。我学着他的样子,小心翼翼地落脚,却还是踩断了一根枯枝,
发出清脆的“咔嚓”声。他回头瞥我一眼,没说话。我又试。尽量用脚掌先着地,慢慢压实,
避开落叶多的地方。手臂张开保持平衡,低头弯腰,钻过矮树丛。很累。比平常走路累十倍。
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全身肌肉都绷着。没走多远,我就气喘吁吁,伤口也开始抗议。
他停下来,递过竹筒。“歇一刻。”我接过水,大口喝着,汗珠从额头滚落。
“为什么……要学这个?”我喘着气问。“逃命,或者靠近猎物,都用得上。
”他靠着一棵树,“不想下次被那山羊追上,就好好学。”歇够了,继续。整个上午,
我们就在这片林子里反复练习走路。他偶尔会指出我的问题——“脚抬太高”,
“呼吸太重”,“胳膊碰到叶子了”。我学得很慢,不断出错。他不骂,也不急,
就那么看着,然后示范正确的。快到正午,日头毒辣起来。我累得几乎虚脱,
靠在一棵树上喘气。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回去。”回到山洞,他让我重复早上的步骤,
生火,处理他抓回来的另一只山鼠。这次我熟练了一些,虽然依旧恶心,但手稳了不少。
烤鼠肉的时候,我看着他擦拭那把石片,忍不住又问。“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懂这些?
为什么帮我?”他擦石片的动作停了一下,抬眼看向洞外。“我有个妹妹。”他声音很低,
“如果她还活着,跟你差不多大。”我愣住了。“她也被选为新娘。”他继续说,
语气没什么起伏,“那年我十三岁,想带她跑,没跑掉。”洞里安静下来,
只有火堆的噼啪声。“后来呢?”我轻声问。“后来,我找到了这里。”他看向那些白骨,
“没找到她。大概……早就成了其中一副。”他收起石片,不再说话。我看着他的侧影,
第一次在他那总是没什么表情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极淡的,像是刻进骨头里的东西。
那不是悲伤,是比悲伤更坚硬的东西。那天下午,他没再让我学走路。
而是给了我一根削尖的树枝,教我辨认几种附近常见的,能止血、消肿或者充饥的草叶。
“记牢。”他说,“名字不重要,长什么样,有什么用,记死。”我学得很认真。用手摸,
用鼻子闻,努力把每一种的特征刻进脑子里。我知道,这些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
傍晚时分,他带我到洞口,指着远处暮霭中隐约可见的山峦轮廓。“那边,”他说,
“最高的那座山后面,就是山神的老巢。”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群山叠嶂,
在夕阳下泛着冷硬的青黑色。最高的那座山峰,像一只沉默的巨兽,俯瞰着这片山林。
“那山羊每隔七天,会来山洞一次。”他声音平静,“带走还活着的新娘。”我算了算日子,
心里一沉。“那就是……还有四天?”“嗯。”他转头看我,“四天。你能学会多少,
看你自己。”压力像石头一样压下来。四天。我要从一个连老鼠都不敢杀的祭品,
变成能杀回去的人?我看着远处那座山,又看看身边这个来历不明的少年。四天。
我握紧了手里削尖的树枝。4第四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他就把我摇醒了。
“今天学点实在的。”他丢给我一捆柔韧的藤蔓,还有几根粗细不一的树枝。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看着地上的东西,不明所以。“陷阱。”他蹲下身,
拿起一根一头削尖的硬木,开始在地上刨坑。“最简单的,绊索,陷坑,刺桩。看仔细。
”他的动作很快,挖坑,布置削尖的树枝,覆盖伪装,
设置触发机关……一边做一边讲解要点。“藤蔓要绷紧,但不能太显眼。坑不用太深,
能崴断脚脖子就行。尖刺朝上,斜着插……”我看得眼花缭乱,只觉得他手指翻飞,
没一会儿,一个看似寻常的落叶地面下,就藏着能让人掉进去扎个对穿的险恶机关。“试试。
”他站起身,示意我自己动手。我学着他的样子,选了个靠近兽径的位置,开始挖坑。
泥土混着碎石,很难挖。削尖树枝更是费力,石片总打滑,差点割到手。他在旁边看着,
不帮忙,也不催促。好不容易弄出个歪歪扭扭的坑,布置好尖刺,盖上树叶。
看着那片微微隆起的地面,我自己都觉得漏洞百出。“猎物不是瞎子。”他点评,“风一吹,
叶子飘走一半。重新弄。”我憋着口气,推倒重来。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日头升高,
我才勉强做出一个能入他眼的陷坑。手心磨出了水泡,一碰就疼。“记住感觉。”他说,
“手上记住了,比眼睛记住有用。”午后,他换了个花样。
带我认了几种带有麻痹或致晕效果的草叶和树汁,教我如何涂抹在尖刺或者箭头上。
“分量要准。”他警告,“少了没用,多了直接毒死,引不来那山羊。”“引它?
”我心头一跳。“不然呢?”他看我一眼,“等它自己撞进你的陷坑?
它在这山里走了几百年,比你熟。”我哑口无言。“这东西,
”他指指一种紫色浆果挤出的汁液,“抹在石片上,划破点皮,能让那畜生晕眩一会儿。
就一会儿,是你唯一的机会。”我小心地收集那些浆果,用叶子包好汁液,
感觉自己像故事里那些调制毒药的巫婆。傍晚,他没让我生火。而是带着我,
悄无声息地潜行到山洞附近的一处高地,指着下方一条被踩得发亮的小径。“它每次来,
都走这里。”他压低声音,“看清楚地势。”那是一条夹在两块巨大山岩之间的窄路,
一侧是陡坡,长满带刺的灌木,另一侧下方是乱石滩。“你的陷坑,设在哪里最有用?
”他问。我仔细观察。窄路中段,有个稍微开阔的转弯处,地面松软,适合挖坑,
而且转弯时视线受阻……“那里。”我指向那个位置。他点点头,算是认可。
“算你还有点眼力。”回到山洞,天色已暗。他没点火,我们借着洞口透进的微弱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