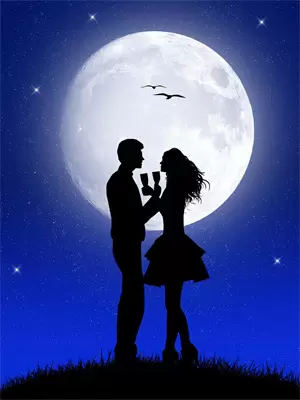认识那伙年轻人的时候,是个刚入秋的傍晚。风里带着点未褪尽的暑气,裹着桂花淡淡的甜,
他们围坐在巷口的小饭馆里,吵吵嚷嚷却又透着种莫名的疏离,
像一群被世界轻轻隔在玻璃罩里的人。人来疯最先注意到的是人来疯姑娘,15岁的年纪,
个子已经窜得很高,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轻轻晃动,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
话密得像春雨后的竹笋。后来才知道她打了八年舞蹈,
可从没见过她展示哪怕一个简单的动作,只是偶尔她抬手整理头发时,手腕转动的弧度里,
藏着几分经年累月沉淀的舒展。她总在人群里最活跃,讲段子、学方言,
把小饭馆的气氛搅得热热闹闹,可当邻桌有人好奇地朝这边看过来时,
她的笑声会下意识地收住半分,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局促。
芬芳的香文静姑娘就坐在她旁边,17岁,斯斯文文地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
说话时条理分明,每一个字都吐得清晰柔和,却总把“我就是个废物”挂在嘴边。
她穿着素色的连衣裙,坐姿端正,像株安静的含羞草,别人聊天时她大多在听,
偶尔插一两句话,也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她说自己喜欢做影子,乖乖地跟在别人身后,
不需要被注意到。可我分明见过她在饭馆角落的书架前,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看得入神,
手指轻轻摩挲着书页,眼神里有不属于“影子”的专注与亮泽。
大法官小个子姑娘是这群人里最“正常”的一个,马上要高三,
理科生的特质在她身上很明显,说话做事都透着股克制的飒爽。
她总在饭桌上抱怨男朋友的车技,说每次坐他的车都晕得想吐,语气里满是嫌弃,
可眼睛里却没有真的怒意。她会精准地计算AA制的账单,分毫不差,
也会在有人讲废话时冷冷地戳破,逻辑清晰得让人无法反驳。16岁的年纪,
本该是肆意张扬的,她却像揣着一把精准的尺子,丈量着自己的情绪与言行,
很少泄露出她对失控的隐秘抗拒。神仙一把抓大神姑娘坐在最里面,21岁,
脸色带着点长期体弱的苍白,说话声音轻轻的,却总能在聊到传统文化时眼里发光。
她是音乐系的,对古琴、昆曲、诗词格律都有着惊人的深刻理解,偶尔提起某句古文,
能流畅地背出上下文,甚至追溯到不同版本的注解。她的身体似乎不太好,
吃几口饭就要停下来歇一歇,可聊到《广陵散》的曲式结构时,语气里的笃定与热忱,
让人暂时忘了她眉宇间的倦意。她总说自己没力气去应付复杂的人和事,
可说起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时,眼里分明藏着对知己的深切向往。
铁柱大神经男孩和大神姑娘同岁,师范院校的模范生,却活得大大咧咧。
他总穿着宽松的运动服,说话声音洪亮,席间最活跃的除了人来疯姑娘,就是他。
他有一辆二手汽车,还有一辆心爱的摩托车,总说喜欢骑着摩托车四处溜达,
感受风从耳边掠过的自由。他会在饭桌上讲自己支教时的趣事,讲课堂上调皮的学生,
语气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可当有人提议“下次约着认识几个新朋友”时,
他的话头会突然顿住,转而说起摩托车的保养,眼神飘向窗外,避开了众人的目光。
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带着种让人羡慕的放纵与默契。吃饭永远AA制,
算得清清楚楚却从不含糊;半夜里有人在群里喊“一起起床尿尿”,
真的会有人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顶着夜色去卫生间,然后在群里吐槽“被你坑醒了,
被窝都凉了”;兴致来了,会突然闯进某个人的家,掀开对方的被窝,
看着对方睡眼惺忪地跳起来,然后一起在客厅里吃零食、看电影,闹到后半夜。可这份亲密,
却似乎只局限在他们几个人之间。他们不跟外人玩儿,不轻易和陌生人说话,
更不会主动交新朋友。在学校里、在家人面前,
他们都是别人眼里的乖乖仔:人来疯姑娘会收起张扬,
做听话的学生;文静姑娘会扮演好懂事的女儿;小个子姑娘专注于学业,
做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大神姑娘乖乖养病,认真上课;大神经男孩恪守师范生素养,
温和有礼。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曾经抑郁,或者现在还在抑郁泥潭里挣扎的人。
那些打打闹闹的瞬间,那些肆无忌惮的亲密,像是他们给自己搭建的避风港。
在这个小圈子里,他们可以不用伪装,可以喊着“我是废物”,可以嫌弃男朋友车技不好,
可以大大咧咧地骑摩托车,可以做影子,也可以做自己。可抑郁的阴霾,
并没有因为这份亲密而彻底消散。它像一层薄薄的雾,笼罩在他们的生活里,
让他们不敢轻易走出这个小小的圈子。他们会在热闹过后突然沉默,
会在笑得最开心时眼底闪过一丝落寞,会在深夜里对着手机屏幕发呆,迟迟无法入睡。
轻轻的慢慢的走有一次,我偶然撞见人来疯姑娘一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
没有了往日的活泼,只是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长椅的木板。我走过去打招呼,
她抬头时,眼睛红红的,带着未干的泪痕。“有时候觉得,
我们就像一群被困在透明盒子里的人,”她轻声说,“在里面很暖和,真的很暖和。”是啊,
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相互取暖,半夜起床尿尿的默契,掀被窝的放纵,AA制的分明,
都是他们对抗孤独与抑郁的武器。他们乖乖地做着别人眼里的乖乖仔,却在彼此面前,
露出最真实的模样——有脆弱,有迷茫,有不甘,也有对温暖的渴望。这群青春期的孩子,
像一颗颗被风雨洗礼过的种子,带着伤痕,却依然努力地在彼此的陪伴中生根发芽。
他们的抑郁还在,孤独也还在,可他们之间的那些小美好,那些肆无忌惮的亲密,
就像被窝里的一束微光,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彼此前行的路,让他们在黑暗中,
不至于太过孤单。或许,青春就是这样,一边带着伤痕,一边相互扶持;一边被困在阴霾里,
一边努力寻找光亮。而他们之间的情谊,就是那束最珍贵的光,温暖着彼此的被窝,
也温暖着那段兵荒马乱的青春期。左右互搏术秋意渐浓的时候,那伙年轻人又来过几次。
有时是周末的午后,踩着阳光闯进巷口的小饭馆,人来疯姑娘依然是最热闹的那个,
远远就喊着“老板,照旧来几道菜”,路过我桌前时,会停下脚步冲我笑一笑,
说“又碰到啦,下次我们带自制的小饼干给你尝”;文静姑娘跟在后面,
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古籍,路过时轻轻点头问好,声音柔和得像羽毛,
说“上次你提到的那首词,我回去查了不同的注本”,没等多说几句,
就被人来疯姑娘拉着去选座位了。小个子姑娘总是和大神经男孩一起到,
她还是会吐槽男朋友的车技,说“这次坐他的车,居然没晕车,算他进步”,
大神经男孩在一旁嘿嘿笑,插话说“下次我骑摩托车载你,保证稳得很”,路过我时,
会抬手打个招呼,喊着“下次我们约着去郊外兜风,要不要一起?”,没等我回应,
就被小个子姑娘笑着推走了“别瞎邀请,人家不一定有空”。大神姑娘来得稍晚些,
脸色依旧带着点苍白,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吉他的布包,路过时会停下脚步,
和我聊上两句关于音乐的话题,说“最近在练一首新的曲子,下次有机会弹给你听”,
语气轻轻的,却满是认真,聊了两三句,就被里面的伙伴喊着“快来坐,菜要凉了”。
每次见面都很仓促,大多是几句简单的问候,夹杂着他们之间的插科打诨。有一次临走前,
人来疯姑娘突然跑过来,眼睛亮晶晶地说“我们下下周六还来这儿,到时候给你带饼干,
再给你表演个小魔术”,文静姑娘在一旁补充“我们还打算吃完饭后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你要是有空,可以一起”。大神经男孩也凑过来,拍着胸脯说“我开车载你们,
保证不晕车”,被小个子姑娘笑着怼了一句“就你那车技,还是算了吧”。
大神姑娘站在后面,轻轻点头“我们都约好了,下下周六下午三点,还在这儿见”。
他们的约定说得热热闹闹,带着青春期独有的鲜活与直白,像秋日里的一束暖阳,
短暂却明亮。我看着他们勾肩搭背地离开,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拐角,
耳边还残留着他们的笑声与打闹声,心里忽然觉得,那些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抑郁阴霾,
似乎在这样一次次的相聚与约定里,淡了些许。而那个下下周六的约定,像一颗小小的种子,
埋在渐凉的秋日里,带着几分期待,等着下次见面时,绽放出更多温暖的模样。
奶奶的爱秋意一天天深了,巷口的桂花香也愈发浓郁,那伙年轻人的身影,
也成了小饭馆里渐次频繁的风景。更让人心头暖暖的是,他们每次来,总不会空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