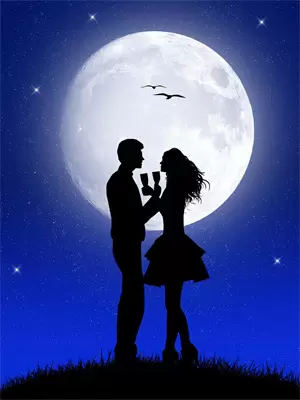第一章:乌台诗案前的快乐打工人一、上班如上坟,
但苏轼穿了新鞋北宋熙宁十二年1079年三月初七,京城汴梁,晨雾未散。
苏轼踩着新买的麻履,走在通往御史台的路上。鞋底厚实,鞋帮挺括,
是他用上月俸禄的三分之一,特意从“潘楼街老字号”订制的理由很简单:穿新鞋上班,
领导会觉得他“精神”。而精神,往往是保住饭碗的第一道防线。可他的精神状态,
其实早就裂开了。就在昨夜,他又被噩梦惊醒。梦里王安石骑着一头青牛,
牛角上挂着“青苗法”的竹简,追着他满汴梁跑,一边跑一边喊:“子瞻!
你那篇《上神宗皇帝书》写得不错,就是太酸了!”醒来后,苏轼摸了摸额头的冷汗,
顺手抄起砚台边的残稿,团成一团,扔进痰盂。“写什么写,再写就要进监狱了。
”但白天还得上班。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官服绿色,七品,湖州知州任上刚调回京,
暂时在“权知开封府推官”位子上挂职。说白了,就是个临时工,
负责审案、写判词、处理市井纠纷。听起来体面,
实则日日与泼皮无赖、争产兄弟、偷鸡贼打交道。“苏推官早啊!
”街角卖炊饼的老张冲他拱手。“早。”苏轼勉强一笑,顺手买了一个。咬一口,焦香酥脆,
瞬间治愈了三分怨气。可刚走到府衙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咆哮:“苏子瞻!
你写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民有菜色,官有酒气’?你当这是写词呢?!
”苏轼差点把炊饼噎住。说话的是他的顶头上司,
开封府尹李定一个以“铁面无私”著称、实则深得王安石信任的改革派干将。
此人最恨两种人:一是反对新法的旧党,二是文风太飘的文人。而苏轼,恰好两项全中。
“下官……下官只是如实记录。”苏轼硬着头皮走进去,把判词呈上。李定冷笑一声,
把纸拍在案上:“如实?你倒说说,哪条律法写着‘官有酒气’要判罚?嗯?
你这是在讽刺朝廷官员奢靡无度?”苏轼心里嘀咕:我讽刺的是你昨儿晚上在樊楼喝到三更,
还搂着歌姬唱《雨霖铃》的事儿,能怪我吗?但他嘴上乖得很:“大人明鉴,下官绝无此意。
那‘酒气’,是指酒坊蒸馏时的气味……百姓误以为是官衙熏香,故有此谣。
”李定眯眼盯了他三秒,忽然哈哈大笑:“好!好一个‘酒坊蒸馏’!苏子瞻啊苏子瞻,
你这张嘴,比你的笔还能圆。”苏轼赔笑:“不敢,不敢,全靠大人包容。”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在北宋当公务员,最重要的不是判案能力,
而是把黑话说成白话、把牢骚写成颂歌的本事。二、朋友劝他“闭嘴”,
他反手写了一首讽刺诗中午休沐,苏轼约了好友王诜shēn在“樊楼”二楼小聚。
王诜是驸马都尉,皇亲国戚,平日最爱收藏书画、结交文人。见苏轼一脸疲惫,
他直接倒了杯酒推过去:“子瞻,你再这么写下去,迟早要出事。”“我写什么了?
”苏轼灌了一口酒,酒是自酿的“雪堂春”,带点甜,是他从黄州老乡那儿学来的方子。
“你上个月那首《戏子由》‘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全汴梁都传疯了!
”王诜压低声音,“李定前天还在我府上打探,问你是不是在暗讽新法重律法、轻经义。
”苏轼一愣,随即苦笑:“我那是在夸我弟弟子由老实巴交,只会读书不会钻营。
怎么到他们耳朵里,就变成政治檄文了?”“因为你姓苏。”王诜叹气,“你是苏洵的儿子,
苏辙的哥哥,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旧党三代目。你说一句‘天气真好’,
他们都觉得你在影射‘新法如阴云’。”苏轼沉默片刻,忽然笑了:“那我不如真写点狠的。
”王诜吓得差点把酒杯打翻:“你疯了?!”“没疯。”苏轼提起笔,蘸了酒水,
在桌上写:“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王诜一看,
倒吸一口凉气:“你这是讽刺‘新法扰民’!百姓为应付青苗法、保甲法,
一年大半时间都在跑衙门,连孩子说话都学官腔了!”“对啊。”苏轼眨眨眼,“但你看,
我一句脏话没说,一个官员没点名,连‘新法’俩字都没提。他们要抓我,
得先证明‘儿童语音’是指官话,‘城中’是指衙门这能算罪?
”王诜扶额:“你是真不怕死。”苏轼哈哈大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我怕。
但我更怕活得像个哑巴。”这顿酒后,苏轼果然又写了好几首“无害”诗。每一首,
都像裹着糖衣的毒药,甜得让人咽下去才发现苦到心肝。比如他写农民插秧:“雨中耕作苦,
十指皆泥黑。归来问税吏,新谷已征毕。”比如他写市井小贩:“昨日担柴入市卖,
今日空筐泪满腮。官说物价须平准,不许高声叫出来。”这些诗,很快被抄录、传阅,
从茶馆酒肆,一路传到御史台的案头。李定看着这些“民谣”,冷笑:“苏子瞻啊苏子瞻,
你以为你写的是民生疾苦?你写的是政治炸弹。”三、乌台来人那天,
他正在煮猪肉六月十七日,苏轼调任湖州知州的任命刚下,他正忙着收拾行李。这回外放,
本是好事。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去江南喝喝茶、写写诗、吃吃猪肉,多自在?
他甚至已经开始研究《猪肉颂》的第二版:“慢著火,少著水,
火候足时它自美……”可就在他把一块五花肉放进砂锅的那一刻,门外马蹄声急。
“奉御史台令!苏轼接旨!”苏轼手一抖,锅盖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
来的是御史台的差役,共四人,面色冷峻。为首的掏出一纸公文:“苏轼,
有人告你‘讪谤朝政,讥讽圣上’,着即刻收监,待审!”苏轼脑子“嗡”了一声。
他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我的肉还没炖上呢!但他还是强作镇定,拱手道:“敢问罪名?
”“乌台诗案。”差役冷冷道,“你那些诗,句句是刀。”苏轼苦笑,
回头看了眼灶上咕嘟冒泡的砂锅,叹了口气:“容我……交代两句家事。”差役点头。
他走进内室,妻子王闰之早已哭成泪人。儿子苏迈跪在地上,脸色惨白。苏轼没哭,
反而笑了:“没事。最多流放。大不了去海南吃椰子。”他悄悄塞给苏迈一张纸条,
低声说:“若听闻我下狱,以此示人。”纸条上写着:“臣轼罪当万死,然不敢欺君。
”这是他的最后防线:认罪,但不认错。出门前,他忽然想起什么,又折返回厨房,
掀开锅盖,深吸一口气,喃喃道:“可惜了这锅好肉……”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尾声:快乐打工人,终究成了政治犯苏轼被捕那天,汴梁下了一场小雨。百姓们站在街边,
默默看着这位“苏推官”被押上囚车。没人敢说话,
但有人悄悄往车上扔了一块炊饼是老张家的,还是焦香酥脆。囚车驶向乌台,苏轼坐在里面,
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忽然想起昨夜梦到的青牛。原来王安石没骑牛来追他。是朝廷的律法,
早已化作千钧重枷,压在他肩上。而他这一生,不过是在枷锁里跳舞的文人。
但跳得真好看啊。第二章:乌台牢狱中的米其林三星体验当一个吃货被关进御史台,
他决定把牢饭吃出仪式感一、“牢饭难吃?那是你没加酱油!”苏轼被关进乌台的第一顿饭,
堪称北宋版“地狱开局”。一个粗陶碗,半碗发馊的糙米,几根发黄的菜梗,
外加一块硬如砖头的腌鱼。狱卒把碗往地上一蹾:“吃吧,苏大才子。”苏轼蹲下,
盯着那碗饭,沉默三秒。然后他笑了。“这位兄台,”他忽然抬头,语气诚恳,“你这腌鱼,
是不是用陈年井盐腌的?味道太齁了。若加点米醋,
再淋两滴 soy sauce酱油,风味立马不同。
”狱卒愣住:“……啥是soy sauce?”“哦,我说的是‘酱清’。”苏轼解释,
“就是豆酱滤出来的汁。我家厨娘常说,一滴酱清,胜过十味香料。
”狱卒:“……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是牢饭,不是樊楼宴!”苏轼不恼,
反而从袖中掏出一小包东西是他被捕前偷偷藏的“秘密武器”:自制复合调味料,
内含花椒粉、陈皮屑、芝麻油渣,还有几粒晒干的梅子。“来,”他把调料撒进饭里,
又用筷子搅了搅,“你看,颜色是不是立马鲜亮了?再配上窗外这雨声,简直‘牢中清供,
胜似山珍’。”狱卒目瞪口呆。更离谱的是,隔壁牢房的囚犯听见动静,
扒着栅栏喊:“苏学士!能分一口不?我拿半块馍换!”苏轼大方:“拿去!但记住,
饭要趁热吃,凉了腥气就出来了。”就这样,苏轼入狱第一天,没喊冤、没哭诉,
反而开了个“牢狱米其林快闪店”。二、审讯?不,是诗词鉴赏会乌台审讯,
向来以“酷烈”著称。主审官李定、舒亶等人,早准备好了一叠“罪证诗”,
打算把苏轼锤成“反革命诗人”。可当他们把《戏子由》《山村五绝》等诗拍在案上,
厉声质问:“你写‘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不是暗讽陛下如‘死龙’?
”苏轼眨眨眼:“大人误会了。我那是在夸松树根扎得深。‘蛰龙’是《周易》里的典故,
指潜藏的贤才比如……您这样的清官?”李定:“……”又问:“‘赢得儿童语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是不是说新法扰民?”苏轼叹气:“唉,大人有所不知。
我家小儿子在汴梁学说话,满口官腔,连‘爹’都叫成‘大人’。我这是自嘲当爹失败啊!
”舒亶冷笑:“那你写‘读书万卷不读律’,总不是夸自己无能吧?
”苏轼拍案而起其实是轻轻扶了下桌子:“此言差矣!我这是在推崇实务精神!
如今科举只考经义,不考律法,导致许多进士连《宋刑统》都没翻过。
我这是在呼吁教育改革啊!陛下若知,定当赞赏!”审讯官们发现,
这人嘴皮子比判词还利索。每句诗他都能圆出三个版本,一个比一个正能量。最绝的是,
他还会主动帮审讯官“分析”诗句:“大人,您看这句‘东风知我欲山行,
吹断檐间积雨声’,表面写景,实则表达对朝廷清正之风的向往东风就是陛下,
积雨就是小人!”李定听得头晕:“你……你别说了!
”苏轼诚恳:“要不要我再写一首颂圣诗?保证押韵!”审讯官们面面相觑这哪是犯人?
这是甲方爸爸在指导乙方改稿!
三、狱中社交:把审讯官发展成粉丝苏轼的“牢狱营销”不止于饭食和嘴炮。他发现,
乌台的狱卒、书吏,甚至低阶御史,其实都是他的读者。有人偷偷塞纸条进来:“苏学士,
您那首‘明月几时有’,我家小女天天唱,能再写一首吗?”有人借送水之机,
低声问:“听说您会做东坡肉?配方能说说吗?”就连主审官舒亶,某日审完案,
竟红着脸问:“那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下一句该怎么接?
我想写给我娘子……”苏轼眼睛一亮:“哦!那得看你是想表达‘无奈’还是‘豁达’。
若想浪漫点,可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若想务实点,就说‘不如回家吃饭,
今晚有红烧鱼’。”舒亶:“……后者更真实。”苏轼大笑:“那就选后者!诗要真,
情才深。”渐渐地,乌台监狱形成了奇异的氛围:白天审讯,晚上开文学沙龙。
苏轼甚至组织了一次“狱中诗会”,主题是《论如何在不冒犯皇帝的前提下说真话》。
参与者包括两名死囚、三个贪官、一个伪造文书的书生,以及……两名假装路过偷听的御史。
会上,苏轼金句频出:“讽刺要裹糖衣,牢骚要押韵脚。”“骂人不带脏字,才是高级黑。
”“写诗如炖肉,火候到了,味道自然来。”那名伪造文书的书生听得热泪盈眶:“苏学士,
我以后造假账,一定写得像您的诗一样美!”苏轼拍拍他肩:“不,你该去考进士。
”四、儿子送饭,暗藏生死密码苏轼入狱后,长子苏迈每日送饭。父子约定:若无事,
送菜肉;若有性命之忧,送鱼。此乃古代“牢狱暗号”鱼象征“覆水难收”,
也因“鱼”与“狱”音近,被视为不祥。二十多天过去,每日都是青菜豆腐,苏轼心渐安。
直到某日,苏迈因筹钱奔波,暂托亲戚代送。亲戚不知暗号,见市集有鲜鱼便宜,
便买了一条蒸了送去。苏轼掀开食盒,看见那条鱼,脸色瞬间惨白。“完了。”他喃喃道,
“他们要杀我。”那一夜,他辗转难眠,提笔写下两首绝命诗:“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第二首,是写给弟弟苏辙的。
字字泣血,却无一句怨恨。可第二天,狱卒来收碗,看见诗稿,竟没上报,
反而悄悄藏了起来。后来苏轼才知道:那狱卒,是他《赤壁赋》的铁粉。
连狱卒都舍不得他死,皇帝能下得去手吗?果然,几日后,神宗皇帝赵顼召见宰相王珪,
问:“苏轼……真该死?”王珪拿出苏轼那句“蛰龙”诗,强调“不臣之心”。
神宗沉默良久,忽然问:“他写过‘陛下圣明’吗?”王珪一愣:“……写过,
在《谢恩表》里。”神宗叹道:“那他骂人时,可有指名道姓?”“……无。”“那他诗中,
可有谋逆之语?”“……无。”神宗摆摆手:“那就不是死罪。顶多……流放。
”皇帝终究舍不得杀一个能把牢饭吃出花样的才子。尾声:出狱那天,
他问的第一句话是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获释,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不得签书公事。出狱那日,天寒地冻。苏迈扶着他走出乌台大门,父子相拥而泣。
围观百姓纷纷涌上,有人递热汤,有人塞炊饼。苏轼裹紧破旧棉袍,深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忽然转头问儿子:“家里……还有肉吗?”苏迈一愣:“有,但不多。
”苏轼眼睛亮了:“那今晚炖一锅!我要写《猪肉颂》终章‘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他顿了顿,
笑容温暖如春:“这一回,我要让全天下人都吃得上好肉。”第三章:黄州团练副使,
其实是“野生美食博主”当一个被贬官员开始养猪,北宋的美食史从此改写一、团练副使?
其实是“社区协管员”黄州,长江边的小城,湿热多雨,蚊虫成群。
苏轼的“团练副使”听着威风,
实则是个无权、无俸、无编制的虚职相当于今天的“社区志愿协管员”,
主要任务是“不得签书公事”,翻译过来就是:别说话,别写字,别惹事。
朝廷发的“安置费”刚够租个破屋。他一家二十余口包括仆人、侄子、远亲,
挤在临皋亭一间漏雨的茅屋里。第一天晚上,屋顶塌了半边,雨水顺着梁缝滴进饭锅。
苏轼没骂娘,反而笑:“正好省水,直接煮成粥了。”可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黄州米贵,
肉更贵但猪肉便宜得离谱。原来,北宋人以羊肉为尊,猪肉被视为“贱肉”,富人不屑吃,
穷人不会煮。导致满城肥猪,市价“价贱如泥土”。苏轼眼睛一亮:“天助我也!
”他立刻化身“北宋李佳琦”,在朋友圈其实是信件激情安利:“黄州好猪肉,
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待他自美时,人间真味足!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猪肉种草文案”。
二、东坡肉诞生记:一场失败的炖肉实验苏轼决定改良猪肉吃法。
他先试“爆炒”结果柴得像鞋底;又试“水煮”腥味冲天,猫都绕道走。直到某日,
他想起在乌台炖肉的经验:“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于是,他找来当地陶匠,
定制一口厚底砂锅;又向老农请教,得知黄州井水偏硬,
适合长时间炖煮;再从药铺买来陈皮、八角不对,北宋还没八角,
他用的是花椒、桂皮、甘草。最关键的一步:不放酱油,改用“酒糟+盐+糖”调色提鲜。
第一次实验,他炖了整整四个时辰。揭盖那一刻,满屋异香。肉块颤巍巍如琥珀,入口即化,
肥而不腻。邻居闻香而来,扒着墙头喊:“苏学士!开锅了吗?”苏轼大方分肉,
附赠“烹饪口诀”:“火要小,水要少,时间要够,心要静。”有人问菜名。
他望向窗外那片荒坡那是他新开垦的菜地,当地人称“东坡”。“就叫……东坡肉吧。
”一道名菜,就此诞生。但苏轼没申请专利,反而印了“菜谱”四处散发。
三、从养猪到酿酒:被贬官员的“副业帝国”猪肉好吃,但得有酒配。黄州酒贵,且多掺水。
苏轼一拍大腿:“自己酿!”他翻《齐民要术》,研究酿酒法,又向道士请教“曲药”配方。
结果第一锅酒酿出来,喝一口,酸得直皱眉。他不气馁,在笔记里写道:“吾造酒,味如醋,
人皆笑之。然吾不悔,因知酒之妙,在试错也。”第二年,他改良配方,
加入本地蜜枣与桂花,酿出“蜜酒”,清甜怡人。
他又开始种菜、养鸡、采药、制墨……甚至尝试做“豆腐”当时叫“黎祁”。
最离谱的是,他听说黄州有野蜂蜜,竟带着儿子苏过深入山林,差点被蜂群追下山。
苏过抱怨:“爹,您是来受罚的,不是来开农家乐的!”苏轼哈哈大笑:“贬谪是朝廷给的,
生活是自己造的。他们管得了我的官职,管不了我的舌头!”短短两年,
他在东坡建起“苏氏生态农庄”:猪圈、菜畦、酒窖、墨坊一应俱全。
当地百姓起初笑他:“堂堂翰林学士,竟干这等粗活?
”后来发现他养的猪不臭、酿的酒不酸、种的菜不虫,纷纷来取经。苏轼来者不拒,
还办了“东坡生活讲习班”,
主题包括:《论猪肉的108种死法》《如何用三文钱过一天》《被贬后,
如何优雅地活下去》他成了黄州第一“生活博主”,粉丝从农夫到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