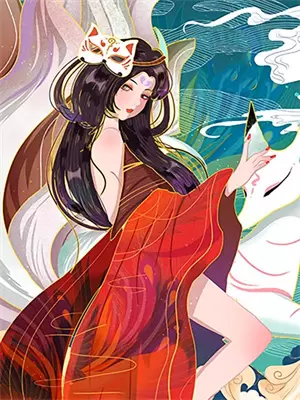1他是从一片尸体堆里醒过来的。不是梦。是真的。没有半点模糊。
左边是一块残破的混凝土墙板,压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女人,她的眼睛睁着,
脸上还挂着海水冲刷后未干的沙粒;右边,是一整块从便利店招牌撕裂下来的塑料壳,
硬生生穿透了一个男人的胸腔。沈予凡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双手发着抖,
嗓子像被海水灌满,干涩、咸腥、痛。他脑子一片空白,只知道自己还活着。可真希呢?
他猛地起身,跌跌撞撞地往镇中心跑去。风停了,但空气仍充满了死的味道。电线杆倾倒,
便利店屋顶卷成了麻花,水沟里泡着断手,塌掉的消防站下,有人正用铁锹挖尸体。
他跑到那幢小楼前,那是他们租住的木造小屋,两层。此刻只剩一面摇摇欲坠的墙壁。
他用脚踹开门板,冲进去,在瓦砾里翻找,撕破了手掌也没察觉。“真希!佐藤真希!
”没人回应。他突然想起,最后的记忆——她说,她要回房拿那本画册。“等我一下,
我的《春日回忆录》还在。”他拽着她的手,拼命摇头:“不行,真希!已经警报了!
”“你先走,真的很快,我知道放在哪。”她给了他一个笑,是那种温柔却让人抓不住的笑。
他松手了。他竟然松手了。沈予凡跪倒在地上,死命捶着地板,直到指骨渗出血。
他像个疯子一样翻遍了整栋房子的废墟,最后在厨房后方的角落,
看见了一截熟悉的白色衣角。他冲过去,用尽全身力气搬开横梁。是她。佐藤真希仰躺着,
脸侧有伤,嘴角带血,但她的双臂——双臂仍紧紧抱着那本被水泡烂的速写本。
“真希……”沈予凡瘫在她身旁,把她揽进怀里,她的体温早已散尽,像一尊潮湿的石雕。
他把头埋进她肩膀,失声痛哭。我和真希第一次见面,是在三年前。
那时我刚调来东京分部做项目协助,语言不通,孤身一人。雨天的涩谷街头,我在找出口,
她撑着一把红伞站在我面前。“你是沈予凡先生吗?”她的中文并不标准,但清晰。我点头。
她说:“你手机坏了,我们领导让我来接你。”她就是这样出现的,像一场细雨,从不打雷,
也不耀眼,只是静静地、默默地包围你。她是公司安排的兼职翻译,一周两次出勤。
她话不多,常常是我说一堆,她只微笑地点头。后来她跟我讲,
其实那时我日语烂得像婴儿乱叫,她根本听不懂一半,但看我认真,就忍住了笑。
我对她没什么男女之情,起初只是异国他乡的孤独缓解剂。直到有一天,
她帮我翻译完一个冗长的客户会议,累得瘫在长椅上。“你没吃饭?”她问。“嗯。
”她递给我一个饭团。“这个是我做的。”我愣住。“特意给你带的。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她在对我好,不是因为职责,而是因为喜欢。
我们是在第二年的春天确定关系的。她带我去新宿御苑赏樱,
成千上万的人在粉色花海下野餐、唱歌、接吻。我拎着一袋啤酒,她拎着画板,
一路走到人群最稀的河边。她铺开画纸,说:“坐下。”我坐下,她开始画我。
我问她:“你为什么突然要画我?”她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
“因为想把你记下来。”那一刻我心跳加速,像傻子一样盯着她。风吹起她的发,
她眯着眼笑。那笑容,比春天还温暖,比樱花还干净。我忍不住,凑过去,亲了她一下。
她也没躲。她轻声说:“你终于亲我了。”原来她等很久了。可我终究还是没抓紧她。
海啸那天,我明知道她执拗,却还是放她一个人回去。我以为我们还有以后,
以为风暴会给我们时间。可她是佐藤真希,一个会为了一幅画不惜生命的女人。
她不是为了画才回去,
留下那一年所有的日常——我们共处的小屋、窗边的猫、厨房的香气、我早上打哈欠的表情,
还有她最爱的樱花落在屋檐的模样。那是她活着的证据。而我,亲手松开了她的手。
沈予凡跪在地上,紧紧抱着她的遗体。天边终于放晴了,太阳从海面升起,
照亮这片被吞噬的土地。他低头看着她的脸,轻声说:“我会替你活下去,真希。
”“所有你想画的,我都会替你画完。”2真希的葬礼是在废墟中举行的。
棺材是用废木板拼成的,摆在一块临时搭建的平台上。没有寺庙,没有僧人,也没有仪式,
只是几个邻里街坊穿着泥泞的旧衣,在风里默默鞠了一躬。她的父母来了。
两位老人颤巍巍地跪在地上,替女儿给每个前来吊唁的人磕头。母亲泣不成声,
父亲却一滴眼泪也没流,只是一遍遍用粗哑的嗓音说:“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来看真希……”沈予凡站在最角落,指甲陷进掌心,沉默不语。
真希的速写本已经无法完整还原,那些泡烂的纸张在风中翻页,像是她轻声絮语,
又像是她在告别。一周后,沈予凡拒绝了回国的调令。“你疯了?”同事在电话那头愣住,
“你在那种地方还有什么留恋?东京本部能给你项目主设计的职位,升职加薪,
团队稳定……”“我不会回去了。”“你……是因为那个女孩?”他没回话。
他在宫城县的沿海小镇定居下来。住在救灾志愿者分配的集装箱里,吃方便面、罐头,
有时候一天能在重建工地上干十二个小时。没人理解他。他也懒得解释。第二年春天,
他去了那片早已被夷为平地的老宅旧址。那里现在什么都没有,连地基都被铲平了,
只剩一片光秃秃的沙地,和远处一块锈迹斑斑的路牌。沈予凡脱下外套,蹲下身,
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花种。是风信子的种子。那是她最喜欢的花,曾经说过,
“风信子是春天的眼泪,美得干净又忧伤。”他一颗颗种下去,指缝被沙子割出血。他不管,
只一遍遍地、机械地重复着。风吹来,他仿佛听见她的声音:“你很傻。”“你更傻。
”“可你终于学会种花了。”五月初,那年的第一场花开了。
风信子淡紫的花瓣在残垣之间缓缓摇曳,如同她的笑容,一点点,渗入这个破碎的世界。
沈予凡站在那片小花田前,久久不语。他从怀里拿出一个透明塑料壳,
里面装着一张勉强拼接完整的画。画里是他们两人坐在春日小屋的屋檐下,身后是满树樱花,
前方是一张铺着红格子布的野餐垫。他一笔一笔修补了整整八个月。现在,终于合上了。
第三年,他开始教镇上的孩子画画。镇上唯一的学校倒塌后,政府没再修。
他在一块废弃停车场支了个帐篷,摆上画架与课本,把它当成教室。每次画画前,
他都让孩子们画下“你想记住的一个瞬间”。有个孩子画了一碗饭,
说是地震前妈妈做的最后一餐。有个孩子画了一只狗,后来跑掉了。他每次看着那些画,
心都会沉下来,但嘴角却会笑。因为他知道——他们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忘记。第四年春天,
他重新设计了那个被毁掉的小镇。他不是建筑师了吗?他做了整整十年,
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新家?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把小镇分成三层:靠海是防波堤和花田,
中段是画室、教室、咖啡屋,最上方是一个高台,建了一座玻璃美术馆。那是他们约好的,
梦里的“山海画室”。画室落成那天,他没有剪彩,也没有邀请媒体。只是独自一人,
把画册摆进玻璃展厅,墙上写着一行字:她曾经活在春天里,后来我们都记住了她。
第五年的风信子,又开了。沈予凡穿着干净的白衬衣,走在花海中。他肩膀上驮着一个小孩,
那是镇上来访的记者的儿子,吵着要看“最美的画”。
他指着远处那个透明的展厅说:“她在那里。”孩子问:“她是谁?”他低头,微笑。
“是这个镇子上,最勇敢的人。”3沈予凡从没想过,自己会爱上这样一个女人。佐藤真希,
从不热烈,也不张扬。她说话轻轻的,走路也没有声音,喜欢把情绪藏在画里,
笑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像月牙一样温和。可只有他知道,她其实比任何人都固执。
刚在一起那年春天,他提议回国发展。她愣了一下,说:“那我们怎么办?”他还在犹豫,
说不出个所以然。真希点点头,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那天晚上,她画了一幅画。
画上是两只风筝,一只断了线,在云里飘远。另一只仍在原地,静静仰望。他看懂了。
可他装作没看懂。直到后来,她带他回老家。真希的家乡,在宫城县石卷市一个临海的小镇。
小镇不大,街道两旁是低矮的木屋和田地,夏天稻香四溢,海风咸咸的。
她的父母在镇上经营一家杂货铺,日子不富裕,但干净、安静。沈予凡第一次去,
是在一个傍晚。他一下车,就看见真希站在站台边,手里拎着一个饭盒,
里面是用紫苏叶包着的饭团,形状奇怪,但香得要命。她牵着他,一路从车站走到家,
路上经过小学、神社、海堤、渔港。她一边走,
一边像个孩子似的介绍:“那是我小时候画画的地方。”“那棵树下,我第一次被老师骂哭。
”“那边是我们以前养猫的屋子,它叫小团。”她的声音里藏着一种特别的情绪,是归属感,
是根系,是一个人真正属于某处的气味。沈予凡没说话。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她的世界,
不在东京,也不在他这里。她的世界,是这个小镇,是那一排排花木和那片安静的海。
她的父母很喜欢他。吃饭时父亲斟酒,母亲夹菜,说着蹩脚的中文笑着问:“你喜欢真希吗?
”他怔了一下,回答得很小声。“喜欢。”母亲笑了,父亲却只轻轻地叹了口气。那一夜,
真希和他在屋后看星星。“我爸妈年纪大了,其实希望我留在这里。”他嗯了一声。
“但我也知道,你不是会留下来的人。”她说这话时,头靠在他肩膀,声音轻得像风。
沈予凡突然就有点心慌。他不确定,她到底有没有怪他,还是只是单纯在描述一个事实。
他不敢问。他只是拉过她的手,十指紧扣。“我可以试着留下来。”她侧过头,看了他很久。
“真的吗?”他点头。“那你愿意陪我完成一个梦吗?”真希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画室。
不在东京,在她家乡的山坡上。她小时候常爬那座山,说从那里能看到整个小镇的屋顶,
春天能看见海浪边一整片樱花林,夏天能听见蝉鸣落在屋瓦上。
她把理想中的画室形状画下来,白色木墙,透明天窗,窗前是一圈旋转的书架,
最外层是一个能俯瞰海平线的小阳台。“我要在这里画画、教孩子们画画、种花、办展览,
还要把我的作品,全部挂在墙上。”“你呢?”“我就在你旁边工作,每天下班来接你。
”“你不会觉得无聊吗?”“你说了算。”她笑了。沈予凡没告诉她,那一夜,他失眠了。
不是因为焦虑,而是因为那种从未拥有过的、安稳又长久的愿景,太像梦了。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实现,但他很想试一次。他们在那片山坡上,埋下了第一根木桩。
是他画的草图,她补充的色彩。两人一边测量一边打闹,她用笔在他手背上画了一只兔子,
说是吉祥物。“这只兔子叫‘留留’,意思是‘留下来’。”他揽着她亲了一口。
“我留下了。”“真的吗?”她抬头,认真问。他犹豫了一秒,然后说:“真的。”她笑了。
那天夕阳很好,山脚下的海面闪着金光,远处的稻田像柔软的丝绸,
一切都像童话一样安静、美好。可童话总是太短。离开前那一晚,
她拿出那本还未完成的画册。“《春日回忆录》。”她轻声说。“我想画完它,然后,
就真正准备好了。”“准备什么?”她没回答,只是笑着看着他。“你会一直在吗?
”“我会。”他答得毫不犹豫。她抱住他,说了一句日语,他听不太懂,
只知道大概是“我相信你”。他亲了亲她的额头。那晚的风,也很好闻。
可他再也没等到那个画册画完的那天。4那天早晨的风,很不寻常。天是灰的,风是咸的,
海面却静得出奇,像一块按不下情绪的水银。镇上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
拉长的日语发音里混着杂音——“强震预警,请所有居民立刻前往高地避难。
”真希站在窗边,神情一瞬间空白。“是海啸。”她父亲冲进来,拽住她:“快!去山上!
带上你朋友!”沈予凡第一时间去收拾证件、食物与衣物。屋外已是一片混乱,
人们推着自行车、拉着老人、背着孩子,向山坡方向奔逃。警车在街道里穿梭,
扩音器喊破天。就在他准备好一切的时候,真希却停在门口,没有动。“我的画册。”她说。
“你疯了?!”沈予凡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现在就走!”“我要带上它。
”“你要命还是要那几张纸?!”她抬起头,眼里没有慌张,只有极度的清明。
“那不是几张纸,予凡。”“那是我二十六年的人生。”她说完,松开了他的手,
转身往楼上跑去。沈予凡踹翻椅子,跟着她冲上楼,逼着她快点收拾。真希打开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