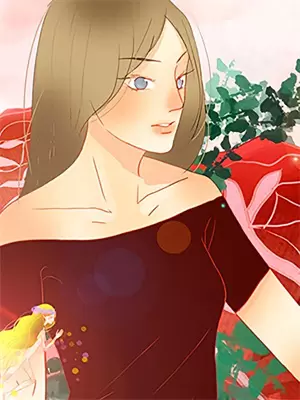
雨下得特别大。
砸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像要把玻璃都敲碎。我躺在床上,浑身湿透,被子黏糊糊地贴在身上。不是汗,就是雨水。这破房子的屋顶,又漏了。空气里一股子霉味,混着劣质消毒水的味道,熏得人头疼。
冷。刺骨的冷。
我动了动手指,骨头缝里都透着酸。这感觉,太熟悉了。死之前,也是这么冷。
死之前?
我猛地睁开眼。
天花板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边角都卷了起来,露出底下黑乎乎的霉斑。一盏昏黄的白炽灯吊着,灯绳晃晃悠悠。这不是我后来租的那个地下室。这是我……二十岁那年,喻家还没发达的时候,我和我妈挤着的那个老破小的阁楼间。
我,喻争,回来了?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撞,撞得我肋骨生疼。不是做梦。那股子刻进骨子里的绝望和冰冷,太真实了。上一秒的记忆,还停留在医院那间冰冷的单人病房里。消毒水味浓得呛人,仪器发出单调又刺耳的“嘀嘀”声。我浑身插满了管子,连抬根手指都费劲。床边站着的人,是我名义上的丈夫,陆明泽。
他穿着一身高定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俯视着我,眼神里没有半点温度,只有一种令人作呕的、高高在上的怜悯。
“阿争,别怪我。”他的声音平得没有一丝波澜,“你的气运,是上天赐给喻家的礼物。现在,它该回归了。”
回归?
我喉咙里嗬嗬作响,想骂,却只能挤出一点气音。我看着他那张英俊的脸,这张曾经让我迷恋、让我心甘情愿付出一切的脸。为了他,为了喻家,我像个傻子一样,把我妈留下的最后一点积蓄都填进了喻家那个无底洞的生意里;为了他,我日夜颠倒打工,把自己熬得人不人鬼不鬼,就为了供他那个所谓的“气运之子”弟弟喻飞,去国外镀金;为了他,我放弃了学业,放弃了所有朋友,把自己活成了喻家的一条狗,一个移动的、取之不尽的“气运”血包。
喻家是怎么发达的?靠我。
喻飞那个“气运之子”的名头是怎么来的?吸我的血!
陆明泽娶我,不是因为爱我,是因为只有我这种命格特殊、气运磅礴的人,才能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命,去供养喻飞,去维系喻家的“繁荣”。他娶我,是为了更方便地榨干我最后一点价值!
“飞飞刚签下了一个跨国大单,喻家需要更稳固的根基。”陆明泽的声音像淬了毒的冰锥,扎进我的耳朵里,“你的命格,你的气运,是最好的祭品。放心去吧,喻家会记得你的牺牲。”
牺牲?去他妈的牺牲!
我想尖叫,想撕烂他那张虚伪的脸。可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转身,对着旁边穿着奇怪袍子的老头点了点头。那老头嘴里念念有词,手里拿着一个黑漆漆的、像罗盘又像骨头的东西,朝我走过来。一股阴冷刺骨的力量瞬间攫住了我,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进骨头里,疯狂地抽取着什么。生命力,气运,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都在飞速流失。视线迅速模糊,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最后看到的,是陆明泽冷漠的侧脸,和窗外喻家灯火辉煌的别墅剪影。
不甘心!
蚀骨的恨意像毒藤,在心脏里疯长,缠绕得我几乎窒息。凭什么?凭什么他们踩着我尸骨享受荣华富贵?凭什么我要做那个被献祭的祭品?就因为我的气运旺别人?
冰冷的雨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涩得发疼。
我用力抹了把脸,挣扎着从那张湿透的、散发着霉味的破床上坐起来。环顾四周,狭小的空间堆满了杂物,墙上挂着一本老式挂历,上面的日期清晰地写着:2018年4月15日。
真的回来了。
回到了喻家刚刚靠着我的“旺夫运”和“旺家运”,搭上几个小项目,开始有点起色,但还没真正发达起来的时候。回到了我妈病重,急需一大笔手术费的时候。回到了陆明泽那个伪君子,还在我面前扮演深情款款、温柔体贴未婚夫的时候。回到了喻飞那个所谓的“气运之子”,还只是个眼高手低、靠家里供着的纨绔的时候。
也回到了,他们还没能彻底把我榨干、把我绑死的时候。
心脏还在狂跳,不是因为虚弱,而是因为一种近乎疯狂的兴奋在血液里奔涌。上辈子被抽干气运、在绝望中死去的痛苦和冰冷,此刻化作了最炽烈的燃料。
“呵……”一声低哑的冷笑从我喉咙里挤出来,在哗啦啦的雨声中显得格外诡异。
喻家。陆明泽。喻飞。
你们欠我的,该还了。
你们想要的气运?好啊。
这次,我主动“献祭”。
只不过,祭品是谁,由我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