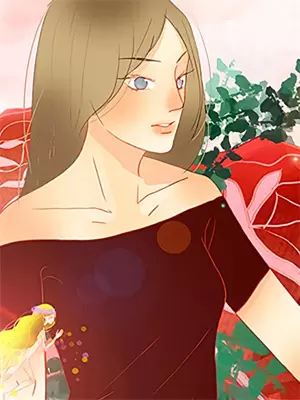
沈砚第一次见到陆明舒,是在昭和三十年的暮春。那天雨下得很大,青石板路被浇得油亮,
倒映着油纸伞的影子。他抱着怀里的古籍,小跑着躲进临街的茶寮,
雨珠顺着长衫下摆滴下来,在脚边积成小小的水洼。“先生,要杯雨前龙井吗?
”茶寮老板递过抹布,眼神落在他怀里的书册上,“又是去给顾先生送稿子?”沈砚点头,
刚接过抹布,就听见邻桌传来瓷器碎裂的脆响。穿月白旗袍的女子正弯腰捡茶杯碎片,
指尖被划破,殷红的血珠滴在青灰色裙摆上,像落了朵残梅。
她身后的男人一脸不耐:“明舒,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真是越来越笨了。”女子没说话,
只是将碎片拢进手帕,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沈砚注意到她耳后别着朵白玉兰,
雨水打湿了花瓣,却依旧透着清冷的香。“这位先生,能否借您的手帕一用?
”女子忽然抬头,声音像浸在溪水里的玉,清润却带着凉意。沈砚慌忙掏出手帕递过去。
她的指尖触到他的手,冰凉的,像刚从雨里捞出来。男人在一旁嗤笑:“陆明舒,
你还真把自己当大家闺秀了?一条手帕而已,值得这么客气?”女子没理他,
叠好手帕递回来,上面沾着几点血迹。“多谢。改日我清洗干净,再还您。”“不必了。
”沈砚看着她被雨水打湿的鬓角,“倒是您的手,需要处理一下。
”男人不耐烦地拽起她的手腕:“走了,别在这丢人现眼。”女子踉跄了一下,
回头看了沈砚一眼,目光里藏着些说不清的东西,像雨雾里的远山。
茶寮老板叹着气收拾残局:“那是陆老板的千金,嫁了个纨绔子弟,可惜了这副好模样。
”沈砚捏着那方沾血的手帕,忽然想起方才她耳后的白玉兰——听说陆家老宅的庭院里,
种着满城最好的玉兰树。二再见陆明舒,是在顾老先生的书房。她穿着素色旗袍,
手里捧着幅卷轴,站在书架前的样子,像幅被时光定格的工笔画。
顾老先生笑着介绍:“这是陆老板的女儿,明舒。她爹托我给她看看这幅《寒江独钓图》,
说是家传的宝贝。”陆明舒颔首致意,目光落在沈砚身上时顿了顿,显然也认出了他。
“沈先生。”“陆小姐。”沈砚低头整理书稿,指尖莫名发紧。顾老先生铺开画卷,
陆明舒站在一旁,轻声讲起画的来历:“这是我外祖父年轻时收的,
说是倪瓒的真迹……”她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眼神里有光,
和那日在茶寮里的落寞判若两人。沈砚忽然明白,她不是笨,
只是把锋芒藏在了温顺的表象下。看完画,陆明舒要走,外面却又下起了雨。
顾老先生让沈砚送她回家,“正好你们顺路,明舒住的陆家老宅,离你租的院子不远。
”雨丝斜斜地织着,两人共撑一把油纸伞,脚步声在巷子里格外清晰。
陆明舒的旗袍下摆扫过青石板,带起细小的水花。“那日在茶寮,多谢沈先生。
”她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举手之劳。”沈砚往她那边倾了倾伞,
“陆小姐的手……”“已经好了。”她抬手拢了拢鬓角,耳后的白玉兰换成了素银簪,
“倒是那方手帕,弄脏了,实在抱歉。”“不过是块帕子。”沈砚看着她被雨水打湿的睫毛,
“陆小姐不必放在心上。”走到陆家老宅门口,朱漆大门上的铜环被雨冲刷得发亮。
陆明舒站在门内,忽然说:“沈先生若不嫌弃,进来喝杯热茶吧?我爹种的雨前龙井,
味道不错。”沈砚犹豫了一瞬,点了点头。庭院里的玉兰树果然茂盛,雨水顺着花瓣滴落,
在青石板上敲出细碎的响。陆明舒端来茶盏,水汽氤氲了她的眉眼。“我爹常说,
沈先生是顾老先生最得意的门生,年纪轻轻就懂这么多古籍。”“陆小姐过誉了。
”沈砚捧着茶盏,暖意从指尖蔓延到心口,“倒是陆小姐,对书画的见解,很独到。
”她笑了笑,眼角有浅浅的细纹。“不过是从小听得多了。我爹总说,女孩子家学这些没用,
不如嫁个好人家。”她低头抿了口茶,声音轻得像叹息,“可我总觉得,这些笔墨里的东西,
比人心靠谱。”沈砚没接话。他想起那日茶寮里的男人,听说姓周,是商会会长的儿子,
仗着家里的势力,在外面横行霸道,对陆明舒更是非打即骂。雨停时,天边泛起淡淡的霞光。
沈砚起身告辞,陆明舒送他到门口,忽然从廊下折了枝玉兰递过来。“这个送您。
晒干了泡茶,很香。”玉兰花瓣上还沾着雨珠,清冽的香气钻进鼻腔。沈砚接过花枝,
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两人都顿了一下,像触电般缩回手。“多谢陆小姐。
”他低头看着那枝玉兰,心跳得有些乱。“沈先生慢走。”她转身回了院子,
素色旗袍的裙摆扫过门槛,像朵被风吹落的云。三自那以后,
沈砚去陆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有时是顾老先生托他送书稿,有时是陆明舒找他讨论书画,
更多的时候,是他借口路过,站在玉兰树下,看她坐在廊下看书。她总穿素色的旗袍,
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露出纤细的脖颈。阳光透过玉兰花瓣落在她脸上,像撒了层碎金。
沈砚会坐在不远处的石凳上,假装看书,眼角的余光却总追着她的身影。
周少爷来的次数也多,每次来都带着酒气,说话粗声粗气。有次他看到沈砚,
当即翻了脸:“陆明舒,这穷酸书生怎么总在你家?你是不是背着我勾三搭四?
”陆明舒把沈砚护在身后,声音冷得像冰:“周志安,沈先生是我家的客人,
你说话放尊重点。”“客人?”周志安一把推开她,伸手就要打沈砚,“我看是奸夫淫妇!
”沈砚没躲,拳头落在他脸上时,他听见陆明舒尖叫着扑过来。混乱中,
周志安的指甲划破了她的胳膊,旗袍袖子瞬间洇出片血迹。“够了!”陆明舒挡在沈砚面前,
脸色苍白如纸,“周志安,你再这样,我就去告诉你爹!”周志安怕了,骂骂咧咧地走了。
沈砚看着她胳膊上的伤,心口像被堵住了:“为什么要护着我?”“你是我家的客人。
”她咬着唇,不让眼泪掉下来,“再说,是他不对。”沈砚替她包扎伤口时,
指尖忍不住发颤。她的皮肤很白,伤口像道狰狞的红痕。“陆小姐,你不该这么委屈自己。
”她笑了笑,笑声里全是无奈:“沈先生,这世道,女子哪有不委屈的?
我爹需要周家的势力,我……不过是枚棋子。”那天沈砚离开时,玉兰花瓣落了满地,
像场盛大的告别。他忽然很想带她走,带她离开这座困住她的牢笼,去看真正的山河湖海。
可他只是个穷书生,连自己的温饱都勉强维持,又能给她什么呢?初夏的时候,
顾老先生去世了。葬礼那天,陆明舒来了,穿着一身黑衣,脸上没施粉黛,却更显清丽。
她站在沈砚身边,递给他一方手帕:“顾老先生常说,你是个好孩子,只是性子太直。
”沈砚接过手帕,上面绣着株兰草,针脚细密。“是陆小姐绣的?”“闲着无事做的。
”她低下头,“顾老先生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葬礼结束后,
沈砚收到了顾老先生的遗嘱,说要把书房里的那些古籍都留给她。他去收拾书时,
陆明舒也来了,帮他整理那些泛黄的纸页。“这些书,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找个地方存起来,慢慢整理。”沈砚看着满室的书,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或许……我会离开这里,去北平看看。听说那里有很多古籍研究的学者。
”陆明舒的动作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北平很远吧?”“嗯,要坐很久的火车。
”沈砚看着她,“陆小姐……要不要一起去?”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他凭什么邀请她?
她是有夫之妇,就算过得再不好,也不是他能随便带走的。陆明舒沉默了很久,
久到沈砚以为她没听见,她才轻轻摇了摇头:“我走不了。我爹年纪大了,陆家还需要我。
”她从袖中拿出个小小的锦盒,“这个送你,算是……饯别礼。”锦盒里是半块玉佩,
青白色,上面刻着朵玉兰。“这是我娘留下的,说是能辟邪。”她把玉佩放在他手里,
指尖的温度烫得他心头发颤,“沈砚,到了北平,好好生活。”他想说些什么,
喉咙却像被堵住了。只能握紧那半块玉佩,看着她转身离开,黑衣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像滴墨融进了宣纸。四沈砚去北平的那天,陆明舒没来送他。他在火车站等了很久,
直到火车鸣笛,才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车开的时候,他看见站台上有个穿黑衣的身影,
手里攥着块手帕,像株被风吹得发抖的玉兰。北平的日子很忙,
他在图书馆找了份整理古籍的工作,闲暇时就去拜访那些学者,
日子充实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半块玉兰玉佩被他系在腰间,时常摩挲,
边缘都磨得光滑了。偶尔收到老家朋友的信,说周志安依旧混账,陆明舒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陆家的生意也大不如前。每次看到这些,沈砚的心就像被浸在冰水里,又冷又沉。
三年后的冬天,他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字迹娟秀,是陆明舒的。信里说,
周志安在外面赌钱输了精光,把陆家的产业都抵押了出去,她爹气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
还说,她把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都当了,凑了些钱,想送她爹去北平治病,
问他能不能帮忙找个住处。沈砚看完信,连夜请了假,买了回南方的火车票。
车窗外的雪景一闪而过,他的心却像被火烧着,恨不得立刻飞到她身边。回到老家时,
正是深冬。陆家老宅的大门上了锁,铜环生了锈,院子里的玉兰树落光了叶子,
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邻居说,陆家早就搬走了,陆老板病重,
陆明舒带着他去了北平,临走前还问起过他。沈砚的心沉到了谷底。他在老宅门口站了很久,
雪花落在他的肩头,像落了层霜。他忽然想起她信里的话,原来她真的来了北平,
只是他不知道她在哪里。回到北平后,沈砚四处打听陆明舒的消息。他去医院问,去客栈问,
甚至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却都石沉大海。日子一天天过去,
他腰间的玉佩被摩挲得越来越亮,心里的希望却一点点熄灭。春暖花开的时候,
他在医院给一位老先生送整理好的古籍,路过病房时,听见里面传来熟悉的咳嗽声。
他停下脚步,心跳得像要炸开。推开门,看见陆明舒正给病床上的老人喂药,
鬓角多了几缕银丝,眼角的细纹也深了些,却还是他记忆里的模样。她抬头看见他,
手里的药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沈砚……”她的声音发颤,
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沈砚走到她面前,伸手替她擦去眼泪,指尖触到她的皮肤,
依旧是冰凉的。“我回来了。”五陆老板的病渐渐好了起来,只是身体大不如前。
沈砚把他们接到自己租的院子里,院子里也种着棵玉兰树,是他去年刚栽的。
陆明舒白天去医院照顾父亲,晚上回来就帮沈砚整理古籍。她的字写得好,
抄录的文稿工整秀丽,沈砚看着那些字,总觉得像在看一幅画。周志安没来找过麻烦,
听说他把家产败光后,就跟着一个戏班子跑了,再也没回来。陆明舒提起他时,
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仿佛那些委屈和痛苦,都随着岁月淡忘了。初夏的一个傍晚,
玉兰花开得正盛。沈砚在灯下整理书稿,陆明舒坐在对面缝补衣服,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
落在两人身上,温柔得像场梦。“沈砚,”她忽然开口,“我这里有样东西,该还给你了。
”她从箱底翻出个锦盒,打开一看,是另一半玉兰玉佩。“当年我娘把玉佩分成两半,
说若是遇到真心待我的人,就把这半块给他。”她把玉佩放在沈砚手里,
“周志安从来没见过这个,我一直留着。”沈砚把两块玉佩拼在一起,严丝合缝,
像从来没分开过。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指尖终于有了温度。“明舒,
我们……”“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她打断他,脸上泛起红晕,
“只是我爹……”“陆伯父那边,我去说。”沈砚看着她的眼睛,“明舒,这些年,
我心里一直有你。”陆明舒的眼泪掉了下来,落在玉佩上,折射出温润的光。“我也是。
”陆老板并没有反对。他拉着沈砚的手,叹了口气:“是我对不起明舒,让她受了这么多苦。
以后,你要好好待她。”他们的婚礼很简单,请了几个相熟的朋友,在院子里摆了两桌酒席。
陆明舒穿着沈砚给她做的新旗袍,天蓝色的,上面绣着玉兰花纹,是他亲手描的样子。
她站在玉兰树下,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细纹里都盛着光。沈砚看着她,
忽然想起初遇那天的雨,想起茶寮里的血迹,想起火车站的背影。
那些艰难的、痛苦的、思念的日子,仿佛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婚后的日子平淡却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