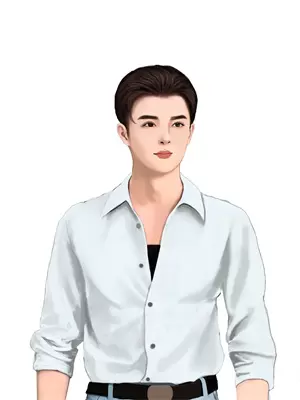1977年夏末,京城胡同里的蝉鸣还带着股韧劲,把午后的日头拽得老长。
西四牌楼附近的四合院里,青砖灰瓦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墙根下几盆指甲花开得热闹,
红的粉的,倒把斑驳墙皮衬得鲜活了些。沈聿年刚从部队回省亲,
穿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流畅的肌肉线条。
他刚帮邻居张大爷修好了吱呀作响的院门,回自家院打算歇口气,
手里还捏着块没吃完的绿豆糕——出门时他妈塞的,说他在部队总吃不上这些精细东西。
二十九岁的人,肩上扛着团长的星,在北疆待了快十年,性子磨得像院里的老青砖,
沉稳内敛,极少有什么事能让他动容。可此刻,眼皮忽然不受控制地跳,
一股莫名的燥热顺着后颈爬上来。没等细想,院门口那方天空突然亮了。
不是太阳那种暖融融的光,是极亮极绚目的流光,像打翻了天上的调色盘,
赤橙黄绿青蓝紫绞成一团,带着点微烫的气浪,“轰”地砸进院子,正好落在他面前三步远。
强光刺得沈聿年猛眯起眼,下意识抬手挡了挡。耳边像有蜂鸣,等炫目的光慢慢褪去,
他放下手,喉咙忽然像被什么堵住,连呼吸都忘了。光里站着个姑娘。
沈聿年自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后来走南闯北,见过不少漂亮姑娘,可眼前这一位,
让他脑子里所有形容样貌的词都成了摆设。她穿的裙子从没见过,不是的确良也不是棉布,
料子像过年时供销社柜台里锁着的绸缎,却比绸缎亮得多,泛着珍珠母贝般的光泽,
随她轻微动作流动着细碎光斑,像是把一整个星空披在了身上。更惊人的是她的脸。
眉如远山含黛,眼若秋水横波,鼻梁挺翘得恰到好处,唇色是天然的粉嫩,像刚摘的樱桃。
皮肤白得像上好的羊脂玉,在刚褪去的霞光里几乎要透明,连绒毛都看得清。身段高挑匀称,
那身流光溢彩的裙子勾勒出的曲线,让沈聿年这样定力十足的军人都忍不住红了耳根,
慌忙移开视线,又忍不住偷偷瞟回去。这哪是凡间的姑娘?沈聿年脑子里只剩这一个念头。
他奶奶信佛,常跟他讲天上仙女的故事,说仙女踩着云彩来,浑身带光。眼前这情景,
可不就跟奶奶说的一模一样?那光,那衣裳,
那张美得让人不敢直视的脸……姑娘似乎还没缓过神,
眨了眨那双清澈得能映出人影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像蝶翼般扇了扇,
眼神里满是茫然和惊恐。她看了看周围灰扑扑的院墙,
又看了看捏着绿豆糕、穿旧衬衫的沈聿年,小嘴微张,像有无数问题想问,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你……”沈聿年喉结动了动,声音有些干涩,
“你是……”想问“你是谁”,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万一真是仙女呢?问得唐突了,
怕是要得罪天上的神仙。姑娘听到他的声音,身子轻轻抖了下,像受惊的小鹿。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裙子,又抬头望了望被四方院墙框住的一小块天空,眼圈忽然红了。
豆大的泪珠滚下来,砸在胸前衣襟上,顺着那些流光溢彩的纹路滑下去,
瞧着竟有些让人心疼。“我……我不知道……”她的声音软软糯糯的,像浸了蜜的泉水,
带着点哭腔,“我刚才还在……怎么一下子就到这儿了……”沈聿年这才注意到,
她说话的腔调跟京片子不一样,也不是他听过的任何地方口音,软乎乎的,
有种说不出的好听。他心里更确定了几分——这姑娘绝非凡人。凡间哪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声儿?他站起身,尽量让语气温和些,动作也放缓了,怕吓着她:“别怕,
这儿是我家,安全得很。你……是不是迷路了?”这话问得他自己都觉得别扭。
仙女还会迷路?姑娘摇摇头,又点点头,
眼泪掉得更凶了:“我不认识这儿……我想回家……”沈聿年看着她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
心里那点对“仙女”的敬畏,渐渐被怜惜取代。不管她从哪儿来,看样子年纪不大,
又是孤身一人,肯定吓坏了。他把手里的绿豆糕往旁边石桌上放了放,
指了指自己刚坐的竹椅:“先坐下歇歇吧,天热,别中暑了。”姑娘犹豫了下,
看沈聿年虽高大英挺,眼神却正直,不像坏人,便慢慢挪到竹椅边坐下。裙摆散开时,
那些流光在灰暗的院子里格外扎眼,连墙根下的指甲花都像被比得没了颜色。
沈聿年站在一旁,看她小心翼翼地坐着,双手不安地绞着裙摆,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
爹妈和小妹沈聿月去前院李婶家借绣花线了,估计也快回来,要是看到这姑娘,
指不定得惊成什么样。得先想办法把人留住,再慢慢弄清楚情况。这么个“仙女”似的人物,
让外人看到了,指不定传出什么闲话,万一被当成特务或精神有问题的送到派出所,
就麻烦了。正想着,院门外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妈,你说李婶那线够不够红啊?
我想给聿年哥绣个红牡丹在枕头上。”是小妹沈聿月的声音,透着活泼。“够够的,
你李婶那线是她闺女从上海捎来的,颜色正着呢。”这是他妈王秀兰的声音,带着爽朗。
接着是钥匙开门的声儿。沈聿年心里一紧,赶紧朝姑娘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别说话。
门“吱呀”开了,王秀兰和沈聿月一前一后走进来,手里还拿着个装绣花线的小纸包。
“聿年,歇着呢?”王秀兰抬头就看到院子里的儿子,随即目光落在竹椅上的姑娘身上。
下一秒,王秀兰手里的纸包“啪嗒”掉在地上,绣花线撒了一地。沈聿月也张大了嘴,
眼睛瞪得溜圆,半天没合上。
娘俩的反应跟沈聿年刚才如出一辙——被这姑娘的样貌和打扮惊得说不出话。
“这……这是……”王秀兰指着姑娘,又看看儿子,一脸难以置信。沈聿年赶紧走过去,
挡在姑娘身前,低声对他妈和小妹说:“妈,小月,先进屋说。”他怕娘俩咋咋呼呼的,
再吓着这位“仙女”。王秀兰和沈聿月这才回过神,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和好奇。王秀兰赶紧捡起地上的线,
沈聿月一步三回头地跟着往正房走,眼睛直勾勾盯着竹椅上的姑娘,像看什么稀世珍宝。
进了屋,沈聿年把门掩上,简单说了说刚才的情况,没提自己觉得对方是仙女的事,
只说这姑娘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受了惊吓,什么都不记得了。“老天爷!”王秀兰拍着大腿,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姑娘穿的啥呀?也太好看了吧!”“哥,她是不是从外国来的?
”沈聿月好奇地问,“我在画报上见过外国人穿得花里胡哨的,可没她这么好看!
”沈聿年摇摇头:“不知道,她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问啥都只哭。
”王秀兰一听就心软了:“可怜见的,这么小的姑娘,肯定是遇到难处了。不管咋说,
先把人留下,总不能赶出去啊。”她想了想,又说,“可她这身份……没有介绍信,
没有户口,咋在这儿待着?万一被查着了……”70年代的京城管理严,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确实是个大麻烦。沈聿年皱着眉,心里已有了主意。他在部队待了这么多年,
这点门路还是有的。先给姑娘办个临时身份证明,就说是远房亲戚,家里遭了灾来投奔的。
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落户口。“妈,你别担心,身份的事我来办。”沈聿年沉声道,
“她一个姑娘家,无依无靠的,咱们不能不管。”王秀兰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
点了点头:“你说得对。这姑娘看着就不是坏人,瞧着那模样,
那气质……说不定真是个有福气的。”她忽然凑近沈聿年,压低声音,“儿子,
你看这姑娘……”沈聿年知道他妈想说啥,脸微微一热,赶紧打断:“妈,先别说这个,
把人安顿好再说。”他转身往外走,想再去看看姑娘怎么样了。刚到门口,
就见沈聿月蹲在竹椅旁边,仰着小脸跟姑娘说话,那股子好奇劲儿,
像是要把人家从里到外看个遍。姑娘似乎不那么怕了,正小声回答着沈聿月的问题,
脸上还挂着泪痕,眼神却清澈了些。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她绝美的脸上,
光影交错,美得像幅画。沈聿年站在门内,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这道流光,不仅带来了天上的“仙女”,也给这平静的四合院,带来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他深吸一口气,不管以后会怎么样,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得让这位“仙女”在凡间,
有个安身之处。王秀兰是个麻利人,心里有了主意,手脚就快了。她拉着沈聿月进东厢房,
翻箱倒柜找出自己年轻时做的蓝色卡其布褂子和灰色裤子,又找了双半旧的布鞋,
拍了拍上面的灰:“先让姑娘换上吧,她那身衣裳太扎眼了,出去准得被人围观。
”沈聿月拿着衣裳,蹦蹦跳跳跑到院子里,递过去,笑得一脸灿烂:“姐姐,
我妈让你换身衣裳,你那裙子太好看了,穿出去会被好多人看的。
”姑娘看了看那身灰扑扑的布衣裳,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流光溢彩的裙子,
眼神里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接了过来,小声道了谢。
沈聿月领着她去院子角落的洗澡间——那是沈家前年加盖的,用砖头砌的,
里面放着个大木盆,平时烧水洗澡都在这儿。“姐姐,你就在这儿换吧,
我给你烧点水擦擦身子?”“不用不用,”姑娘赶紧摆手,“我自己来就行,谢谢你。
”等姑娘换好衣裳出来,沈聿年和王秀兰都愣了一下。卡其布褂子和灰裤子是最普通的样式,
王秀兰年轻时比姑娘矮些,裤子还短了一截,露出纤细的脚踝。可穿在这姑娘身上,
硬是穿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布料虽粗糙,却掩不住玲珑有致的曲线,
领口松松垮垮露出一点白皙脖颈,更显得肤白胜雪。那张脸没了华服映衬,
反而更突出本身的绝色,素净中带着惊心动魄的美。“真……真好看……”王秀兰喃喃道,
心里越发喜欢,这姑娘真是穿啥都好看,天生的衣架子。沈聿年也觉得,褪去一身流光后,
她少了些“仙气”,多了些人间的鲜活,看着更让人亲近了些。“还没问姑娘你叫啥呢?
”王秀兰拉着姑娘的手,她的手粗糙,带着做惯了家务的薄茧,姑娘的手却软得像棉花,
滑溜溜的,让她都舍不得松开。姑娘愣了愣,
似乎在努力回忆:“我……我好像叫……林书昀。”“林书昀?”王秀兰念叨着,
“这名字好听,书香气十足,跟你人一样文雅。”她又问,“家里还有啥人?家在哪儿啊?
”林书昀的眼神又黯淡下去,
摇了摇头:“不记得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王秀兰一看她又要哭,
赶紧打住:“想不起来就不想了,没关系,先在婶儿家住着,啥时候想起来了再说。
”沈聿年在一旁听着,心里有了数。他起身道:“妈,我去趟街道办和派出所,
给书昀办个临时证明。”“哎,好,”王秀兰点头,“路上小心点,跟人家好好说。
”沈聿年走后,王秀兰拉着林书昀在屋里说话,问她饿不饿。林书昀确实饿了,
刚才惊吓过度没感觉,这会儿放松下来,肚子就咕咕叫了。王秀兰一听,乐了:“饿了就好,
饿了就有救。”她系上围裙,“婶儿给你做碗鸡蛋面,咱家常便饭,你别嫌弃。”厨房里,
王秀兰烧着火,沈聿月在一旁帮忙剥蒜。林书昀也想帮忙,
却被王秀兰按住了:“你坐着歇着,看你细皮嫩肉的,肯定没干过这些活。
”林书昀确实没干过。她以前住的地方,做饭都有专门的人打理,哪里见过这种烧煤的灶台?
看着王秀兰熟练地添煤、拉风箱,火苗“呼呼”地舔着锅底,她觉得新奇又陌生。不一会儿,
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端上了桌。粗瓷大碗里,卧着两个金黄的荷包蛋,面条是手擀的,
带着韧劲,汤里飘着葱花和香油,热气腾腾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林书昀看着这碗面,
愣住了。她以前吃的东西,摆盘精致,用料讲究,却从没见过这样简单朴实,
却又透着股暖意的食物。“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王秀兰催着她。林书昀拿起筷子,
学着王秀兰的样子夹了根面条,吹了吹送进嘴里。面条筋道,带着麦香,汤是骨汤熬的,
鲜得恰到好处。她眼睛一亮,又夹了口鸡蛋,蛋黄是半流心的,抿一口,满口都是蛋香。
她吃得很慢,却很认真,一小口一小口地,把一碗面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脸颊也变得红扑扑的,看着更像个活生生的人了。“好吃吗?
”沈聿月凑过来问。林书昀用力点头,眼睛亮晶晶的:“好吃!比我以前吃的都好吃!
”这话是真心的。以前的食物再精致,也吃不出这种带着烟火气的温暖。
王秀兰笑得合不拢嘴:“好吃就多吃点,以后婶儿天天给你做。”下午三四点,
沈聿年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临时身份证明。他找了街道办的老同学,编了个理由,
说林书昀是他远房表妹,家乡遭了水灾,家里人都没了,一路投奔过来,路上受了惊吓,
好多事记不清了。那同学跟他关系铁,又看他是部队干部,信得过,没多问就给办了。
“办好了,”沈聿年把证明递给林书昀,“暂时先这样,等回头我再想办法把户口落下来。
”林书昀接过那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她的名字“林书昀”,年龄二十一岁,
籍贯是邻省一个偏远县城,关系栏里写着“沈聿年表妹”。看着这张纸,
她心里忽然有了点踏实的感觉,好像自己终于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有了一个“身份”。
“谢谢你。”她抬头看着沈聿年,眼神里满是感激。沈聿年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
移开视线:“不用谢,既然到了我家,就安心住着。”晚饭时,沈父沈建国回来了。
沈建国是机床厂的老工人,话不多,但为人正直。看到林书昀时,他也惊了一下,
听王秀兰说了情况,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留下吧,都是可怜人”,就没再多问,
只是吃饭时,总忍不住往林书昀碗里夹菜。一家人围着小方桌吃饭,灯光昏黄,
映着每个人的脸。林书昀看着沈聿年沉稳地给父母盛汤,看着沈聿月叽叽喳喳讲厂里的趣事,
看着王秀兰不停给自己夹菜,看着沈建国默默喝酒,心里那点漂泊无依的恐慌,
渐渐被一种叫做“家”的温暖填满了。饭后,沈聿月拉着林书昀去她的房间睡。
沈聿月的房间不大,墙上贴着《地道战》的海报,书桌上堆着几本课本和连环画。
林书昀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闻着被子上阳光和肥皂的味道,
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咳嗽声和说话声,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回去。但至少现在,
她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有一群愿意接纳她的人。窗外,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
落在林书昀恬静的脸上。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嘴角微微向上翘了翘。正房里,
沈聿年刚洗漱完,王秀兰就凑了过来,压低声音问:“儿子,你觉得书昀这姑娘咋样?
”沈聿年擦头发的手顿了顿:“挺好的,懂事。”“就光懂事啊?”王秀兰白了他一眼,
“你都二十九了,跟你一样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看林书昀这姑娘,人长得好,
性子看着也温顺,又是你表妹虽然是编的,知根知底的……”沈聿年知道他妈想说啥,
脸一热:“妈,你别瞎想,人家刚过来,还不稳定呢。”“我咋是瞎想了?
”王秀兰不依不饶,“你看你爸多喜欢她,小月跟她也好得跟亲姐妹似的。
这姑娘一看就是有福气的,跟你站在一块儿,多般配!”沈聿年没说话,
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林书昀那张绝美的脸,想起她哭鼻子时委屈的模样,
想起她吃面条时满足的眼神……他摇了摇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开。
她是“仙女”一样的人,自己是个糙汉子,怎么可能般配?可不知怎的,闭上眼睛,
眼前却总是晃着那道落在院子里的流光,和流光里那个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的姑娘。
林书昀在沈家住了下来,开始学着适应这个全然陌生的年代。王秀兰怕她闷,
每天出门买菜、去合作社扯布,都乐意带着她。一开始,
林书昀总被街上的景象惊到——灰扑扑的街道,穿着蓝、灰、军绿色衣裳的人群,
自行车叮铃铃地穿梭,墙上刷着醒目的红色标语,供销社门口排着长队,
人们手里捏着各种票证,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这些都跟她以前的生活截然不同。
她以前想买什么,只需要动动手指,自然有人送到面前,
哪里见过这样精打细算、什么都要凭票的日子?“这布票啊,是按人头分的,
一年就那么几尺,做件褂子就差不多了。”王秀兰拿着布票,
在供销社柜台前跟售货员熟稔地打招呼,“给我来块深灰色的,做条裤子。
”林书昀站在一旁,看着柜台里那些颜色单调、款式陈旧的布料,
再想想自己以前挂满衣帽间的华服,心里有些怅然,却也没说什么。她知道,
现在不是讲究这些的时候。回到院里,邻居们都知道沈家来了个远房表妹,
长得跟画里的人似的。一开始还有些好奇,总借着送东西、借工具的由头来看看,
每次都被林书昀的长相惊得直咋舌。但林书昀性子温和,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嘴巴又甜,
“张大爷”“李婶”地叫着,手脚也勤快,见谁忙不过来就搭把手,时间长了,
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只当沈家这表妹是个有福气的,生了副好皮囊。
林书昀跟着王秀兰学做家务。一开始连扫地都扫不利索,扫帚在她手里像有了自己的主意,
东一下西一下,弄得尘土飞扬。王秀兰看着好笑,也不催她,
耐心地手把手教:“扫地要顺着一个方向,慢慢扫,别急。”学择菜的时候,
她更是闹了笑话,把菠菜叶扔了,留着菜根,还振振有词:“这个根看着不好吃啊。
”逗得王秀兰和沈聿月哈哈大笑。“傻姑娘,菠菜就是吃叶子的,根得扔掉。
”王秀兰笑着给她纠正,“你呀,以前在家肯定是个娇小姐,啥活都不用干。
”林书昀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她确实是娇小姐,以前别说择菜了,连菜长啥样都认不全。
沈聿年在家的日子不多,每天要么帮着家里干点重活,要么就去部队看看老战友。
但他总能在不经意间看到林书昀忙碌的身影——她蹲在院子里择菜,
阳光照在她认真的侧脸上;她跟着王秀兰学纳鞋底,针扎到手,疼得龇牙咧嘴,
却还是咬着牙继续;她帮沈聿月复习功课,
耐心地讲解着那些她觉得很简单的算术题……看着她一点点褪去身上的“仙气”,
变得越来越像个普通的邻家姑娘,沈聿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不再觉得她是高高在上的仙女,只觉得她是个需要人疼、需要人照顾的小姑娘。这天傍晚,
沈聿年从外面回来,刚进院门,就闻到一股焦糊味。他皱了皱眉,快步走进厨房,
就看到林书昀正对着一口黑乎乎的锅手足无措,脸上还沾了点烟灰,像只小花猫。“怎么了?
”沈聿年走过去。林书昀看到他,脸一下子就红了,带着哭腔:“我想给大家熬点粥,
结果……结果就成这样了……”锅里的米已经变成了黑乎乎的一团,糊味呛得人难受。
沈聿年忍着笑,接过她手里的锅铲:“没事,我来吧。你去洗洗脸。”他把糊锅端出去倒掉,
重新刷了锅,添了水,架在火上。等水开了,抓了把米放进去,又切了点红薯块扔进去,
慢慢搅着。林书昀洗了脸,站在一旁看着他熟练的动作,小声道:“对不起,
又给你添麻烦了。”“没事,谁还没个第一次。”沈聿年头也没抬,“熬粥要小火,
得时不时搅一下,不然容易糊底。”“哦。”林书昀乖乖应着,看着他专注的侧脸,
心里有些暖暖的。这个男人虽然话不多,却总是在她需要的时候出现,
默默地帮她收拾烂摊子。粥熬好了,稠稠的,带着红薯的甜味。
王秀兰和沈建国、沈聿月回来,闻着香味就凑了过来。“还是聿年熬的粥好喝。
”王秀兰盛了一碗,咂咂嘴,“书昀啊,以后做饭这事,你慢慢学,不急。”林书昀点点头,
看着沈聿年端起碗喝粥,嘴角还沾了点米粒,她忍不住想笑,又赶紧忍住了。晚上,
沈聿月拉着林书昀在院子里乘凉,指着天上的星星给她看:“书昀姐,你看那颗星星最亮,
我妈说那是织女星。”林书昀抬头看着满天繁星,心里忽然有些想家。她以前住的地方,
夜空总是被霓虹灯映得灰蒙蒙的,很少能看到这么多这么亮的星星。“真好看。”她轻声说。
“是呀,”沈聿月叹了口气,“就是我哥要走了,他假期快结束了。
”林书昀心里一动:“沈大哥要走了?”“嗯,后天就回部队了。”沈聿月有些舍不得,
“他在北疆,一年才回来一次。”林书昀没说话,心里有些失落。
她在这里最熟悉、最依赖的人,就要走了。那她以后怎么办?沈聿年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主动开口:“我回去的时候,你跟我一起走吧。
”林书昀愣住了:“跟你一起?”“嗯,”沈聿年点头,“你在这儿也没什么亲人,
跟着我去部队那边,有个照应。部队大院里都是家属,环境也单纯。
”王秀兰和沈建国也觉得这主意好:“对对,跟着你哥去部队好,省得我们担心。
”“到了那边,让你哥给你找个轻松点的活干,也能自食其力。”林书昀看着沈聿年,
他眼神真诚,不像在开玩笑。她想了想,点了点头:“好,我跟你走。
”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她知道,跟着沈聿年,总比一个人留在这里要好。
沈聿年看着她点头,心里松了口气。他其实早就想好了,把林书昀一个人留在京城,
他不放心。带在身边,至少能照看着。出发前一天,王秀兰拉着林书昀去供销社,
用攒了很久的布票和钱,给她做了两套新衣裳,一套蓝色的,一套灰色的,还买了双新布鞋。
“到了部队,别让人看不起,穿得整齐点。”王秀兰一边给她收拾行李,一边念叨着,
“跟你沈大哥好好相处,他那人看着冷,心热。
”沈聿月则偷偷塞给林书昀一本连环画:“书昀姐,想我们了就看看这个,
上面有我画的小像。”林书昀看着手里的新衣裳和连环画,眼圈又红了。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她对这个家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沈建国话不多,只是默默地给她塞了个布包,
里面是几块钱和一些粮票:“拿着,路上用。”林书昀哽咽着说了声“谢谢叔叔阿姨,
谢谢小月”,把这些温暖都记在了心里。第二天一早,沈聿年带着林书昀离开了四合院。
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胡同里静悄悄的,只有他们的脚步声。
林书昀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灰扑扑的四合院,看了看门口那棵老槐树,
心里暗暗说:我还会回来的。沈聿年似乎察觉到了她的不舍,放慢了脚步,
轻声道:“以后放假,我带你来看看。”林书昀点点头,跟上他的脚步,朝着胡同口走去。
那里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将带着他们驶向一个全新的地方,一个充满未知,
却也充满希望的未来。吉普车驶出京城,一路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