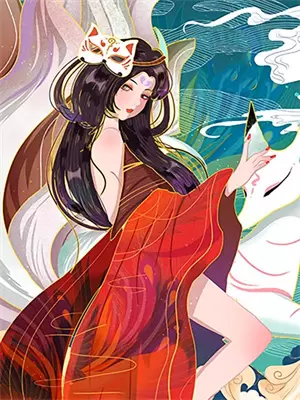北京798艺术区,深夜十一点四十七分。剪辑室的显示器散发的冷光像手术刀,
剖开我尘封的硬盘。屏幕上是2019年林樾在北海道风雪中最后一次回头,
定格成永恒的诀别。我怀疑自己剪的根本不是纪录片,
而是一封超长的、浸满无声尖叫的道歉信,写给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再拆开的人,
写给那些被我们亲手埋葬的声音,
孩子的哭声、玻璃的悲鸣、雪落时他试图捕捉却最终失去的寂静。
故事的开端清晰得如同昨日冲洗出来的胶片,2017年深秋,
杭州的空气里浮动着桂花甜腻的香和钱塘江水汽的微腥。我背着沉重的器材包,
为了那个“非遗手工”的纪录片,一头扎进满觉陇山坳里一个不起眼的手作玻璃工作室。
空气灼热,带着熔炉特有的硫磺和金属气息。汗顺着额角滑下来,有点痒但我没空擦。
镜头是我的盾牌,隔着取景器世界变得安全而有序。然后他走进了镜头。林樾二十八岁。
资料上写着“青年玻璃艺术家”。他站在熔炉旁,橙红的火光勾勒出他清瘦却紧绷的侧影,
下颌线像用刀削过。汗水浸湿了他额前几缕黑发,黏在苍白的皮肤上。
他正专注地吹制一个器皿,腮帮鼓起,气流通过长长的吹管注入炽热的玻璃液中。
那姿态带着一种近乎献祭的专注。我习惯性地调整焦距,捕捉他微微抿紧的唇线,
鼻梁上细小的汗珠,还有……左耳。镜头不由自主地推上去。他的左耳廓形状完美,
但耳道口异常光滑,没有助听器的痕迹。
资料上轻描淡写的一句“左耳失聪童年高烧后遗症”。他似乎察觉到了镜头的凝视,
动作有极其细微的停顿,但并未回头。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需要人微微侧耳才能听清。“许导”他结束吹制,将半凝固的玻璃放进退火窑,转过身,
目光平静地穿过镜头落在我脸上“想拍什么?”“过程”我放下机器,
试图让语气显得专业而松弛,“成功,当然也包括失败。观众需要看到真实的制作过程。
”他擦汗的手停在半空,眼神骤然冷了下去,像淬火的玻璃瞬间凝固。“失败?
”他重复了一遍,声音更轻了,带着一种奇异的锋利,“失败不该被展示,它只配听个响儿。
”第一次冲突,像一块小石头投入深潭,沉闷而短促。
工作室里只剩下熔炉的低吼和退火窑风扇的嗡鸣。他的抗拒如此直接,
几乎带着一种创伤性的敏感。项目陷入僵局。我辗转联系到一位在欧洲颇有影响力的策展人,
拿到了一个顶级玻璃艺术驻地的申请名额,以此为筹码,再次坐在他对面。
“国际玻璃艺术驻地”我把资料推到他面前,“机会难得。
条件只有一个:让我拍《森之卵》的创作过程,无论成败。”他盯着那叠印刷精美的资料,
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长久的沉默。熔炉的火光在他眼底跳跃,映出一种深不见底的挣扎。
最终,他抬起眼,目光锐利地刺向我:“成交,但要录下爆裂声,真正的爆裂声,你能做到?
”“我能。”我听见自己说,带着一种职业性的笃定,心里却莫名地一沉。
那要求里藏着一种近乎自毁的偏执。几天后,我第一次踏入他远离工作室的私人住处。
房间整洁到近乎空旷,只有一张工作台,一个巨大的书架,
和一面密密麻麻贴满了泛黄的拍立得照片的墙。全是同一个女孩的背影。马尾辫,
纤细的脖颈,奔跑的、低头的、看书的、站在阳光树影里的背影。唯一的正面照,
是她仰头看着旋转木马,侧脸模糊在光晕里,笑容灿烂却带着一种易碎的透明感。
每张照片右下角,都用极细的蓝色墨水笔,签着一个字母“Z”。像一个无声的咒语,
瞬间攫住了我的呼吸。空气里弥漫着旧相纸和灰尘的味道,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过去的悲伤。林樾没有解释,甚至没有看那面墙一眼,
只是沉默地递给我一杯水。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投下冰冷的栅栏。我按下快门的手指,
第一次不是因为构图或光线,而是因为一种突如其来的、想要抓住某种正在流失之物的灵感。
时间像被按下了快进键。2018年,镜头内外,
我和林樾的轨迹开始无可避免地重叠、缠绕,直至模糊了边界。
纪录片素材在硬盘里堆积如山,但真正盘踞在我脑海的,却是那些没有被镜头记录的碎片。
那是在富阳的深山里,为了寻找一种传说中能使玻璃呈现特殊“霜雪”质感的高岭土。
越野车在颠簸的山路上抛锚。深秋的山林暮色四合,寒意刺骨。
我们只能投宿在半山腰一座破败的小寺庙。大殿空旷阴冷,
只有一尊斑驳的泥塑佛像在摇曳的烛光里悲悯地垂目。柴火在破铁盆里噼啪作响,
映着林樾沉默的脸。他往火堆里添了根柴,跳跃的火光落在他失聪的左耳上,
像在抚摸一道隐形的伤口。“Z”他忽然开口,声音低哑,被火焰吞噬了大半,“她叫周止,
小时候和我住一个大院。” 他的目光没有焦距,穿透火光,落在更远的黑暗里。
“她总在我被欺负时冲过来,像只炸毛的小猫……后来她病了,白血病,
十八岁生日刚过就走了。” 他顿了顿,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她走前拉着我的手说,
‘林樾,你还欠我一滴眼泪呢,我等着’,可我一滴也流不出来,大概聋子连泪腺都坏了吧。
”他扯了扯嘴角,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弧度。寺庙外,山风呼啸着穿过松林,发出呜呜的悲鸣。
那一刻,我下意识地摸出手机,没有打开专业的摄影机,只是悄悄地按下了录音键。
镜头外的真实,带着粗粝的毛边和刺人的温度,开始入侵。手机屏幕上,
录音波纹微弱地起伏着,像一颗不安的心跳。情感的临界点在2018年北京的初雪夜到来。
我陪他去协和医院取最新的耳蜗调试报告。诊室里暖气开得很足,医生拿着报告单,
语气是职业性的平静,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林先生,
从目前的神经反应和影像结果看,左耳残余听力已经基本消失。植入体效能也到极限了。
很抱歉,没有进一步手术的必要了。”空气凝固了。林樾坐在那里,背脊挺得笔直,
像一尊冰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
他沉默地接过报告单,对医生点了点头,起身,走出诊室,动作机械而精准。我追出去,
在充斥着消毒水气味和人群嘈杂声的医院大厅里,几乎要跟丢他单薄的身影。
推开厚重的玻璃大门,寒风裹挟着雪花扑面而来。城市被这场初雪温柔覆盖,
霓虹在雪幕中晕染成模糊的光斑。林樾站在医院门口高高的台阶上,没有立刻走下。
他仰起头,望着漫天飘落的雪花,雪花无声地落在他苍白的脸上、睫毛上、失聪的左耳上。
“许镜”他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如同梦呓,被风雪卷走大半。他侧过头,右耳转向我,
眼神空洞而专注,仿佛在聆听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声音。“下雪是什么声音?
”我的心猛地一缩,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毫无预兆地俯下身,
微凉的唇带着雪花的湿意,印在我的唇上。那是一个短暂、冰冷、带着绝望气息的吻,
像一片雪花落在滚烫的皮肤上,瞬间消融,只留下刺骨的寒意。“我想记住雪落的声音。
”他退开一步,雪花落在他微颤的睫毛上,声音破碎在风里。那一刻,
我手机里的录音软件仍在后台无声地运行着,
忠实地录下呼啸的风声、远处车辆的鸣笛、医院广播的模糊通知,
唯独录不下他渴望捕捉的、雪落的声音,也录不下我胸腔里那震耳欲聋的轰鸣。
外部世界的裂痕也随之蔓延。纪录片拍到一半,
最大的投资人一个热衷于“正能量”和“心灵鸡汤”的传媒公司老板,审看了粗剪素材。
他肥胖的手指敲着桌子,唾沫横飞:“小许啊!方向错了!观众要看什么?看天才!
看他是怎么克服残疾,凤凰涅槃!看励志!看疗愈!把这些灰暗的、失败的东西,统统剪掉!
特别是那些碎玻璃的声音,听着就晦气!剪成‘玻璃王子的救赎之路’,才有卖点!
”我看着他油光发亮的脑门,心中一阵翻涌。“王总”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林樾不是王子,玻璃也不是童话。他的挣扎,他的残缺,他对失败的凝视,这才是真实。
片子不能这么改。”“真实?”王总嗤笑一声,“真实能卖钱吗?不改,后续资金一分没有!
你自己掂量!” 他摔门而去,留下满室令人窒息的沉寂。资金链应声断裂,
像一根被绷到极限的琴弦,铮然崩断。团队人心惶惶,项目岌岌可危。几乎在同一时间,
一封来自北海道的邮件像一束微光,穿透了阴霾。
林樾获得了北海道小樽一个传奇玻璃工坊的冬季驻地名额,邀请我作为随行导演,
拍摄他构思已久的“最终章”一件名为《玻璃之森》的作品。他说,
那将是声音与玻璃最极致也最危险的对话。希望像一簇微弱的火苗,重新燃起。
我开始疯狂地寻找新的资金,联系海外的发行渠道,几乎不眠不休。启程前夜,
身体深处涌起一股莫名的疲惫和晕眩,小腹隐隐传来一阵令人不安的坠胀感。
在机场冰冷的洗手间里,我颤抖着撕开一片验孕试纸的包装。等待结果的那几分钟,
像被拉长成一个世纪。洗手间顶灯惨白的光照在小小的塑料窗上,两条线。一深一浅。
弱阳性。我大脑一片空白。巨大的、混杂着难以置信和隐秘恐慌的浪潮瞬间将我吞没。
航班信息在广播里催促着登机。林樾还在外面等着。我该怎么办?告诉他?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失血的脸,把那张小小的试纸紧紧攥在手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又用纸巾死死盖住。先去北海道等拍摄完了再说。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了出去,
努力让步伐显得正常。候机大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林樾坐在长椅上,
低头看着一本关于声波物理的书,侧脸在顶灯下显得安静而专注。我走到他身边坐下,
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快登机了。”他“嗯”了一声,
合上书抬起头望着窗外滑行起飞的巨大飞机,眼神空茫仿佛穿透了钢铁机身,
落在某个遥远不可触及的时空。北海道的冬天是凝固的寂静。
小樽的玻璃工坊孤悬于一片无垠的雪原之上,像一个遗世独立的冰冷堡垒。零下二十一度,
呵气成冰。巨大的落地窗外,是亘古不变的、令人绝望的纯白。工坊内,
熔炉日夜不息地燃烧着,发出沉闷的咆哮,是这片死寂之地唯一粗重的呼吸。
林樾的创作近乎疯狂。他构想中的《玻璃之森》,
是让滚烫的液态玻璃在特定频率的声波冲击下瞬间爆裂、凝固,
让裂纹像有生命的藤蔓般自行生长、蔓延,
最终形成一片由无数破碎晶体构成的、诡异而壮丽的“森林”。这实验危险而精密,
对声音的频率、强度、玻璃的温度和厚度要求都苛刻到了极点。每一次尝试,
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和漫天飞溅的高温玻璃碎片。“再靠近一点!许镜!
”林樾在巨大的噪音中对我吼,他戴着厚重的防护耳罩和面罩,
眼神在炉火的映照下燃烧着一种近乎癫狂的光。
巨大的音箱阵列对着熔融的玻璃液发出低沉的咆哮。我扛着沉重的摄影机,
镜头紧紧追随着坩埚里那团炽热的、流动的橙红。每一次声波的冲击,都让我心脏狂跳,
胃部抽搐。防护服里的身体早已被汗浸透。小腹的隐痛从未真正消失,
反而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拍摄、高温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变得顽固而清晰。
像一把迟钝的锯子,在身体深处缓慢地拉扯。我咬紧牙关,
把每一次不适都归咎于水土不服或疲劳过度。我不敢去想那张揉皱的试纸,
更不敢看林樾在声浪与火焰中专注到忘我的侧脸。每一次成功的爆裂,
都伴随着他眼中短暂迸发的、近乎神性的光芒,那光芒让我所有的话语都哽在喉咙里,
无法出口。直到那天下午。一组高频声波实验结束后,
工坊里弥漫着刺鼻的焦煳味和玻璃粉末。我放下机器一阵剧烈的眩晕猛地袭来,眼前发黑,
身体不受控制地晃了晃。紧接着,一股温热的暖流毫无预兆地涌出,顺着大腿内侧蜿蜒而下。
触目惊心的红,迅速在米白色的工作裤上洇开,像一朵绝望绽放的花。
世界的声音瞬间消失了。熔炉的咆哮,林樾调试设备的敲击声,
窗外呼啸的风雪一切都归于死寂。只剩下血液奔流的轰鸣在耳膜内疯狂鼓噪。
我扶着冰冷的金属工作台,指甲深深抠进掌心,才勉强站稳。林樾正背对着我,
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上一块爆裂玻璃的裂纹走向,完全没有察觉。不能在这里,不能让他看见。
我几乎是挪到存放个人物品的角落,用一件厚外套死死系在腰间,挡住那片刺目的红。
抓起钱包护照,
个负责记录数据的日本助理工程师说了一句:“我出去一趟买点东西” 没敢看林樾的方向,
低头冲进了门外铺天盖地的风雪里。札幌市立综合病院,消毒水的味道浓烈得令人窒息。
冰冷的检查器械,医生职业化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日语。
当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医生看着检查单,
着口音的英语清晰地说出“Spontaneous abortion”自然流产时,
我躺在诊疗床上,只觉得天花板惨白的灯光晃得人眼睛生疼。没有眼泪,
只有一种巨大的、冰冷的空洞感,从身体深处蔓延开来,吞噬了一切。
“胚胎组织已完全排出,注意休息避免情绪剧烈波动”医生的声音像是从水底传来,
模糊不清。我拿着几张处方单和一沓日文写的注意事项,像一具空壳,飘出了医院。
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札幌的街道被厚厚的白色覆盖,行人匆匆,世界照常运转。只有我,
被抛在了无声的废墟里。毁灭的序曲在几天后奏响。2020年1月23日。
工坊那台老旧的电视,断断续续播放着国际新闻频道。屏幕下方,
刺眼的红色滚动条疯狂跳动:中国武汉爆发不明原因肺炎,
封城……多国启动撤侨……航班大面积熔断取消。“航班熔断”我喃喃地重复着,
心一点点沉下去。这意味着,我们被困在了这座雪原上的玻璃堡垒里,归期无望。
林樾坐在工作台前,一遍遍擦拭着几片刚刚完成、裂纹异常美丽的玻璃碎片,动作很慢,
像在擦拭易碎的珍宝。电视屏幕的蓝光映在他脸上,一片死寂的平静。他没有说话,
但周身笼罩着一层比窗外冰雪更寒冷的隔阂。是源于一个更深的、无法触及的深渊,
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由沉默和秘密筑成的高墙。“林樾”我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发紧。
流产的事,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胸口,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味。我必须告诉他。
在这个与世隔绝、被末日般消息笼罩的雪夜里。他抬起头,眼神空茫地扫过我,
没有任何焦点,仿佛我只是工坊里一个无关紧要的影子。他站起身,走向熔炉区,
开始准备新一轮的实验。这一次,他调试的声波频率前所未有地高,
音箱发出的尖啸声让空气都仿佛在震动。坩埚里的玻璃液翻滚着,呈现出一种妖异的亮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