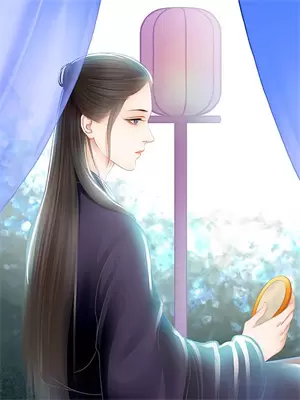我沉尸古井那夜,穿着未嫁的猩红嫁衣。水冷,恨更刺骨。如今我归来,携十缕残香索命。
每一缕,都是你们罪孽的滋味。嘘…听见了吗?那缕栀子香里,藏着你的死期。1我醒来时,
已在井底。冰冷的水浸透了我的嫁衣,那件由苏杭最好绣娘耗时三月缝制的凤穿牡丹喜服。
如今成了一张猩红的裹尸布,紧紧贴在我浮肿的皮肤上。奇怪的是,我感受不到丝毫寒冷。
只有一种沉重的、无处不在的湿漉感,像是被浸泡了许久的朽木。黑暗浓稠得化不开。
我试图移动,四肢却像被无形的水草缠绕,动弹不得。仰头望去,
井口是一轮遥不可及的、微微发灰的圆月,那么高,那么远。几缕枯草的剪影耷拉在井沿,
随风轻晃。我是怎么到这里的?记忆如同破碎的镜片,扎得我头疼。最后清晰的画面,
是摇曳的烛光,满室喜庆的红,还有……我正对镜簪上最后一支赤金珍珠步摇。
镜中人眉眼含羞,唇角噙着对明日婚期的期待。然后呢?
然后是一阵猝不及防的猛力从背后袭来!一只手,冰冷而有力,死死捂住了我的口鼻。
另一只手粗暴地扼住我的喉咙,将那声惊呼掐灭在萌芽。天旋地转间,
我闻到了极其淡雅的栀子香气,混杂着一丝陌生的、冷硬的烟味。再然后,
便是无止境的坠落,冰冷的井水吞噬了我所有的感知。等等。坠落?窒息?若我已死,
此刻思考的又是什么?一股巨大的恐慌攫住了我。我猛地低头,
借着井口投下的那点微弱月光,看向自己的身体——大红嫁衣依旧鲜亮,
金线刺绣反射着幽暗的水光。但透过湿透的衣料,
我看到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灰白浮肿,指尖泡得发皱,毫无血色。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没有温度。一个认知如同井水般冰冷地浸透我的“意识”:沐晚晴,你已经死了。
死在新婚前夕。死在沐家后院的这口废弃古井里。“……老爷都快急疯了,
城里城外寻了三日,连根头发丝都没找见!”井口上方,突然传来压低的交谈声,
是两个小丫鬟的声音,有些耳熟。“嘘!小声些!太太不让私下议论……可不说又能怎样?
人都没了,沈家那边今日一早就来人了,说是要退婚帖呢!”“退婚?
大小姐这还没过门就……沈少爷也太薄情了些!”“噤声!主家的事也是我们能嚼舌根的?
快走吧,这井边阴气重,我老觉得脊背发凉……”脚步声渐行渐远。我却如遭雷击。三日?
我竟已“失踪”了三日?沈墨言……他来退婚?那个前日还握着我的手,
温言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沈墨言?那个为我画了无数肖像,
说要将我最美模样永远留存的沈墨言?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愤和凄凉涌上心头,比井水更刺骨。
我挣扎着,想要冲出这口囚禁我的深井,去问个明白!意念一动,
身体竟真的轻飘飘地向上浮起。不是游动,而是仿佛失去了重量,穿透了冰冷的井水。
穿透了长满青苔的井壁砖石,如同一个……虚无的泡泡。当我回过神来,
已然飘立在井沿之上。夜风吹过庭院里的老槐树,树叶沙沙作响。我低头,
看着井中自己那具穿着嫁衣、静静漂浮的尸身。又低头,看向此刻站在井边的“自己”。
月光穿透了我的手掌,照在地上,没有留下丝毫影子。原来,我已成孤魂。
一股无形的牵引力忽然传来,伴随着一丝极细微。
却让我魂体为之颤动的熟悉香气——那是我为婚礼特意调制的头香。初闻是栀子,
尾韵却带一丝冷梅的清冽。香气来自宅子东边,我的灵堂方向。
我身不由己地被那缕残香牵引,飘过熟悉又陌生的庭院。越过一道道门廊。府内白幡飘动,
灯火通明,却处处透着一股压抑的死寂。灵堂设在了前厅。素烛高烧,白幔低垂。正中央,
停放着一口厚重的、尚未盖棺的檀香木棺。我的父亲,几日间仿佛老了十岁,鬓角尽是霜白。
他佝偻着背,由管家搀扶着,正老泪纵横地望着棺内。几名姨娘和下人跪在下方,低声啜泣。
我飘近些,目光落向棺内——空的。那棺材里,只有我平日穿的几件衣裙,整齐地叠放着。
上面放着一支我常用的旧式钢笔。他们甚至找不到我的尸身来入殓。
“我的晴儿啊……”父亲一声悲呼,捶打着心口,“你到底去了哪里啊!
让爹爹如何是好啊……”我心如刀绞,扑过去想扶住他:“爹!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
”可我的手穿透了他的手臂,我的呼喊消散在空气里。他毫无察觉,
依旧沉浸在那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碰不到他,他也听不见我。我绝望地环顾四周,
目光猛地定格在跪在父亲身后不远处的两人身上。一身缟素的表妹林婉茹,
正拿着绣了栀子花的绢帕。轻轻拭泪,哭得梨花带雨,肩膀微微颤抖。而她身旁,
同样一身素色长衫。面容憔悴、眼含悲痛的年轻男子,正是我的未婚夫——沈墨言。
他微微低着头,侧脸在烛光下显得格外俊朗,也格外悲伤。任谁看了,
都会认为他是一个痛失所爱的深情之人。可我却清晰地看到,他低垂的眼眸深处。没有泪光,
只有一片沉沉的、看不透的暗色。以及,他微微抿紧的嘴角,
那一丝若有若无、近乎错觉的……放松?灵堂里烛火猛地摇曳了一下。
一股远比井水阴寒的气息,自我的魂体深处,汹涌而出。2我立在灵堂的阴影里,
望着那口空棺。望着悲痛欲绝的父亲,望着那对看似哀戚的璧人。
一股冰冷的怨愤在我虚无的胸腔里翻腾,几乎要冲破这魂体的束缚。为什么?是谁?
那丝牵引我而来的冷梅栀子香,在此地尤为清晰,丝丝缕缕,萦绕不散。
它来自棺中我那些旧衣,更来自林婉茹手中那方不断拭泪的绢帕。我飘近她,
死死盯着她那双哭得红肿、却依旧清澈的眼睛。她似乎全然感受不到我的注视,
只是依偎在沈墨言身侧,柔弱得像一株需要依附的藤蔓。
“婉茹妹妹……”沈墨言的声音沙哑,带着恰到好处的疲惫与悲伤。
他轻轻拍了拍林婉茹的肩,“节哀,晚晴……她若在天有灵,也不愿见你如此伤怀。
”他的指尖掠过她的肩头,动作自然,却让我魂体莫名一滞。那语气里的温柔,那般熟稔,
那般……亲近。远超出对一个未婚妻表妹应有的分寸。林婉茹抬起泪眼看他,
那眼神复杂得让我心惊。有依赖,有安慰,还有一丝难以捕捉的、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
她轻轻点头,用那绣着栀子的帕子掩住唇,又是一阵低泣。不对。这不对劲。
我试图穿透她那层悲恸的伪装,看清底下藏着的真相。可我如今只是一缕幽魂,徒有双眼,
却看不透人心。灵堂里人多,阳气盛,待得久了。我只觉魂体被那烛火烟气炙烤得有些涣散,
极不舒服。那无处不在的哭声和诵经声,更像是一把把钝锉,磨着我的意识。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飘出灵堂,如同被风吹送的落叶,漫无目的地在偌大的沐府游荡。
白日的府邸,因着我的“丧事”,显得格外沉寂压抑。下人们步履匆匆,低着头,不敢交谈。
他们穿过我的身体,毫无知觉。我尝试触碰廊下的兰花,手指却直接没入了花瓣之中。
我对着一个相熟的小丫鬟呼喊,她却只是猛地抱紧胳膊。
嘀咕了一句“这穿堂风怎地突然这般冷”,便加快脚步走开了。彻底的隔绝。彻底的虚无。
这比井底的冰冷更让我绝望。不知不觉,我飘回了生前居住的院落“晴苑”。这里一如往昔,
花木扶疏,只是门窗紧闭,少了人气。我穿透梨木雕花门,进入内室。梳妆台上,
我常用的那把牛角梳还搁着,上面缠绕着几根乌黑的长发。绣架上,
未完成的鸳鸯戏水图只绣了一半,针还别在红色的丝线上。空气中,
似乎还残留着我平日惯用的熏香味道。那是我用晒干的玉兰和沉水香调配的。
一切仿佛都停留在三日前,我最后离开这里的那个傍晚。仿佛下一刻,
丫鬟小翠就会推门进来,笑着说:“小姐,该试嫁衣了。”物是人非事事休。
巨大的酸楚淹没了我。我飘到梳妆台前,凝视着镜面——那里空空如也,映不出丝毫影像。
我果真成了无影无形的孤魂野鬼。悲从中来,我下意识地伸手,想去触摸那梳子,
触摸我曾经存在过的证明。
就在我虚无的指尖触及梳齿的刹那;一股强烈的悸动猛地攫住了我!并非触感,
而是一种更深层、更奇异的连接。一些破碎的画面、声音、情绪,如同被投入石子的静湖,
骤然荡开涟漪,强行涌入我的“意识”!……我坐在这个梳妆台前,小翠站在身后。
仔细地用这把梳子为我通发,嘴里哼着轻快的苏南小调……窗外夕阳正好,
将一切都镀上温暖的金边……我心里想着明日的大婚,想着沈墨言含笑的眼睛,
脸颊微微发烫……是记忆!这把梳子,残留着我生前的记忆碎片!我猛地“缩回手”,
那清晰的幻象瞬间消失。我惊疑不定地审视着那把寻常的梳子。所以,
我并非只能被动地游荡?这些沾染了我生前气息的物件,能让我“看”到过去?
这个发现让我死寂的魂体激动得几乎战栗起来。若真如此,
那我是否……能拼凑出遇害那夜的真相?我急切地环顾四周,目光扫过房间里的每一件物品。
胭脂水粉、书籍、钢笔、花瓶……最终,落在窗前小几上的一只白玉香薰炉上。
那是我最爱用的香炉,炉腹里还积着些许未曾清理的香灰。我凝聚全部意念,
缓缓将手探向那冰凉的玉炉。指尖没入的瞬间,更汹涌的画面扑面而来!……夜已深,
烛台亮着温暖的光。我穿着寝衣,坐在窗边,
就着灯光仔细翻阅一本泛黄的线装书——《香谱拾遗》。炉里正燃着我新调的安神香,
青烟袅袅,气息宁和。我时而提笔,在旁边的纸上记录着什么,眉头微蹙,
似乎在思考一个关键的配比……那是遇害前一夜!
我在为婚礼当日要用的最终版香方做最后的调整!记忆的视角是我自己,
我能感受到当时指尖触摸书页的质感,能闻到空气中那复杂而和谐的香气。那香方……对,
我叫它“十香序”,由十种主香依次调和。前调栀子白兰,中调冷梅瑞脑,
尾韵定是沉香与苏合……我以为此香能佑我婚姻美满,白首偕老……可笑!真是可笑!
悲愤再次上涌,冲散了记忆画面。我定定神,试图再次感知,想看清那晚更多细节。
可香炉能承载的记忆似乎只有这些日常片段。我需要更强烈的……与我死亡直接相关的物品,
或者……气味。对,气味!那缕始终牵引我的冷梅栀子香,那方林婉茹握在手中的绢帕!
我猛地穿透墙壁,疾速飘回灵堂。法事似乎暂告一段落,人群稀疏了许多。
父亲已被扶去休息,棺木依旧停在那里,显得格外孤寂清冷。林婉茹和沈墨言也不在了。
我焦急地搜寻,终于在后院廊下看到了他们。他们并肩而立,似乎在低声交谈着什么,
林婉茹依旧时不时用那方绢帕按一按眼角。就是现在!我朝着林婉茹手中的帕子扑去,
将所有意念集中于那一点。指尖触及丝帕的瞬间,预想中的记忆画面并未出现。
反而是一股极其阴寒歹毒的感觉顺着我的“指尖”猛地反噬而来!呛得我魂体几乎要散开!
那帕子上的香气……不对劲!除了我调制的冷梅栀子头香,那丝帕深处。
还隐藏着另一种极其淡薄、却令人极度不适的甜腻气息!那气息冰冷、滑腻,像毒蛇的信子,
带着一种不祥的腐朽感!这绝不是我香方里的任何一味香!而且,
这帕子……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我一定在哪里闻到过这种甜腻阴冷的气息,
在某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还想进一步探究,沈墨言却忽然动了。他似乎是觉得有些冷,
抬手紧了紧身上那件素色薄绸长衫的外套。随着他的动作,一股极其细微的。
与他此刻清雅形象截然不同的气味,从那外套的衣料间逸散出来。
那是一丝……劣质的、艳俗的脂粉香气。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井苔的土腥味。
我的魂体骤然僵住,所有的感知瞬间聚焦于那丝转瞬即逝的、来自沈墨言身上的陌生气味上。
冰冷黏腻的恐慌,如同井水般再次将我淹没。他……去过井边?
3沈墨言身上那丝混杂着劣质脂粉与井苔的气味。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入我虚无的核心。
他去过井边?在我死后?他去做什么?无数可怕的猜测瞬间涌上心头,
几乎要将我残存的理智撕裂。我必须知道真相!而眼下唯一的线索,似乎都指向了“香”。
那方帕子上的诡异甜腻,沈墨言身上的陌生气息,还有……我遇害前正在调配的“十香序”。
我的调香室!那间位于晴苑西厢的屋子,
存放着我所有的珍爱:采集自天南地北的香料、精油,大大小小的琉璃瓶、玉钵、铜秤,
还有无数我亲手写下的香方笔记。那里是我生前除卧室外待得最久的地方,
必然残留着最浓烈的气息和最清晰的记忆。意念一动,魂体已穿透重重墙壁,
瞬息间便置身于调香室内。屋内景象让我魂体一滞。一切看似整齐,却整齐得过分了。
我惯用的那套青玉研钵和玉杵被擦得锃亮。规规矩矩地放在桌角,
而不是像我往常那样随手放在触手可及的正中央。架子上那些贴着标签的香料瓷罐,
排列顺序似乎也被细微地打乱过。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刻意清扫过的、混合了多种残留香气的味道。
复杂却失去了原本和谐的灵魂。这里被人动过了。而且,动得小心翼翼,试图掩盖痕迹。
是谁?在我“失踪”后,谁需要来动我的调香室?我飘到那张宽大的梨花木调香台前。
台面光洁,几乎能照出我虚无的轮廓。但我能“嗅”到,这里残留的香气最为混乱驳杂。
我缓缓将手覆上台面,凝聚所有意念,去感知,去捕捉……零碎的画面再次涌现,
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清晰!……烛光摇曳,将我的影子投在墙上。
我正专注地对着一个小巧的银秤,小心翼翼地将几粒乳白色的瑞脑投入玉钵中。
旁边铺着一张宣纸,上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十香序”的配方。十种主香的名字依次排列,
每一种后面都标注了精确的分量和加入顺序。
栀子、白兰、素馨、玫瑰露……直至最后的沉香与苏合。我记得那种期待又谨慎的心情。
这是我为人生最重要日子准备的献礼,我要让它完美无瑕。记忆的画面陡然晃动了一下,
像是平静的水面被投入石子。……门被轻轻推开,林婉茹端着一盏参茶走了进来,
声音柔得能滴出水:“晚晴姐姐,夜深了,歇歇眼睛吧。”我记忆中的我抬起头,
对她笑了笑,接过茶盏放在一旁:“快了,就差最后定韵的几步,
墨言说最喜欢沉香尾调的那点余韵。”林婉茹走近,目光落在宣纸的香方上,
眼中满是惊叹和羡慕:“姐姐真是巧手,这香气光是闻着原料就已这般醉人,
成品不知该何等惊艳。沈大哥……真是有福之人。
”她的指尖似无意地拂过那写着“苏合”二字的瓷罐。“婉茹妹妹若是喜欢,
明日我匀一些给你。”我笑着低头,继续研磨钵中的香料。“那怎么好意思,
这是姐姐特意为婚礼调的……”她推辞着,却又凑近了些。仔细看着我的动作,
状若无意地问,“姐姐,这十种香料的顺序,可是有什么讲究?我看你添放时分毫都不差呢。
”“自然有讲究,”我心情颇好,耐心解释,“香气如乐章,次序一乱,前调压不住中调,
尾韵便会散乱无力。尤其是最后三味,定要依序而入,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记忆的画面到这里变得模糊,林婉茹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如何回应,
都已不清。只记得她最后放下参茶,柔声劝我早些休息,便离开了。
参茶……我猛地从记忆碎片中抽离,目光扫过调香台。那只白瓷参茶杯早已被收走,
台面上没有任何茶渍残留。但我的视线,却被台面边缘一道不易察觉的细微划痕吸引。
划痕旁,散落着几粒极细微的、不同于任何香料的透明晶粒。我本能地觉得那晶粒不对劲。
不是香料,那是什么?我环顾四周,试图寻找更多线索。
目光最终落在角落的一个白玉废料盒里。那里通常存放着调配失败或是不慎洒落的香料残渣。
盒子里似乎有东西。我凑近看去,只见几片琉璃碎片半掩在香灰中,折射出微弱的光。
看那弧度,像是一个小巧的香水瓶被打碎了。瓶中的液体早已挥发殆尽,
但残留的香气却异常浓烈刺鼻。即使混杂在诸多气味中,也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不和谐!
那正是我熟悉的“十香序”的基底,但其中。
却霸道地掺杂进了一股极其不协调的、甜腻到发齁的异香!
这异香……与我之前在林婉茹帕子上嗅到的那丝阴冷甜腻,同出一源!只是这里更为浓烈,
更为赤裸!有人在我调配好的“十香序”里,额外添加了东西!而这瓶被动了手脚的香水,
被打碎了,丢弃在这里!是谁?是谁进来动了我的香?是林婉茹吗?她那晚的来访,
真的只是关心?巨大的疑团和冰冷的恐惧攫住了我。就在这时,
一股强烈的、源自魂体本能的悸动从远方传来——是那口井!那口吞噬我的古井方向,
传来了某种强烈的、与我密切相关的感应!那里有东西!重要的东西!
我毫不犹豫地抛下调香室的一切,循着那感应疾速飘去。夜色深沉,后院空无一人,
只有风吹过荒草的呜咽。我飘至井边,那感应愈发强烈,源自井口石壁的一道狭窄裂缝。
我凝聚魂体,小心翼翼地将感知探入那潮湿阴冷的石缝。指尖触到了一件冰冷坚硬的小物件。
我费力地将它“勾”了出来。它落在井沿的青苔上,在月光下反射出温润幽微的光泽。
那是一枚翡翠耳坠。水滴形状,翡翠成色极好,通透莹绿,用细细的银钩穿着。
我认得这枚耳坠。这是去岁生辰时,我父亲送给林婉茹的礼物。她当时欢喜得什么似的,
几乎日日戴着。还曾在我面前炫耀过多次,说这颜色最衬她肌肤。林婉茹的耳坠,
怎么会掉在这井沿的石缝里?在她“悲痛欲绝”、足不出户寻找表姐的三日里?难道她来过?
在我被害之后?还是……更早?冰冷的恨意开始在我魂体内凝聚。
我死死“盯”着那枚在月光下泛着冷光的翡翠,将所有意念集中于其上。
除了井水的湿冷、青苔的土腥,那耳坠上。
还残留着一丝极其淡薄、却让我魂体骤然绷紧的气息。那不仅是林婉茹常用的头油香气。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早已干涸发黑的……血腥气。4那枚翡翠耳坠上的血腥气,
像一把淬了冰的匕首,直直捅入我魂体最深处。冰冷、粘稠、带着死亡气息的铁锈味,
与我记忆中井水的冰冷融为一体。林婉茹!她不仅来过井边,她……极可能亲眼目睹,
甚至参与了我的死亡!否则这新鲜的血气从何而来?是挣扎时溅上的吗?是我的血吗?
无边的恨意如同毒藤,瞬间缠紧了我的意识。我要去找她!现在!立刻!魂体裹挟着阴风,
我猛地扑向林婉茹所住的“蕙兰阁”。夜已深,阁内却还亮着一盏孤灯,
昏黄的光晕透过窗纸,映出一个窈窕的身影。我穿透门扉,直入内室。林婉茹并未睡下。
她只穿着一件素绸寝衣,背对着门口。坐在梳妆台前,手中似乎拿着什么东西,正低头凝视。
屋内弥漫着一股安神香的甜腻气味,试图掩盖什么。
却盖不住那丝若有若无的、从她身上散发出的惊惶。“林婉茹!”我无声地嘶吼,
逼近她身后。试图用我全部的怨念去冲击她,“你看得见我吗?告诉我!是不是你!?
”她猛地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抱紧了双臂。疑惑地回头望了望空无一人的身后,眉头微蹙,
喃喃自语:“怎么突然这般冷……”她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我所有的愤怒和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