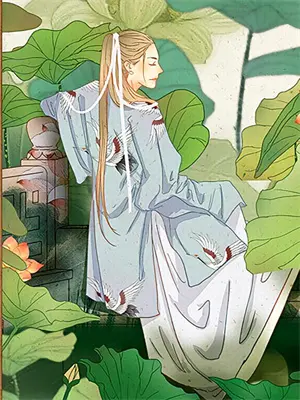
夜雾浓重,连贾府后花园平日里最嚣张的蟋蟀也噤了声。平儿提着一盏昏黄的灯笼,
踏着湿滑的青石板,每一步都轻得像猫。她是奉了王熙凤的命令,
来这偏院“请”二爷贾琏回去的——凤姐儿房里的西洋钟刚敲过三更,这位爷却还未归家。
偏院的门虚掩着,里头透出暖黄的光和一股子甜腻的香气。平儿在门前顿了顿,
深吸一口秋夜的凉气,才推门而入。屋里暖得让人发闷,炭火烧得正旺。多姑娘,
府里新来的裁缝媳妇,正对镜梳妆,见她进来,也不惊慌,只懒懒一笑:“平姑娘来了?
二爷刚睡下。”说着,目光意有所指地瞟向里间那扇松花色的软帘。平儿不接话,
目光扫过凌乱的炕桌,上头摆着吃残的酒菜,两只酒杯挨得极近。地上,
一件宝蓝色的男子外袍随意丢着,袍角沾了点胭脂,在烛光下红得刺眼。她认得,
那是贾琏今日出门时穿的。“二奶奶等急了,我来接二爷回去。”平儿的声音平静无波,
听不出半点情绪。她挑帘走进里间。贾琏果然和衣躺在炕上,呼吸沉重,似是醉得深了。
他面容俊朗,即便睡着,眉宇间也带着几分惯常的风流意味,只是此刻唇角紧抿,
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平儿走近,正要唤他,目光却被他紧攥着的右手吸引。指缝间,
隐约露出一缕墨黑,不是头发是什么?多姑娘跟了进来,倚在门框上,
似笑非笑:“二爷方才还念叨,说平姑娘最是体贴懂事……”平儿像是没听见,
只盯着贾琏的手。她伸出手,指尖微凉,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腕。贾琏在睡梦中蹙眉,
手微微一松。平儿动作极快,几乎是瞬间,便将那缕青丝抽了出来,藏入袖中。
整个过程悄无声息。多姑娘脸上的笑僵了僵。平儿这才转向她,语气依旧温和,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多姑娘,夜深了,你也早些歇着吧。今夜二爷不过是多喝了几杯,
在此歇脚,并无他事,对吗?”多姑娘是个伶俐人,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
干笑两声:“自然是,平姑娘说的是。”平儿不再多言,俯身轻轻推醒贾琏:“二爷,
二奶奶让您回去呢。”贾琏醉眼朦胧地醒来,见是平儿,先是一愣,随即眼底掠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镇定下来,揉着额角坐起:“什么时辰了?竟睡过去了。”他起身,目光扫过屋内,
掠过平儿平静的脸和多姑娘不太自然的神情,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他穿上外袍,
对多姑娘随意摆了摆手,便跟着平儿出了门。夜路寂静,只有两人的脚步声。
贾琏的酒醒了大半,沉默地走在平儿身后半步。灯笼的光晕在脚下晃动,
勾勒出她纤细却挺直的背影。他知道,方才的事,绝不可能轻易过去。行至穿廊下,
四下无人,贾琏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宿醉的沙哑:“平儿……方才……”平儿停下脚步,
转过身,灯笼的光照着她半边脸,柔和却看不清眼底情绪。
她缓缓从袖中取出那缕用红绳系着的青丝,在贾琏面前晃了晃:“二爷说的,是这个么?
”贾琏脸色微变,伸手便要来夺。平儿却手腕一收,将青丝紧紧握在手心,
声音低了几分:“二爷,这样东西,若叫二奶奶瞧见,只怕多姑娘在府里待不到天明。
便是二爷您,也少不了一场天翻地覆。”贾琏看着她,忽然笑了,
带着点破罐子破摔的惫懒:“你既拿了,又不当场嚷出来,想要什么?直说吧。
”他凑近一步,身上酒气混杂着多姑娘房里的脂粉香,扑面而来,“银子?
还是……你也想学那多姑娘,寻个靠山?”平儿眼底闪过一丝极淡的厌恶,后退半步,
拉开了距离。她抬起头,直视着贾琏:“二爷误会了。平儿不要银子,更不敢有非分之想。
”“那你要什么?”平儿沉默片刻,夜风吹动廊下的枯叶,沙沙作响。
她的声音在风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娘的坟,在城外乱葬岗,多年无人打理,快要平了。
求二爷得空时,派人去修缮一番,立块像样的碑。”贾琏愣住,万万没想到是这个要求。
他隐约记得平儿是王家的家生奴才,她娘好像也曾在府里当过差,具体却记不清了。
“你娘……?”“我娘叫云裳,从前在大老爷房里伺候过。”平儿的声音很轻,
却像针一样扎进贾琏耳中。贾琏心头一震。云裳……他有点印象了,
是个眉眼温顺的江南女子,在他还小的时候,似乎确实在父亲贾赦房里见过。
后来……后来听说病死了,还是怎么的,他记不清了,府里旧人来来去去,一个丫鬟的生死,
谁又真放在心上。他看着平儿,此刻她才仿佛卸下那层温顺懂事的面具,
眼底藏着深不见底的悲凉。“就这个?”贾琏有些不信。“就这个。”平儿点头,
“二爷应允了,这缕青丝,今夜便从未存在过。平儿也会记得,
二爷只是与多姑娘商议裁衣事宜,醉后歇在了偏院。”这交易简单得让贾琏意外,
又沉重得让他心惊。修缮一座孤坟,对他而言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却能换来平儿如此重要的缄默。这丫头的心思,远比他想的要深。“好,我答应你。
”贾琏应得干脆,“明日就吩咐赖大去办。”平儿福了一礼:“谢二爷。
”她将握着青丝的手伸到贾琏面前,缓缓张开。那缕黑发静静地躺在她白皙的掌心。
贾琏伸手去拿。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青丝的那一刻,平儿的手指却轻轻合拢,堪堪避过。
贾琏一怔,看向她。平儿抬起眼,目光清亮,竟让贾琏无端感到一丝压力。“二爷,
君子一诺,重如千金。平儿虽是个丫鬟,却也知道信义二字。望二爷……莫要忘了今夜之言。
”贾琏看着眼前这个平日低眉顺眼的丫头,忽然觉得有些陌生。他扯了扯嘴角:“放心,
忘不了。”这次,平儿彻底松开了手。贾琏迅速将青丝揣入怀中,像是怕它飞了。
两人一前一后,继续往凤姐院里走。快到院门时,
已能听到里头传来王熙凤拔高了嗓音在训斥小丫头。贾琏整理了一下衣袍,深吸一口气,
准备应对接下来的风暴。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平儿一眼。平儿已重新垂下眼帘,
恢复了那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仿佛刚才在穿廊下那个眼神锐利、与他讨价还价的丫头,
只是他醉后的一场幻影。只有她紧握灯笼的手指,因用力而微微泛白,
泄露出一丝不为人知的波澜。她跟在贾琏身后,踏进那灯火通明、却更显压抑的正房。
王熙凤凌厉的目光立刻扫了过来,如同刀子般刮过两人。平儿的心,在胸腔里沉沉地跳着。
她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那缕青丝换来的承诺,如同投入深潭的一颗石子,涟漪之下,
是贾府深不见底的黑暗,和她蛰伏多年,等待时机的复仇之心。她娘的坟,不能白修。
贾琏的风流债,也绝不会就此了结。今夜,她只是轻轻扣动了第一枚胭脂扣。
凤姐儿的生日宴,排场摆得极大。合府上下,连带着各房有头脸的管事媳妇、体面的老嬷嬷,
都挤在花厅里。戏台上锣鼓喧天,唱的是《麻姑献寿》,咿咿呀呀的唱词混着酒肉香气,
织成一片虚假的繁华。平儿穿梭在席间,手脚不停地斟酒布菜,
眼角余光却时刻留意着主位上的王熙凤和已然离席半晌的贾琏。
凤姐儿今日穿了件大红遍地金的袄子,脸上敷着厚厚的粉,笑容满面地应酬着各路诰命夫人,
但那笑意并未抵达眼底。她怀孕已近四月,小腹微隆,脾气却比往日更显焦躁,
一双丹凤眼时不时扫向贾琏空着的位置,目光阴沉。贾琏离席时,推说是前头有男客要招呼。
可平儿方才去厨房催菜时,分明瞧见小厮兴儿鬼鬼祟祟地往后院鲍二家的住处方向溜。
一股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蛇,缠上了平儿的心头。果然,酒过三巡,
王熙凤脸上的笑渐渐挂不住了。她扶着腰起身,说是要更衣,
目光却锐利地钉在平儿脸上:“平儿,你跟我来。”平儿心下一沉,默默跟上。
王熙凤并不往净房去,反而径直朝着后院仆役聚居的矮房走去。脚步又快又急,裙裾带风。
平儿几乎是小跑着才能跟上,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行至鲍二家窗外,
里头隐约传来男女调笑的声响,夹杂着杯盘碰撞。王熙凤的脚步猛地顿住,
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她胸口剧烈起伏,猛地一脚踹开了那扇薄薄的木门!
屋内的景象不堪入目:贾琏衣衫不整,醉醺醺地搂着同样鬓发散乱的鲍二家的,
正凑在炕上吃交杯酒。炕桌歪斜,酒菜洒了一地。骤然被撞破,贾琏惊得酒醒了一半,
鲍二家的更是尖叫一声,缩到炕角。“好!好个恩爱夫妻!”王熙凤气得浑身发抖,
声音尖利得刺耳,“我当你是去应酬贵客,原来是在这奴才窝里当起了新郎官!
”贾琏恼羞成怒,加之酒意上涌,也豁出去了,梗着脖子骂道:“泼辣货!我不过吃杯酒,
你便闯进来喊打喊杀,成何体统!”“体统?你跟这贱婢滚在一处,就有体统了?
”王熙凤怒极,一眼瞥见吓得瑟瑟发抖的平儿,满腔邪火仿佛瞬间找到了出口。她猛地转身,
扬手就朝平儿脸上狠狠掴去!“还有你这小蹄子!定是你替他遮掩,与他合伙来欺瞒我!
”平儿猝不及防,被这一巴掌打得踉跄几步,脸颊火辣辣地疼,耳边嗡嗡作响。她捂着脸,
百口莫辩。这无妄之灾,她早已习惯,只是心头的寒意,比脸上的疼痛更甚。混乱中,
贾琏见王熙凤动手打平儿,更是火上浇油,借着酒劲,竟从墙上抽出挂着的宝剑,
指着王熙凤吼道:“你这妒妇!今日我非要杀了你不可!”王熙凤见他动剑,先是一惊,
随即更是悲愤交加,哭喊着“你杀了我干净!”便扑上去撕打。贾琏酒醉之下,脚步虚浮,
被王熙凤一撞,剑尖乱晃,险些伤及旁人。鲍二家的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只会哭嚎。
平儿顾不得脸上疼痛,急忙上前阻拦,死死抱住贾琏持剑的胳膊:“二爷!使不得!
快放下剑!”她又扭头对王熙凤哭求:“二奶奶,您快别说了,仔细气坏了身子!
”一场闹剧,惊动了整个贾府。最终,还是惊动了贾母。老太太被簇拥着赶来,见此情景,
气得连声念佛。她先命人夺下贾琏的剑,又呵斥王熙凤:“凤丫头!你也是大家子出身,
怎地这般不顾体面,和男人拌嘴动手?他纵然有不是,你也不该如此!”王熙凤跪在地上,
哭得哽咽难言:“老祖宗……他……他竟要杀我……”贾母又转向贾琏,
语气却缓和了许多:“琏儿,你也是胡闹!凤丫头怀着你的骨肉,你不在跟前体贴,
反倒生出这些事来!还不快给你媳妇赔个不是!”一场险些闹出人命的风波,
在贾母三言两语间,便被定性为“夫妻拌嘴”,轻描淡写地化解了。
贾琏被罚跪祠堂思过一夜,鲍二家的被撵出府去,而率先发难、动手打人的王熙凤,
只因“怀着身孕,受了委屈”,反而得了贾母一番温言安抚。众人散去,留下满地狼藉。
平儿脸颊红肿,默默收拾着残局。她扶着醉得东倒西歪的贾琏往祠堂去,夜风一吹,
贾琏酒劲上涌,蹲在路边呕吐起来。平儿轻拍着他的背,等他吐完,递上一方干净手帕。
贾琏抬起头,眼神浑浊,带着几分狼狈和茫然。月光下,平儿看到他手腕内侧,
有几道新旧交错的浅粉色疤痕,像是利刃划过所留。那绝非今日争斗所致。平儿心头一震,
想起府里私下传闻,说二爷时有抑郁之态。她原不信,此刻亲眼所见,
才知这风流倜傥的琏二爷皮囊之下,竟藏着如此深的苦痛。贾琏察觉到她的目光,
猛地缩回手,用袖子遮住疤痕,语气恢复了几分平日的油滑,
却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看什么?还不快扶我起来。”平儿垂下眼,不再多看,
默默扶起他。祠堂阴冷,她替他铺好垫子,又倒了杯热茶。“今日……连累你了。
”贾琏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忽然低声说了一句。平儿摇摇头,没说话。
她看着祠堂里森然的牌位,想着贾母方才那番“男人偷情无罪,女人反抗有罪”的论断,
一股冰冷的绝望浸透四肢百骸。在这深宅大院,规矩是男人的护身符,却是女人的催命符。
凤姐儿再厉害,终究越不过这道天堑。而她平儿,一个卑微的丫鬟,命运更是轻如草芥。
今日之辱,他日之祸,或许都只是这吃人规矩下的寻常一幕。她替贾琏掩上祠堂的门,
转身走入沉沉的夜色里。脸上的指印犹在,心底的念头,却比这秋夜更寒,更坚定。
那缕青丝换来的承诺,或许远远不够。她要在这风月无边的泥潭里,为自己,
寻一条真正的生路。贾府上下,白茫茫一片。贾敬的丧事,办得风光又压抑。
灵堂设在宁国府,香烟缭绕,僧道诵经声日夜不绝,衬得那“当大事”的匾额愈发肃杀。
作为荣国府的得力下人,平儿被王熙凤支使着,频繁往来两府之间,递送物品,传达消息,
一双脚几乎不曾停歇。这日,王熙凤将平儿唤至跟前,脸上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平静。
她孕肚已显,脸色却苍白得厉害,眼下两团青黑,显是连日操劳兼心气不顺所致。
她递给平儿一个沉甸甸的锦盒,里面是一对成色普通的金镯子。“把这个送到小花枝巷,
给那位新二奶奶。”王熙凤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冰冷,“就说我身子重,不得闲亲自去道贺,
一点心意,望她笑纳。你机灵些,好好看看,那位尤二奶奶,究竟是何等天仙人物,
能把我们二爷的魂儿都勾了去,连热孝在身、停妻再娶的罪名都顾不得了。”平儿心头一凛。
贾琏偷娶尤二姐的事,她早有耳闻,却不想凤姐儿已知晓得如此清楚,
更在这当口让她去“道贺”,其用心,不言而喻。这是试探,是示威,也是将她往火坑里推。
她垂下眼帘,接过锦盒:“是,二奶奶。”小花枝巷的院子不大,却收拾得齐整,
透着几分过日子的新鲜气。尤二姐迎出来,穿着一身素净的月白袄裙,鬓边只戴一朵小白花,
容貌确是十分标致,眉眼间带着一股我见犹怜的怯弱温柔。她见平儿是王熙凤身边来得人,
先是有些惊慌,随即强自镇定,客客气气地将平儿让进屋内。“劳动平姑娘跑一趟,
真是过意不去。”尤二姐亲自斟了茶,声音软糯,“姐姐……凤姐姐身子可好?
”“二奶奶安好,只是孕期辛苦,又逢府里大事,不得空来看望二奶奶。”平儿将锦盒奉上,
语气恭敬却疏离。尤二姐打开盒子看了看,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神色,随即盖上,
叹道:“姐姐太客气了。我在这里,一切从简,实在当不起。说起来,也是我的不是,
惹得姐姐生气……”她说着,眼圈竟微微泛红,拿起帕子拭了拭眼角。
平儿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尤二姐,看似柔弱,话里却藏着机锋,一句“惹得姐姐生气”,
便将过错轻轻推了出去,倒显得王熙凤善妒不容人。“二奶奶言重了。”平儿淡淡道,
“我们二奶奶最是明理不过,只是如今府里正值孝期,二爷此举,着实……有些欠妥。
若传扬出去,于二爷前程有碍。”尤二姐抬起泪眼,看向平儿,
目光里带上了几分审视和拉拢:“平姑娘是明白人。不瞒你说,我如今这处境,
也是如履薄冰。只盼着能安生度日,绝不与凤姐姐争什么长短。
只是……二爷他……”她欲言又止,脸上泛起一抹红晕,“我如今……已是有了身孕了。
”平儿端茶的手几不可察地一顿。果然!这才是最要命的!尤二姐竟在这个当口怀了孩子!
若生下男丁,贾琏那句“若生儿子,必休了王熙凤”的醉话,
恐怕真要成悬在凤姐头顶的一把利剑。尤二姐见平儿不语,压低声音道:“平姑娘,
我知道你在凤姐姐跟前不易。她那性子……想必你也受了不少委屈。
若你肯……日后我若能有个立足之地,绝不会忘了你的好处。”这话已是赤裸裸的邀约,
要平儿背叛王熙凤,投靠她这边。平儿心中冷笑。这尤二姐,
以为自己攀上了贾琏就能一步登天,却不知已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王熙凤岂是能容人的主?
她放下茶杯,神色不变:“二奶奶说笑了。平儿只是个丫鬟,主子们的事,不敢妄议。
二奶奶既有了喜,更该好好保养才是。话已带到,平儿还要回府复命,告辞了。
”尤二姐见她油盐不进,脸上闪过一丝失望和恼意,却也不好强留。平儿走出小院,
并未立刻回府。她想起王熙凤吩咐的“好好看看”,便绕到后院,想瞧瞧这院子的格局。
刚走近墙角,却隐约听见灵堂方向传来些异样声响。今日是贾敬大殓之日,
宁国府灵堂本该庄严肃穆。鬼使神差地,平儿循着声音,悄悄走到灵堂一侧的角门外。
门虚掩着,里面的景象让她如遭雷击,浑身血液瞬间冰凉——只见灵堂帷幕之后,
贾琏竟将尤二姐紧紧搂在怀里!尤二姐云鬓微乱,脸颊潮红,正半推半就地依偎着他。
贾琏低着头,在她颈边厮磨,全然不顾不远处就是停灵的棺椁,不顾满堂的香烛纸钱,
不顾这举哀守孝的人伦大防!空气中弥漫着线香味、蜡烛味,
还有一种……一种男女情动时的暧昧气息。平儿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强烈的恶心感直冲喉咙。
她猛地捂住嘴,转身踉跄着跑到墙根下,再也忍不住,弯腰剧烈地干呕起来,
直呕得眼泪都迸了出来。这不是气愤,不是鄙夷,而是一种生理上的极度厌恶。这些男人,
平日里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将最龌龊的欲望,
肆无忌惮地宣泄在这代表最后体面与哀思的灵堂之上!这贾府,从根子上就已经烂透了!
父权、族规,不过是他们纵欲享乐的遮羞布!她扶着冰冷的墙壁,喘息良久,才勉强直起身。
擦去眼角的泪渍,她脸上最后一丝温度也褪尽了。尤二姐的拉拢,王熙凤的利用,
贾琏的荒唐……这一切,都让她感到无比的窒息和荒谬。她想起多姑娘的青丝,
想起鲍二家的醉卧,想起这灵堂后的孝期偷欢……贾琏的风流债,一桩桩,一件件,
都像污浊的泥沙,不断累积。而她,平儿,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丫鬟,手中悄然记录的,
已不仅仅是贾琏的罪证,更是这整个贾府男权世界腐败堕落的证据。
那个孩子……尤二姐腹中的孩子,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吗?平儿不知道。她只知道,
自己不能再被动地周旋下去了。风月无边,终将成空。而她,必须在这成空的废墟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哪怕代价惨重。尤二姐有孕的消息,像一滴冷水溅入滚油,
在荣国府表面平静的湖面下炸开。王熙凤的院落,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
小丫鬟们走路都踮着脚尖,生怕一个不慎,触怒了面色一日阴过一日的二奶奶。这日深夜,
王熙凤将平儿单独唤入内室。烛光摇曳,映着她苍白而锐利的侧脸,
孕肚在宽松的寝衣下依然显眼,却只增添了几分沉郁的压迫感。
她从妆匣底层取出一个寸许长的瓷瓶,瓶身素白,无任何标记,轻轻放在桌上,
发出“嗒”的一声轻响。“平儿,”王熙凤的声音平静得可怕,目光却像淬了毒的针,
紧紧盯着她,“小花枝巷那位,胎气似乎不太稳当。你明日去送些补品,把这个,
混在她的饮食里。”平儿的心猛地一沉,尽管早有预感,亲耳听到这诛心的命令,
还是让她指尖发凉。她看着那个小白瓶,仿佛能看到里面晃动的致命液体。
“二奶奶……这……”她试图挣扎。“怎么?”王熙凤挑眉,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
“你心软了?还是觉得,她肚子里的那块肉,将来能给你更大的前程?
”平儿立刻跪下:“平儿不敢!平儿的一切都是二奶奶给的,绝无二心!
只是……此事关系重大,若是有个万一……”“没有万一!”王熙凤打断她,语气斩钉截铁,
“做得干净些,没人会知道。那尤二姐本就根基不稳,胎象不安,小产了也是常事。难不成,
你还指望她生下个儿子,将来骑到我头上,连带你这‘旧人’也一并收拾了?”字字句句,
都敲在平儿最敏感的神经上。她知道,这不是商量,是命令,是投名状。不做,就是背叛,
立刻就会成为王熙凤下一个清除的目标。她垂下头,看着冰冷的地面,深吸一口气,
再抬起时,脸上已是一片顺从的平静:“平儿明白了。二奶奶放心。”她伸出手,
拿起那个瓷瓶。触手冰凉,沉甸甸的,仿佛坠着一条未成形的性命。次日,
平儿提着食盒去了小花枝巷。尤二姐见她来,神色间多了几分戒备和不易察觉的优越感,
大约是仗着腹中胎儿,自觉地位不同往日。平儿一如往常,
恭敬地摆出几样精致的点心和小菜,说是二奶奶吩咐送来给二奶奶补身。
趁尤二姐不注意的间隙,平儿的手指颤抖着,拔开了瓷瓶的木塞。然而,
就在药粉即将倒入汤羹的刹那,她动作停住了。脑海中闪过贾琏手腕上的疤痕,
闪过灵堂那令人作呕的一幕,也闪过王熙凤冷酷的眼神。她飞快地环顾四周,
迅速将瓷瓶里的粉末倒进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空香囊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