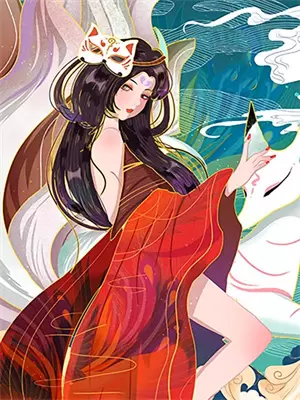建元二十七年,暮春。
建康城外,通丝路码头。
晨雾没散透,风一裹,就卷着黄沙往人脸上扑。
沈青芜抬手挡了下,指尖触到一片粗糙 —— 是骆驼绒毛上沾的沙粒。
三十头骆驼排得笔直,每头背上都压着两捆青油布。
油布裹得紧,却拦不住里头的动静:丝绸蹭着丝绸,是细碎的 “沙沙” 声;茶叶渗着潮气,是淡淡的苦香。
“少东家,铁器箱在这儿!”
李三的嗓门炸开,沈青芜转头,看见那小子正蹲在最前头的骆驼旁,手扒着个黑铁箱。
她走过去,指尖刚碰到油布,就被箱角硌了下。
“挪挪,别压着榫卯。” 沈青芜弯腰,左手护腕蹭过油布,发出 “咔嗒” 一声。
护腕是黑铁的,内侧磨得发亮。
她掀开一角,露出几道浅白疤痕 —— 像三条细虫,趴在手腕上。
“少东家,这疤还是当年学火铳烫的吧?” 李三凑过来,眼神直勾勾的。
“嗯。” 沈青芜没多话,指尖已经摸到了腰间的玉佩。
是算盘形的羊脂玉,边缘被摩挲得泛暖光。
算盘框上刻着细纹路,是母亲亲手描的丝路图。
她捏着玉佩转了圈,耳边突然响起来母亲的声音:“带着它走丝路,能保平安。”
那是母亲咽气前说的。当时这玉佩还沾着血,攥在母亲手里,指缝里全是红。
“青芜丫头!”
拐杖拄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沈青芜回头,看见周伯正往这边走。
老人头发全白了,粗布短打沾着沙,手里捏着封火漆信 —— 火漆上印着 “汉风商盟” 四个篆字。
“这是你娘的旧信。” 周伯把信递过来,声音发颤,“当年跟大月氏国王波调通商,他俩签的契书,就夹在里头。”
沈青芜接过信,火漆凉得硌手。
“大月氏现在是烂摊子。” 周伯突然压低声音,拐杖往西北方向指了指,“三股绳绞着:北炎使团带着儒教的规矩压着,说佛教是‘蛮夷教’,要波调赶僧侣;草原上的瀚海部盯着皮毛,三天两头抢边境;波调自己呢?一边要靠北炎的粮食渡旱灾,一边不敢惹瀚海部,两头受气。”
沈青芜的指尖紧了紧,信纸皱起一道印。
“还有个卢嵩,你得防着。” 周伯的眉头拧成疙瘩,“北炎使团的头,出了名的‘儒教倔驴’。见了商人就骂‘铜臭’,见了僧侣就喊‘蛊惑民心’。你到了那边,别跟他硬刚,拿你娘的信说事 —— 波调念旧情,或许能护你。”
“我知道了。” 沈青芜把信塞进内袋,转身喊老周。
老周正给骆驼喂水,听见喊声,拎着水瓢就跑过来。
他跟周伯同名,却是个精壮汉子,腰间别着把短刀,脸上一道刀疤从眉骨划到下颌 —— 那是当年跟沈母走丝路,跟盗匪拼出来的。
“老周,” 沈青芜递过个布包,里面是碎银和纸条,“沿途盯紧粮价,尤其是疏勒关。我听说那边粮价涨了三成,流民都快啃树皮了。”
老周捏开布包,扫了眼纸条,拍着胸脯笑:“少东家放心!疏勒关的粮栈老板,我跟他喝过酒。保准给你问得明明白白 —— 粮食要是能成,打通商路就稳了!”
沈青芜点点头,转身往码头尽头走。
那里立着块青石碑,刻着 “丝路碑” 三个大字。
碑面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商队名字,最上头那行,是 “汉风商盟沈氏”。
她指尖抚过 “沈氏”,眼前突然黑了下 ——
十岁那年的码头,也是这样的黄沙天。母亲从骆驼上跌下来,胸口插着把弯刀,血把胡服染得通红。她跑过去抱住母亲,看见母亲的手紧紧攥着这枚玉佩,指缝里的血顺着玉佩往下滴。
后来商盟的人说,母亲是为了护一支中亚僧侣商队,才被瀚海部的盗匪报复的。
“娘,我要让丝路少点刀光,多点算盘声。”
沈青芜对着石碑轻声说,指尖把玉佩攥得更紧了。
“少东家!时候到了!”
老周的喊声传来,沈青芜回头,看见太阳已经爬得老高,金色的光洒在黄沙上,把骆驼的影子拉得老长。
她走到一匹棕红色的河西马旁 —— 这是沈母的马,鞍具还是当年的,磨得发亮。
沈青芜翻身上马,右手举起马鞭,朝着商队喊:“出发!”
马鞭落下,骆驼发出低吟,缓缓迈开步子。
“叮铃 —— 叮铃 ——”
骆驼脖子上的铃铛响起来,在黄沙里飘得远。
沈青芜骑在马上,回头望了眼建康城,直到城墙的影子彻底消失在天边,才转头往前看。
丝路像条黄色的带子,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少东家,你听!”
老周的声音突然传来,沈青芜勒住马,侧耳细听 —— 远处有马蹄声,很轻,大概三匹,节奏轻快。
“是探路的。” 沈青芜笑了笑,回头对伙计们说,“走丝路得会听马蹄声:三匹快马是探路的,十匹以上带甲的是军队,乱哄哄的是流民。耳朵要比眼睛灵。”
李三挠着头笑:“还是少东家厉害!我们以前只知道看旗子。”
“这是沈夫人教的。” 老周骑着骆驼凑过来,眼里带着怀念,“当年沈夫人带着我们走丝路,靠听马蹄声,躲过三次盗匪。”
沈青芜没接话,轻轻夹了夹马腹。
河西马懂意,步子快了些。
太阳往西斜的时候,他们到了一片绿洲。
“扎营!”
老周喊了声,伙计们立刻忙起来:搭帐篷的搭帐篷,生火的生火,李三抱着水囊往小溪跑。沈青芜坐在篝火旁,解下腰间的玉佩。
玉佩的侧面有个暗格,她轻轻一掰,里面掉出个微型算盘 —— 只有巴掌大,算珠是黑曜石的。
“少东家,还算账呢?” 老周凑过来,手里拿着个饼子。
沈青芜没抬头,指尖拨着算珠:“一匹丝绸换五张中等皮毛,一张皮毛在南炎能卖二两银子,扣除关税和运费,每匹能赚三两。三百匹就是九百两。”
“我的娘!” 李三刚跑过来,听见这话,眼睛都直了,“比咱们商盟的总账房还精!”
老周笑了,拍了拍李三的肩膀:“这叫‘将门出虎女’!沈夫人当年算得更细,连骆驼的草料钱都能算到文。”
沈青芜停下算盘,抬头望向丝路尽头。夜色已经漫上来,星星挂在天上,亮得刺眼。
“娘当年就是这么算的。” 她轻声说,“咱们不能砸了她的招牌。”
话音刚落,老周突然站起来,脸色变了:“少东家,你听!”
沈青芜立刻侧耳 —— 远处的马蹄声,不再是轻快的 “嗒嗒” 声,而是沉实的 “咚咚” 声,像鼓点,敲在沙地上。
而且不止三匹。
“多少?” 沈青芜的手按在腰间的短刀上。
老周闭着眼听了会儿,声音发紧:“最少十匹,而且是带甲的 —— 马蹄声里有甲片的‘哗啦’声!”
李三的脸瞬间白了:“是、是北炎的兵?还是瀚海部的盗匪?”
沈青芜没说话,抬头望向黑暗处。
那里有片黑影,正朝着绿洲移动。
马蹄声越来越近,震得沙粒都在跳。
篝火的光映在她脸上,一半亮,一半暗。
“都别出声。” 沈青芜压低声音,手已经摸到了微型算盘里的细铁针,“老周,你带两个伙计去帐篷后守着。李三,把火压小 —— 咱们看看,来的是谁。”
黑影越来越近,马蹄声越来越沉。
绿洲里的风突然变了向,裹着黄沙往帐篷里灌。
沈青芜盯着那片黑影,指尖把铁针捏得发疼道:“大家都警醒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