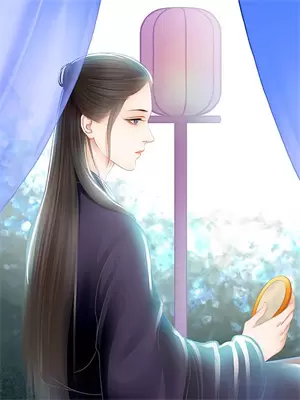老陈头躺在病床上,每一次呼吸都扯着肺叶疼。医生说他最多还有三个月。他不怕死,
但他怕极了死后的事——他这辈子,亏心事做得太多了。年轻时为了争一口水井,
他失手打死了邻居张铁匠,然后伪造了意外现场。张铁匠那死不瞑目的眼睛,
成了他几十年的梦魇。他拼命赚钱,修桥补路,想要求个心安,可他知道,远远不够。
他笃信,下了地府,这笔账是要连本带利还的,怕是要在油锅里炸上几百年。
就在他绝望之际,一个游方的黑衣老道找上门来,盯着他的脸看了半晌,幽幽地说:“先生,
你孽债缠身,阳寿将尽,死后怕是难逃地狱之苦啊。”老陈头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
苦苦哀求。老道沉吟良久,才压低声音说:“有个法子,叫‘借阴寿’。不是借活人的,
而是借……死人的。找个横死之人,他阳寿未尽却枉死,魂魄困于阴阳缝隙,
你用秘法将他的残余寿元‘嫁接’到自己身上,便能多活几年。只是……”“只是什么?
”老陈头急忙问。“此法有伤天和,且一饮一啄,皆有定数。你借了他的寿,
便也承了他的债,他死前的怨念、痛苦,都会缠上你。而且,一旦开始,便不能停下,
直到将他的‘阴寿’耗尽为止。你可想好了?”老陈头已被对死亡的恐惧吞噬,
哪还顾得了以后,连连点头。他立刻想到了张铁匠。这不正是最合适的横死之人吗?
他既有未尽的阳寿,
又是自己欠下的债……一种扭曲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这或许是弥补的一种方式?
老道在张铁匠的荒坟前布下法阵。那晚月黑风高,老陈头按照指示,
将写有自己生辰八字的符纸与张铁匠坟头的一撮土一同烧掉,喝下混合了香灰的符水。
一阵阴风刮过,他感觉一股冰寒刺骨的气息钻入四肢百骸,病痛竟然真的瞬间减轻了大半。
一个月后,老陈头奇迹般地出院了,健步如飞,比生病前还要硬朗。他心中狂喜,
对那老道感激涕零。但很快,怪事接踵而至。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做梦,
梦里永远是那个潮湿、闷热的夏夜,他举起石头,一次又一次地砸向张铁匠的后脑。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石头砸碎头骨的触感,温热的血溅到脸上的黏腻。
张铁匠临死前那难以置信、充满怨恨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
“陈哥……为什么……”梦里的声音嘶哑破碎。老陈头每次都会惨叫着惊醒,浑身冷汗。
白天也不得安宁。他总能在眼角余光里,瞥见一个模糊的、头破血流的身影,
静静地站在墙角或门后。家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铁锈味,那是血的味道。他吃饭时,
会莫名咬到沙子,仿佛嚼到了坟头的土。喝水时,喉咙里总有一股灼烧感,
像是喝下了当年那晚的恐惧。他变得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就能让他暴跳如雷,
眼神里时常闪过张铁匠生前那种执拗和凶狠。家人都觉得他变得陌生又可怕。
更让他恐惧的是,他发现自己对打铁产生了莫名的兴趣。
他鬼使神差地在家里的车库弄了个小炉子,买来锤子和铁块,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
那动作、那姿态,竟与当年的张铁匠有七八分相似!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
仿佛有另一个灵魂在他体内操控着这具身体。“他在借我的寿,也在用我的身子‘活’过来!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中炸开。老陈头终于明白,这“借阴寿”根本不是他在利用张铁匠,
而是张铁匠那未散的怨魂,借助这个仪式,正在一点点地侵蚀、占据他的身体和意识!
他借来的不是寿元,而是一个如影随形的索命债主!他发疯似的想找到那个老道,
可老道早已不知所踪。一年后的同一天,也是张铁匠的忌日。家人发现老陈头死在了车库里。
他穿着不知从哪找来的、张铁匠生前常穿的那种粗布围裙,手里紧紧握着一把打铁锤。
他的死状极其诡异——后脑勺一片血肉模糊,像是被重物反复击打。而他的脸上,
凝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一半是极致的恐惧和痛苦,另一半,嘴角却诡异地向上弯起,
带着一丝属于张铁匠的、沉冤得雪般的狞笑。他借来的“阴寿”,刚好一年。债,还清了,
连本带利,用的是他自己的命和魂。老陈头的死状太过诡异,警方封锁了现场,
以“意外”草草结案——尽管谁都解释不了一个人如何能自己用重物击打自己的后脑勺至死。
葬礼办得悄无声息,亲戚们议论纷纷,都说老陈头是中了邪,或是被厉鬼索了命。
只有老陈头的儿子陈默,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车库角落里那个简易的打铁炉,
以及炉边几页写满潦草字迹的纸。
纸上反复写着“对不起”、“张铁匠”、“借阴寿”、“他在找我”等字眼,
字迹从一开始的惶恐到后来的扭曲,仿佛书写者的精神正逐渐崩溃。
陈默隐约知道父亲年轻时与张铁匠家的恩怨,心中疑窦丛生。他安葬了父亲,
将那份不安与疑惑深深埋藏,继续自己的生活。他刻意远离了老家的房子,在城里努力工作,
结婚生子,试图将父辈那诡异的阴影彻底抛开。转眼二十年过去。陈默的儿子陈星,
已经是个十八岁的大小伙子。陈默事业有成,家庭和睦,那场关于父亲的噩梦似乎早已远去。
然而,就在陈星十八岁生日那天晚上,一切都变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切完蛋糕,
陈星回到自己房间打游戏。深夜,陈默被儿子房间里传来的“咚咚”声吵醒。
他以为是儿子在敲键盘,起身想去提醒他早点睡。走到门口,那声音更清晰了,不是敲键盘,
更像是……用硬物敲击什么的声音。他推开房门,只见陈星背对着他,坐在电脑前,
但电脑屏幕是黑的。他手里拿着一个沉重的金属水杯,正一下,一下,
极其有节奏地敲击着自己的额头。动作僵硬,仿佛提线木偶。“小星!你干什么!
”陈默一个箭步冲上去,夺下水杯。陈星缓缓转过头,眼神空洞,表情麻木,
额头上已经一片青紫。“爸,”他开口,声音带着一种不属于他的、沉闷的沙哑,
“我在……打铁呢。”“打铁”两个字像一把冰锥,瞬间刺穿了陈默二十年的伪装,
将深埋的恐惧彻底挖了出来。他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父亲死前对打铁的痴迷,
那张纸上“张铁匠”的名字,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从那天起,陈星就变了。
他变得沉默寡言,对原本热爱的篮球、游戏失去了所有兴趣。他常常一个人呆在房间里,
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有时陈默偷偷从门缝看进去,会发现他正对着墙壁,
手指在空中无意识地划动,像是在模仿打铁的动作。更可怕的是,他开始说梦话。
不是含糊的呓语,而是清晰、带着浓重口音的句子,那是陈默记忆中,早已模糊的乡下口音。
口井……本该是我家的……”“凭什么……你活了那么久……我烂在了土里……”陈默听着,
浑身冰凉。他知道,那不是梦话。那是张铁匠借着他儿子的嘴,在诉说当年的冤屈。
陈星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原本健壮的小伙子,迅速消瘦下去,脸色蜡黄,
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病变。他只是虚弱,仿佛生命力正被一点点抽走。有时,
他会突然捂住后脑,发出痛苦的呻吟,说那里像被针扎一样疼。陈默崩溃了。他意识到,
父亲当年的“债”,并没有还清。那通过“借阴寿”引入门的恶鬼,像一种恶毒的诅咒,
缠绕着他们的血脉,在下一代身上,再次爆发了。他辞掉工作,带着儿子四处求医,
从顶尖的神经内科到精神科,再到各种知名的心理医生,结果都是一样——查无实据,
病因不明。有医生隐晦地建议他,或许可以试试“别的”途径。走投无路之下,
陈默想起了父亲遗物中那些潦草的笔记。他翻箱倒柜找了出来,看着上面“借阴寿”三个字,
一个大胆而绝望的念头产生了:找到当年那个黑衣老道,或者,找到懂得破解此法的人。
他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和资源,在网上搜寻各种诡异的信息,
拜访那些隐藏在都市角落或深山古观中的“高人”。大多数人听了他的描述,
要么摇头表示无能为力,要么直接将他拒之门外,只说“因果太重,沾惹不起”。
就在陈默快要绝望时,他通过一个线人,
联系上了一个住在偏远山区、据说精通各种阴邪秘术的老婆婆,人们都叫她“鬼婆”。
鬼婆住在山坳里一间几乎与世隔绝的木屋里。她看起来极其苍老,满脸皱纹如同风干的树皮,
但一双眼睛却锐利得惊人,仿佛能看穿人心。陈默带着已经虚弱到需要搀扶的陈星,
跋涉而来。他没有任何隐瞒,将父亲陈老头如何害死张铁匠,如何借阴寿,如何诡异死亡,
以及如今儿子身上的异状,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鬼婆静静地听着,
浑浊的眼睛偶尔闪过一丝精光。她让陈星走到她面前,伸出枯瘦如柴的手,
轻轻按在陈星的额头上,又翻看了他的眼皮。她的手指触碰到陈星皮肤时,陈星猛地一颤,
喉咙里发出一种类似野兽般的低吼。鬼婆松开手,长长地叹了口气,
声音沙哑:“造孽啊……果然是‘阴债缠身,父债子偿’。”“婆婆,求您救救我儿子!
他还年轻,他什么都不知道啊!”陈默噗通一声跪了下来,声泪俱下。
鬼婆摇了摇头:“你父亲当年种下的因,结出了恶果。他以为借来的是寿元,
实际上是引狼入室,将张铁匠那口未散的怨气,直接种进了自己的魂魄里。
这怨气与他的血脉相连,如同跗骨之蛆。他死了,这怨气却没有消散,反而顺着血脉,
找到了下一代中阳气最弱、或者说,与他命格最像的一个——你的儿子。
”她指着陈星:“你看他的眼神,走路的姿态,甚至说话的语气,是不是越来越像你描述的,
你父亲后来的样子?那不是模仿,是张铁匠的怨念,正在借助你父亲残留的气息,
以及你儿子的身体,一点点‘复活’。”“那……那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陈默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办法……”鬼婆沉吟着,眼神复杂地看着陈默,“有,
但极其凶险,而且代价巨大。”“什么办法?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陈默急切地说。
“根源在于张铁匠的怨念不散。普通的超度,
已经无法化解这积累了近五十年、又与你们家族血脉纠缠在一起的怨气了。”鬼婆缓缓说道,
“只有一个法子——‘逆溯归源,斩断因果’。”“什么意思?”“我需要布置一个法坛,
引导你儿子的意识,逆着时间,回溯到当年那个‘借阴寿’的仪式现场,
甚至……回溯到张铁匠被杀的那个夜晚。”鬼婆的声音低沉而肃穆,
“让他亲身体验那段因果,找到怨念的核心。然后,由你,
作为血脉的传承者和债务的承认者,进入那个‘意识空间’,去面对张铁匠的怨魂,
了结这段公案。”“这……这能做到吗?”陈默感到难以置信。“以魂为引,以血为媒,
可以短暂地构建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幻境’。”鬼婆说,“但你要明白,那虽然是幻境,
但里面的凶险却是真实的。张铁匠的怨魂积累了近五十年,在你父亲和你儿子的‘滋养’下,
已经非常强大。你进去,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的意识可能会被撕碎,
或者永远被困在那个噩梦里。而你的儿子,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被怨魂彻底吞噬,
他也将魂飞魄散。”陈默看着儿子那空洞而痛苦的眼神,没有丝毫犹豫:“我去!婆婆,
告诉我该怎么做。”鬼婆看着他决绝的眼神,点了点头:“好。但你要记住几点:第一,
在那个空间里,恐惧是你的催命符,你必须保持绝对的清醒和勇气。第二,
不要试图用暴力对抗怨念,那只会让它更强。你要找到他怨气的核心,尝试……化解。第三,
时间有限,一旦香炉里的引魂香烧完,你们还没回来,通道就会关闭,
你们就永远留在那里了。”她开始准备。木屋中央被清空,画上复杂的符阵。
她让陈星躺在符阵中央,在他周围点上七盏油灯,称为“七星护命灯”。
她交给陈默一柄用桃木削成的短剑,上面刻满了符文。“这剑伤不了活人,
但能斩断阴邪纠缠。关键时刻,或许能护住你。”她又拿出一根暗红色的线,
一端系在陈默手腕上,另一端系在陈星手腕上,“这是‘血脉牵魂丝’,
能保证你在幻境中找到他,也能在最后时刻,将你们一起拉回来。”最后,
她在法坛前点燃了三炷引魂香,青烟袅袅升起,却不散开,而是在空中诡异地盘旋。“躺下,
握住你儿子的手,闭上眼睛,无论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都不要松开。”鬼婆命令道。
陈默依言躺下,紧紧握住陈星冰冷的手。鬼婆开始用一种古老而晦涩的语言吟唱,
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木屋里的温度骤然降低,那七盏油灯的火焰开始剧烈地摇曳,
变成了一种诡异的绿色。陈默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仿佛整个灵魂都被抽离了身体。
周围的景象开始扭曲、旋转,木屋的轮廓模糊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无数闪烁的、破碎的记忆片段。
他看到了父亲苍老而恐惧的脸,看到了张铁匠那血肉模糊的后脑,
……无数声音在他耳边呼啸——父亲的哀求、张铁匠的诅咒、儿子的惨叫……不知过了多久,
那股天旋地转的感觉终于停了下来。陈默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昏暗、潮湿的巷子里。月光惨白,
照在斑驳的墙壁上。这里的空气闷热而污浊,弥漫着一股垃圾腐烂和铁锈混合的怪味。
周围的建筑低矮破旧,是他记忆中几十年前老家的模样。他来了。
他回到了那个被怨念构筑的,交织着过去与现在的诡异空间。他低头看了看手腕,
那根暗红色的“血脉牵魂丝”散发着微弱的荧光,另一端延伸向巷子的深处。他能感觉到,
陈星就在那个方向。他深吸一口气,握紧了手中的桃木剑,沿着巷子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巷子尽头,是一个废弃的打谷场。场院中央,立着一个简陋的棚子,里面炉火正旺,
发出呼呼的声音。一个模糊的身影,正背对着他,抡着一把大锤,一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