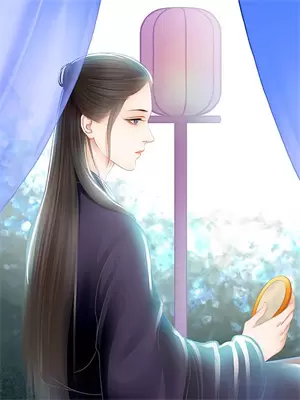我爹第一次用那种眼神看我,是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晚上。我妈上晚班,家里就我俩。
他刚从夜市收摊回来,带着一身仿佛腌入味的油烟和孜然气息。
我们面对面坐在客厅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木头餐桌前,头顶的节能灯管有点接触不良,
光线忽明忽暗。他递给我一根他没卖掉的炸火腿肠,金黄油亮,撒着密密麻麻的辣椒面。
我低头啃着,酥脆的外皮在嘴里咔哧作响。吃着吃着,后颈的汗毛没来由地立了起来。
一抬头,心里猛地一咯噔。我爸没动筷子,也没吃饭。他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
眼神空茫茫的,像是透过我的脸,在瞅别的什么东西。夜市熬夜熬出的满眼红血丝,
嵌在那片空洞里,显得格外瘆人。嗓子眼有点发干,我咽下嘴里的东西,
试探着喊了一声:“爸?”他像是被从梦里猛地拽醒,眼皮狠狠眨了一下,眉头慢慢拧紧,
嘴唇嚅动着,极其陌生地吐出两个字:“小辉?”小辉?我愣住了。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可一时半会儿,脑子就像生了锈,转不动。“爸,你说啥?”我追问,
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点。他浑身剧烈地一颤,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再看他的眼睛,那片迷雾仿佛被风吹散,又变回了让我熟悉的老陈。“啊?没……没啥。
”他慌忙低下头,捡起筷子,声音沙哑得厉害,“快吃,吃完赶紧写作业去。”他埋下头,
胡乱往嘴里扒拉了两口饭,再没看我一眼。可我心里的那股凉意,却顺着脊椎骨,
一点点爬满了全身。小辉?谁是小辉?1.自从那天晚上之后,我就留了心。我发现,
我爸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次数变多了。我们家的老房子隔音不好,
他能在那小小的客厅里来来回回走上十几分钟。那脚步声不像白天那样利索,
而是拖拖拉拉的,带着一种犹豫不决的味道。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
悄悄把房门拉开一条缝往外看。客厅没开大灯,只有卫生间门口那盏昏暗的小壁灯亮着。
我爸就穿着背心裤衩,站在客厅中央,背对着我。他没去厕所,就那么站着,低着头,
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太低了,我听不清,只觉得那调子很奇怪,不像我们这儿的话,
也不像他在摊位上招呼客人时的爽利劲儿。我轻轻叫了一声:“爸?”他猛地转过身,
壁灯的光从他下巴下面照上去,脸显得有点扭曲。“还没睡?”他的声音恢复了正常,
带着点责怪,“明天还上不上学了?”“我起来喝水。”我撒了个谎。“赶紧喝,喝完睡觉。
”他挥挥手,自己先转身回了他和我妈的卧室。我走到茶几边,假装倒水,心跳得厉害。
刚才他那转过来的瞬间,眼神又有点空。而且,他刚才站的位置,正好对着墙上那面旧镜子。
2.小辉这个名字像个钩子,勾得我心里痒痒的。我问我妈:“妈,小辉是谁啊?
”我妈正在叠衣服,手顿了一下,头也没抬:“哪个小辉?你同学?”“不是,
我爸那天晚上叫我小辉。”我妈叠衣服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
语气却还是那么平常:“你听错了吧?你爸一天到晚累得晕头转向,叫错名字有啥奇怪的,
快去把垃圾倒了。”她在搪塞我,我能感觉到。趁着周末他们都不在家,
我溜进了他们的卧室。我爸有个旧木头箱子,放在床底下,平时锁着,
说是放些不值钱的老物件。我知道钥匙在哪,在衣柜顶上那个铁皮饼干盒里。箱子打开,
一股樟脑丸和旧纸张的味道。里面有些旧衣服,几本毛了边的武侠小说,还有一本相册。
我翻开相册,里面大多是我爸妈结婚前后的照片,还有我小时候的糗照。翻到最后一页,
夹层里掉出来一张小小的,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男孩,
勾肩搭背地站在一棵大槐树下,看着也就十一二岁年纪。一个是我爸,小时候脸圆圆的,
笑得见牙不见眼。另一个男孩,瘦一点,眼睛很大,有点腼腆地看着镜头。
他们两个长得居然有五六分相似。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字:“建国与小辉,
一九八五年夏于柳树村。”柳树村?那是我爸的老家,我小时候跟奶奶回去过几次。小辉?
原来真有小辉这个人。他是谁?为什么我爸会对着我叫他的名字?3.没过多久,
奶奶从柳树村来了,给我们送她自己种的青菜。奶奶快七十了,身体还挺硬朗。
我爸那天收摊特别早,一家人一起吃饭。饭桌上,我爸给我奶奶夹菜,说着摊子上的事。
看起来一切正常。我瞅准个机会,假装不经意地问:“奶奶,小辉是谁啊?
我看我爸旧照片里有个叫小辉的。”“啪嗒!”我奶奶手里的筷子掉在了碗里,
发出清脆的响声。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我爸猛地抬头看我,眼神复杂,有惊讶,
好像还有点慌乱。我妈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瞪我:“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瞎问什么!
”奶奶弯腰捡起筷子,手有点抖。她没看我,也没看我爸,只是低着头,
用衣角慢慢擦着筷子,声音又轻又哑:“小孩子家别瞎打听,都是以前的事了。”“奶奶,
小辉是不是……”“小明!”我爸突然打断我,声音有点严厉,“作业写完了吗?
没写完赶紧去写!”我闭上嘴,心里却更确定了。小辉的事,他们都知道,但都在瞒着我。
晚上奶奶临睡前,把我拉到一边,摸着我的头,叹了口气:“小明啊,
你爸……他心里有块疤,很多年了。你别去碰,啊?对他好,对你也好。”什么疤?
和小辉有关吗?奶奶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哀伤和担忧,让我没敢再问下去。
4.我爸的异常越来越明显。他有时候会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但眼神根本没有焦点,
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拉着什么图案。有一天半夜,我被尿憋醒,迷迷糊糊打开房门,
一眼就瞥见客厅有个人影。是我爸。他又站在那面镜子前。但这次不是背对着,
而是脸几乎要贴到镜面上,就那么死死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卫生间透出来的微光映着他半边脸,眼神直勾勾的,带着一种探究,甚至有点凶狠。
那绝不是我爸平时会有的表情。我吓得屏住呼吸,躲在门缝后面。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嘴唇又开始动了。这次,我隐约听到了几个词,断断续续的:“时候未到。
”“我的……”声音很低沉,有点沙哑,语调平板,
完全没有我爸说话时那种带着烟火气的起伏。就在这时,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转过头,
视线精准地投向了我房门的方向。我吓得赶紧缩回头,砰地一声关上门,心脏怦怦直跳。
门外,脚步声靠近,在我门口停了一下,然后又慢慢远去了。那一晚,我几乎没睡着。
5.我们学校有个挺冷门的社团,叫民俗文化研究会,
指导老师是个有点神神叨叨的历史老师。我平时对这些不感兴趣,但现在,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社团活动室堆满了旧书,一股灰尘味。
我在一个落满灰的书架上翻找,手指划过那些发黄的书脊。
什么《地方精怪志异》、《民间丧葬考》看得我头皮发麻。终于,
在一个没有封皮的手抄本里,我看到了一段字迹潦草的话:“魂替之说,古已有之。
谓人之执念深重者,或因至亲横死,心怀大愧,其念力可引亡者残魂依附其身。
初时偶现异状,如口误、行止略改,渐则性情大变,言行皆似亡者,宛如替身。
镜乃通阴阳之器,易照见其魂……”亡者残魂,依附其身,宛如替身。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小辉是死了吗,是因为我爸的愧疚,所以他的魂魄要来找我爸替身。
这段话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进了我的心里。6.我爸那个旧木头箱子,
我又偷偷打开了一次。这次,我翻得更仔细。在箱子的最底层,垫着一块蓝布,布下面,
藏着一个硬壳的笔记本。封面是空白的,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它。
里面是我爸的字迹,从青涩到成熟,断断续续地记录着一些事情。前面大多是些少年心事,
抱怨功课,或者对未来的迷茫。直到我翻到中间偏后的几页。“今天又和小辉吵架了,
都是为了那辆破自行车,我明明知道他也想要,可我就是没忍住。”“小辉走了,
都是我害的。如果我不跟他争,如果我不跑出去,他也不会追出来就不会出事。
”这几页的字迹非常潦草,充满了痛苦和自责。有些字迹被水滴晕开过,像是眼泪。
最后一篇有内容的日记,日期是很多年前了,只有短短一行字,写得力透纸背,
几乎要划破纸张:“小辉,哥对不起你。要是能重来,哥愿意替你。”我合上日记本,
手抖得厉害。所以,小辉真的死了。而且他的死,和我爸有关。我爸一直活在愧疚里。
那句愿意替你,和手抄本上说的执念深重,心怀大愧,完全对上了。
7.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我妈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经常一个人看着我爸发呆,
眼圈红红的。有一天晚上,我起夜,经过他们卧室门口,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抽泣声。
是我妈。“建国,你醒醒好不好?你别这样吓我,”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知道你心里苦,可小辉都走了这么多年了。”里面没有我爸的回应。过了一会儿,
我妈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哀求:“算我求你了,你别再让他缠着你了,
小明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啊。”他?我妈说的是他!她知道!她一直都知道爸爸不对劲,
知道可能和小辉有关!我的心沉到了谷底。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胡思乱想,连妈妈都察觉到了,
甚至用了缠着这个词。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妈眼睛还是肿的。我爸却像没事人一样,喝着粥,
还问我妈:“今天酱料是不是没调好?感觉味道淡了点。”他的语气很正常,
甚至比前段时间还要正常点。可这种正常,在这种背景下,显得更加诡异。我妈低着头,
含糊地应了一声。我看着我爸,他喝粥的样子,拿筷子的手势,都和我记忆里一样。
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那个叫小辉的鬼魂,是不是已经在他身体里住下来了。
8.快到清明的时候,我爸说要回一趟柳树村,给爷爷上坟。他非要带上我。
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回柳树村。村子变化很大,但那股熟悉的泥土和草木气息没变。
奶奶看到我们回来,很高兴,但眼神里总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第二天上午,
我爸带着纸钱香烛,领我去了村里的祠堂。陈姓是村里的大姓,祠堂修得还算气派,
里面摆满了层层叠叠的牌位。我爸点燃香烛,跪在蒲团上,恭恭敬敬地磕了头。
我也跟着照做。上完香,我爸却没立刻离开。他在祠堂角落里徘徊,眼神像是在寻找什么。
最后,他停在一个非常偏僻、积满灰尘的角落,那里空着一小块地方,没有牌位。
他盯着那块空地,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慢慢地蹲下身,从带来的袋子里,
又拿出一叠小小的、粗糙的黄纸钱,就地点燃了。火苗跳跃起来,映着他没有表情的脸。
他低着头,对着那团火,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小辉,哥来看你了。
”我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他果然是在祭拜小辉,在祠堂里,没有牌位的地方,偷偷祭拜。
“哥对不起你,”他的声音带着哽咽,“这么多年了,你是不是还在怪我?”火苗噼啪作响,
祠堂里阴森森的。我看着我爸佝偻的背影,觉得他陌生又可怜。9.从柳树村回来之后,
我爸的变化更具体了。他是个右撇子,炸串递东西都是用右手。可现在,
他有时候会下意识地用左手去拿锅铲,虽然很快会换过来,但那一下非常自然。他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