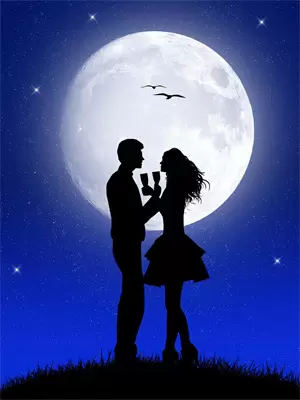我是楚明远,凤翎卫指挥使,刀尖舔血十年,只为太后一句“查前朝遗孤”。江南烟雨里,
我扮作商客,易容术连皇城密探都难辨真伪。可那日,在沈记绣鞋摊前,她盯着我耳后假皮,
轻笑:“大人这妆,化了半日吧?”我心一颤,刀柄抵住她咽喉,
她却捻起我袖口暗纹:“凤翎卫的绣线,掺了金丝的。”她眼波流转,似要洞穿我十年伪装。
1天启三年春,江南南市集。细雨断断续续下了三日,青石板路泛着湿光,
街边摊档陆续收了棚子。我撑伞走过南巷口,风从河面吹来,
带着水腥气和绣线浸久了的微酸味。这地方看着寻常,茶香混着油煎饼的焦香,
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可我知道,越是平静的地方,越容易藏事。我是楚明远,
凤翎卫指挥使,奉太后密令南下查访前朝遗孤踪迹。身份对外是徽州茶商,通关文牒在怀,
住的是南安客栈二楼临街房,每日辰时出门,申时归店,路线不重样。十年行走刀尖,
早已养成习惯——不动声色,不引注目,不露破绽。但我耳后的易容胶皮,
今早贴得偏了半寸。原本只是路过绣鞋摊,想绕到西头找一个卖古物的老头。
那老头据报曾接触过“云”字玉珏相关线索,是我此行唯一明确目标。可脚步刚动,
眼角余光却扫到了摊上那双鞋。靛蓝夹金的丝线。我停住。
那是凤翎卫七品以上文书封角专用线材,宫中监造,民间私藏者斩。
上个月还追查过一批流入市井的残件,至今未结案。如今竟出现在一双三钱银的绣鞋里?
我走近几步,站在摊前,语气平淡:“这鞋结实否?”摊主抬头。是个年轻女子,
约莫二十上下,穿素色布裙,裙角沾着几缕未理净的绣线。她发间用红绳编了银铃,
说话时轻晃,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她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公子耳后胶皮歪了半寸,
风一吹便露馅,穿什么鞋都白搭。”我瞳孔一缩。手已按上腰间短刃。十年来,
我经手大小密案百余件,出入死地数十回,从未有人识破我的脸。更没人敢当面点破。
眼前这姑娘,不过是个摆摊的,眼神却稳得很,笑也笑得自然,仿佛说的不是杀身之祸,
而是谁家晾在外面的衣裳被风吹跑了。我压低声音:“你是什么人?”她没慌,也没退,
只把手中那双鞋递出来,指尖轻轻一挑,露出鞋内一角缝线:“凤翎卫七品以上文书,
皆用蓝金线封角,你们自己定的规矩,反倒忘了?我这鞋里藏的,
可是你们上月追查的‘容州密件’残页。”我心里猛地一沉。那件密件确实在半月前丢失,
途经两省交接驿道,仅凤翎卫高层知晓内容。残页涉及前朝旧部联络暗号,若泄露,
足以牵出三条隐线。而此刻,它竟被缝进一双绣鞋?我盯着她,目光如刀。她却依旧坐着,
手搭在绣绷上,像是随时准备继续穿针引线。“知情者,活不过今日。”我逼近一步,
声音冷得像铁。她抬眸看我,眼底没有惧意,
只有种说不清的笃定:“我知道你在找前朝遗孤,也知道龙脉玉玺不在宫中,
在江南某处祠堂。若你现在杀我,线索就此断绝。若你留我一命,
我可以告诉你——那祠堂的钥匙,是一对刻‘云’字的玉珏。”我僵在原地。这句话,
正是太后密诏末尾那句无人能解的谜语。连陈副使都不知其意,她一个市井女子,如何得知?
我不信巧合,尤其不信这种直插命门的“巧合”。可她的眼神没躲,也没闪,
就像河边长出来的野草,风吹不折,雨打不断。我见过太多人撒谎,有的强作镇定,
有的故作坦然,但没人能在我说出“活不过今日”之后,还这样坐着,
像在等下一针怎么走线。片刻后,我松开手。“你若说谎,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我说完,
转身就走。她没叫住我,只在我迈步时轻轻摇头:“我说的是真是假,你心里已有答案。
倒是公子——下次易容,别用北地胭脂,江南女子不用这个香。”我没回头。
一路回到南安客栈,雨水顺着伞沿滴在门槛外。我关上门,摘下帽子,摸了摸耳后那块胶皮。
确实歪了。那股胭脂味我也闻到了,是北方贵妇常用的檀麝调,我在京中见过几次,
随手用了,没想到竟成了破绽。我坐在桌前,盯着烛火,脑子里反复回放她说的话。
“云”字玉珏……祠堂……钥匙……这些词本不该出现在一个卖鞋女子口中。可她不仅说了,
还说得精准得像握有半份密档。更奇怪的是,她不求财,不求庇护,只拿线索换命。
这种冷静,不像普通百姓。我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雨还在下,
南市集的灯影模糊成一片。那个绣鞋摊已经收了,只剩一根木桩立在原地,
上面挂着块褪色布幡,写着“沈记手工纳底,三钱一双”。沈记。我记下了这个名字。
这女人叫沈清梧。据客栈伙计闲聊提过,她在南市摆摊两年,独居,
有个跛脚老头常来送绣线,养母是个药婆,脾气硬,总念叨她该嫁人。
表面看就是个普通姑娘,靠手艺吃饭,可刚才那一番话,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诱饵,
现在还分不清。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她知道凤翎卫的线。而知道这个的人,
要么是内部叛徒,要么……就是前朝余党。我熄了灯,靠在椅上闭眼。
明日还得去查那卖古物的老头,但现在,我脑子里全是那双鞋,那根线,
还有她说“公子”时嘴角那点若有若无的笑。一个卖鞋的姑娘,
凭什么敢当面揭破凤翎卫指挥使的伪装?她不怕死?还是……她根本不怕我?夜深了,
雨声渐密。我摸了摸颈侧那道旧箭伤。先帝驾崩那夜,我替幼主挡了一箭,
从此再不信任何人。权力场上,情义是刀,信任是毒,唯有刀在手,才能活得久。可今天,
我第一次觉得,或许有一样东西比刀更难防——是那些你以为踩在脚下的尘埃,忽然抬起头,
直视你的眼睛。第二天清晨,我换了新胶皮,特意选了江南本地胭脂,淡得几乎无味。
出门前,我顺手抓了把芝麻糖塞进袖袋。这是习惯,紧张时嚼两粒,心能稳些。走到南市集,
绣鞋摊还没支起来。我站在巷口等。半个时辰后,一辆独轮车吱呀吱呀推来,是她。
她穿的还是那条素裙,腰间挂三个药囊,发间红绳编银铃,动作利落,支摊、摆鞋、挂招牌,
一气呵成。我没上前。她低头穿针,手指灵活,一针一线扎进鞋底,像在写谁的名字。
我站在远处看了很久。直到她抬头,目光穿过人群,准确地落在我脸上。她没笑,也没说话。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像在说:我知道你会来。我也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这一眼,
没言语,也没交手,可我知道——有些事,从昨天开始,已经不一样了。2我站在巷口,
看她支起摊子,穿针引线。昨日那一眼,像根细线缠在心头,松不开。我没走远,
只退到茶棚后头,换了身灰布短打,袖口卷到肘上,手里拎个空竹筐,像个收旧货的贩子。
她低头纳鞋,手指快得几乎看不清动作。
可我知道她在等什么人——那双靛蓝夹金的绣鞋还在摊上摆着,一动没动。这种线,
不该出现在这儿,也不会只是巧合。半个时辰后,药婆家的小童撑伞过来,
说老夫人怕她淋雨。她接过伞,笑着谢了,
又从篮里取出一双新鞋塞给小童:“拿去给你娘穿,底子厚,不硌脚。”小童道了谢跑了。
她望着他背影,眼神静了一瞬,随即收了伞,把摊子一卷,独轮车一推,转身进了小巷。
我跟上去。她绕得极巧,先走东街,再拐北巷,三转两折,像是无目的闲逛。
可每条路都避开了巡街的衙役,也避开了常驻的茶摊耳目。走到第三条岔道,她忽然停下,
从裙兜里摸出一块碎布,包着半块饼,丢在墙角一只黑猫面前。猫窜出来吃,
她便趁机把车藏进柴垛后,自己沿墙根快步往西市去了。我绕过柴堆,贴着屋檐追过去。
西市比南市冷清,屠宰巷更是少有人来。血水顺着沟渠往下淌,腥气扑鼻。
她站在巷尾石阶上,望着对街一间破铺子,不动也不叫人。不多时,
一个跛脚老汉拄着拐杖从暗处走出来,披着油毡斗篷,左袖鼓鼓囊囊。他们没说话。
老汉递出一根铁管,她伸手去接。就在指尖碰到的一瞬,我从屋脊跃下,刀鞘砸在他腕子上。
铁管落地,滚出一段丝线,泛着青灰光泽,上面密密麻麻绣着山川走势,还有几个朱砂点,
标着“脉眼”。“你藏的是什么?”我盯着老汉。他咬牙不语,右手往怀里摸。
我一脚踹在他膝窝,人跪下去,斗篷掀开,露出腰间绑着的一排小瓷瓶,瓶口封蜡,
写着“三日”“五更”之类的字。她没跑,也没拦我,只静静看着我。“你是谁的人?
”我问她。“我是卖鞋的。”她说,“也是那个八岁就没了爹娘的人。
”我冷笑:“你知道凤翎卫的文书线材?知道前朝太医院的‘脉络引线’?还敢用它做鞋面?
”她抬手,解开腰间一个药囊的夹层,取出半块玉珏。正面刻着“云”字,刀痕深而旧。
她没递给我,只是托在掌心:“这东西,本该有两块。一块在我手里,
另一块……听说当年太后赐给了护驾有功的人。”我心里一紧。她继续说:“我爹死前,
烧了一半密档。剩下的副册,被一名老宦官偷偷带出宫,交到了他手上。
那晚你在宫门替幼帝挡箭,颈侧中的是羽箭,箭簇带倒钩,是从右斜插进去的。
当时守门名录全毁,没人记得是谁当值。可那份副册记下了你的名字——楚明远,十七岁,
初任凤翎卫七品执事。”我说不出话。这事只有太后和死去的老内侍知道。
连陈副使都没听过。她看着我:“你查前朝遗孤,是奉命行事。我找灭门真相,是为活命。
你若觉得我在骗你,现在杀了我,没人会问。但下次有人告诉你胭脂香不对的时候,
未必还会站着等你回头。”我盯着她。她没躲开目光,也没有示弱的意思。
就像昨天她说我胶皮歪了那样,平静得像在说天气。我弯腰捡起铁管,打开一看,
里面卷着的丝线图样与地上那段吻合,末端写着“三日后南渡口”。我又看向那老汉,
他仍跪在地上,脸色发青,嘴唇微微颤抖,却不肯开口。“他是谁?”我问。“送信的。
”她说,“不是主事人。”“你们要传什么?”“地形图。”她答得干脆,
“江南三十六镇的地脉走向,每一处‘气眼’都标了记号。这些东西,原本归太医院掌管,
用来勘定皇陵风水。后来……变成了找龙脉的钥匙。”我握紧铁管。
这图一旦落入别有用心之人手中,足以动摇国本。“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上有几道细疤,像是常年穿针留下的。“因为我试过了。
”她说,“躲了十二年,缝了三千多双鞋,换过十七个地方。每次刚摸到一点线索,
就会有人来灭口。直到昨天,我看见你耳后的胶皮歪了,闻到你用的胭脂味不对劲,
我才敢赌一把——你不是他们的人。”“谁的人?”她没回答,只是轻轻摇头。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风从巷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血水,混着雨水流进沟里。
她发间的红绳编着银铃,轻晃了一下,声音很淡。“你不怕我抓你回去?
”我 finally 问。“怕。”她说,“但我更怕一直没人听我说话。
”我松开钳制老汉的手,从怀里掏出一块铜牌扔给他:“拿着这个,去南安客栈后巷等。
天黑前不来,我就当这事没发生过。”老汉愣住,抬头看我,眼里满是惊疑。“走吧。
”我对他说。他迟疑地爬起来,拄着拐一步步退出巷子。我转向她:“你现在可以走了。
”她没动,站在原地,风吹乱了她鬓边一缕发丝。“你不会杀我。”她说,
“因为你心里已经信了一半。”我没否认。她转身去推车,动作利落。走到巷口,她停下,
回头看了我一眼:“三日后南渡口,你要想知道更多,可以来。”然后她走了。
独轮车吱呀吱呀响着,渐渐消失在雨幕里。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截铁管,
掌心已被棱角硌出印子。天上雨还在下,巷子里血水混着泥浆,冲刷着地面。
我低头看了看脚边那段掉落的丝线,青灰色,沾了泥,
却还能看清上面绣的一个点——正对着江南某座废弃祠堂的位置。我把它捡起来,塞进怀里。
转身走出屠宰巷时,我听见远处传来一声鸡鸣。日头快出来了。可我心里清楚,有些事,
已经没法当作没看见。3天边刚泛出灰白,我站在官道旁的泥地里,手里攥着那截青灰丝线。
雨停了,风还刮着,吹得路边枯草伏倒又弹起。沈清梧就在我前头几步远,推着她的独轮车,
车轮压过水洼,发出沉闷的吱呀声。她没回头,只说:“城门快封了。”我没应她。
凤翎卫的规矩摆在那儿——疫区封锁,擅入者斩。可我也知道,那张密图上的朱砂点,
正落在这座死城深处。铁管还在怀里,硌着胸口,像块烧不化的炭。我们走近时,
城门口已经挂上了黑布条,巡防军举着火把来回走动,有人抬着尸首从城里出来,
用草席裹着,扔上板车。一个老妇扑过去哭喊,被兵士一掌推开,摔在泥里。
“西角墙塌了半段。”她说,“能翻进去。”我盯着她背影。她穿着素裙,
腰间三个药囊晃着,发间的银铃一声没响。昨夜她说“三日后南渡口”,可现在,
她带我来了这里。“你改道了。”我开口。“线索变了。”她回身看我,眼神清亮,
“南渡口是幌子,真正的标记在这座城里。你若不信,现在可以回去报信,
等朝廷派大夫来——等他们看完告示上写的‘天罚降世’,再决定要不要救活人。”我没动。
她也不催,只把独轮车靠在树边,解下肩上的粗布包袱,往西边走去。我跟上去。
塌墙处堆着碎砖和烂木头,雨水泡过的土坡滑得很。她手脚利索地攀上去,
裙摆沾了泥也不管。我伸手扶她,她没躲,也没谢,落地后拍了拍手,往前走了两步,
忽然蹲下,从墙缝里摸出一块小木牌,上面画了个歪斜的“井”字。“有人来过。”她说。
我接过木牌,翻看背面,刻着一道短竖线,像是记号。这种暗标,凤翎卫不用,
也不是衙门的手法。我收进袖中,没问她认不认识。城里气味不对。不是单纯的腐臭,
而是夹着一股苦味,像是药熬糊了又混了血。街角堆着几具盖着麻布的尸体,没人收。
一间铺子门板半倒,里面货架空了,地上撒着几包药材,被人踩进了泥里。她弯腰捡起一包,
打开看了看,眉头皱了一下。“怎么?”“三七粉。”她说,“被人抢过,又故意洒出来。
这东西治不了疫病,但能压住咳血——说明有人知道症状,还想藏住真相。
”我看着她把药包塞回怀里。天快黑时,我们在一处破庙落脚。庙门歪斜,神像倒地,
供桌裂成两半。她找来些干草铺在地上,又从药囊里取出薄荷叶,揉碎了撒在四角。“驱邪?
”我问。“驱虫。”她坐下,解开鞋带,倒出些湿泥,“药婆说过,脏地方的虫子会传病。
”我靠着残墙坐下,手按在刀柄上。外面风声渐紧,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又没了。
半夜里,她突然发起热来。额头烫得吓人,嘴里开始说话,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
“云容两脉断……血引龙骨现……”她翻了个身,手指抓着衣襟,
“爹……火盆还没灭……别烧完……”我坐直了身子。她说的“云容”,
我在密档里见过一次——先帝年间,有位御医曾上书提及“云容二脉为龙气锁钥”,
随即被贬出京,再无消息。而我的伤,正是在宫变那夜,从右颈斜穿入肩,切断了一根主脉。
太医院当年的诊记录全毁了,没人说得清那一箭究竟伤到了什么。她忽然伸手,
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病人。“别走……”她闭着眼,声音发颤,
“像那晚一样……把药给他……”我心头一震。那晚混乱至极。幼帝刚登基,刺客冲入殿门,
我挡在阶前,中箭倒地。有个小宫女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塞了颗药丸在我嘴里,滚烫的,
带着草腥味。她被侍卫拖走时,回头看了我一眼。后来我活了下来,那人却再没出现。
我抽出袖中药膏,抹在她额上,又撕下衣襟一角,浸了冷水敷着。她渐渐安静了些,
但手还是不肯松开。我由她抓着,守到五更。天光微亮时,她醒了。
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笑:“指挥使也会熬夜?”我没答话,只把剩下的药膏递给她。她坐起身,
甩了甩头发,动作利落得不像生过病。看到我袖口的布条还缠在她手心,顿了一下,
慢慢解下来,叠好放进药囊。“你说梦话了。”我看着她。她低头整理针线包,
不动声色:“人都会说梦话。”“提到了‘云容’。”她手停了一瞬,
随即继续收拾:“三钱银子。”“什么?”她从发间抽出一根银针,
放在掌心递过来:“买你别再问。”我没接。她也不勉强,自己收了回去,插回红绳里。
起身拍了拍裙子,走到庙门口,抬头看了看天。“今天得找到药堂。
”“为什么非得是你去治?”“因为没人比我知道这病从哪来。”她回头,“你怕我惹事?
那你大可以现在绑我去官府,就说发现可疑女子私自治疫——不过,等你押我走到城门口,
城里就没活人了。”我站起身,拍掉肩上的草屑。“你要是敢耍花样……”“我就算想逃,
也得先活过今天。”她打断我,“况且,你昨夜没松手。”我没吭声。她笑了笑,
转身走出庙门。风卷起地上的灰土,打在脸上。我跟上去,手按在刀柄上,不是防她,
是防这城里的沉默。她走得很稳,穿过一条窄巷,停在一间塌了半边屋顶的铺子前。
门楣上挂着块朽木,依稀能辨出“济安堂”三个字。她推门进去。屋里黑着,药柜倒了,
抽屉全被拉开。她在角落翻出一本残册,封面烧了一半,剩下《疫症辑要》四个字。
她借着窗缝透进的光翻了几页,忽然停住。“找到了。”我走过去。
她指着一行字:“腐心蛊毒,发于肺腑,形似高热,实为血脉逆行。解法:三七三钱,
薄荷五分,另加一味‘寒星草’——可惜这药,十年没人见过了。”她合上书,
抬头看我:“但现在,有人不想让人知道这是中毒。”“谁?”她没答,只是把书塞进包袱,
转身往外走。刚踏出门槛,她忽然停下。巷子对面,一个孩子靠墙坐着,脸色青紫,
呼吸急促。他母亲跪在一旁,抱着他哭。她看了我一眼。我皱眉:“你想干什么?”“救人。
”她说。“官府禁令写着,治疫者斩。”“那你就拦我。”她往前走。我站在原地。她蹲下,
从药囊里取出银针,捻指施针。孩子咳了一声,吐出一口黑血。她面色不变,继续下针,
指尖微微发抖,却不肯停。我转过身,背对着巷口。耳边传来压抑的抽泣,
还有针尾轻颤的声音。一炷香后,她站起来,脸色发白。“他还活着。”她说。我回头,
看见那孩子呼吸平稳了些,母亲抱着他,不停磕头。她把银针收回红绳,指尖有一道裂口,
渗着血。我走过去,撕下一段衣襟,递给她。她愣了下,接过,自己包上。“你不杀我?
”“现在杀你,”我看着她,“城里就真没人敢动手了。”她笑了下,没说话。
风从巷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灰纸,打着旋儿飞向天空。她转身往前走,脚步没停。
我跟在后面,手仍按在刀柄上。药膏的气味还留在指尖,混着她的血。
4风卷着盐粒打在脸上,像细砂磨皮。我坐在板车角落,手攥着包袱底那半块玉珏,
冰得指尖发麻。楚明远一言不发地赶车,鞭子甩得干脆,
可我知道他也在看我——从离开疫城起,他的目光就再没真正松开过。盐场大门在前头立着,
两根木柱漆成暗红,像是干透的血。守卫拦路,要验“身契玉片”。我低头不语,
只把玉珏递出去。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冷笑一声:“新规,拿玉抵税。一块‘云’字玉,
换三斤粗盐。”我刚要开口,楚明远忽然伸手探入怀中。他动作很慢,
像是在摸什么极珍贵的东西。接着,他取出另一块玉珏——黑底,赤纹,刻着一个“容”字。
他没说话,只是将两块玉拼在一起,裂口严丝合缝。守卫愣了下,眼神变了。我抬头看他。
他也正看着我,喉结动了一下,又迅速移开视线。“哑巴夫妇?”守卫嗤笑,“那正好,
省点口舌。”他伸手想抢玉珏,我早有准备,袖中绣鞋一抖,薄荷粉洒出一线,扑进他鼻孔。
他猛地打了个喷嚏,手一松,楚明远立刻抽回玉珏,扬鞭催马,车轮碾过门槛,冲进了盐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