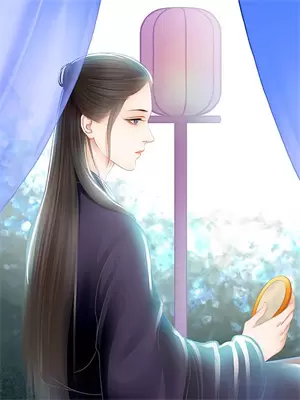死亡灰色头像男生
作者: 桃子快到怀里来悬疑惊悚连载
《死亡灰色头像男生》中有很多细节处的设计都非常的出通过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桃子快到怀里来”的创作能可以将赵三福第七次等人描绘的如此鲜以下是《死亡灰色头像男生》内容介绍:我嚼着泡面翻简历天花板灯管滋啦炸再睁鼻腔灌满腐木指甲缝里全是黑正要骂眼前弹出血红光幕:灰镇代行者第七次轮存活目标:七日“代行者?”我喉咙发身旁老汉直勾勾盯着嘴里嘟囔:“新来的?”他领口别着铜刻着“赵三福”。这名残册第三页出现1阴沉的午天像一块锈死的铁皮盖在头没有太也没有我躺在一座老旧祠堂的供桌底身上盖着件灰布短袖口磨出了毛...
我嚼着泡面翻简历时,天花板灯管滋啦炸开。再睁眼,鼻腔灌满腐木味,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正要骂娘,眼前弹出血红光幕:灰镇代行者第七次轮回,存活目标:七日“代行者?
”我喉咙发紧。身旁老汉直勾勾盯着我,嘴里嘟囔:“新来的?”他领口别着铜牌,
刻着“赵三福”。这名字,残册第三页出现过。1阴沉的午后,
天像一块锈死的铁皮盖在头顶。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我躺在一座老旧祠堂的供桌底下,
身上盖着件灰布短打,袖口磨出了毛边。空气里全是腐木和尘土混在一起的味道,
呛得人喉咙发干。我记得自己是在公司加班,趴在工位上睡着了。再睁眼,就到了这儿。
脑子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任务更新:活过第七日。我没动,也没问是谁在说话。
那声音来得快去得也快,像是从耳朵深处钻出来又立刻消失。我坐起身,手脚有点软,
但还能走。祠堂不大,四根柱子歪斜地撑着屋顶,香炉倒了,灰烬散了一地。
正前方供着几块木牌,字迹模糊,看不清名字。我想出去。刚走到门口,胸口猛地一沉,
像被人按住了心口。呼吸变得费力,眼前发黑。我退后两步,那种压迫感才慢慢散开。
这地方不让出去。我靠墙坐下,摸了摸脖子上的胎记——一片暗红,形状不规则,从小就有。
现在它微微发烫,但我没多想。更让我在意的是,刚才那一瞬间,我好像听见了点什么。
不是声音,是感觉。就像有人在我耳边喘了口气,又迅速抽离。我甩了甩头,
决定先看看外面。第二次尝试,我贴着墙根挪到门边,试探性地伸出手。指尖刚触到门槛,
胸口又是一紧,比上次轻了些。看来不是完全出不去,只是……有限制。趁着还能动,
我冲了出去。外头是条碎石路,两边房子低矮破旧,墙皮剥落,窗户黑洞洞的。
所有路标都指向镇中心的一座老钟楼,锈迹斑斑的指针停在五点四十的位置。街上有人。
一个老汉蹲在路边修鞋,面前摆着个小摊,铜牌上刻着“赵三福”三个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浑浊,却没避开。我走过去,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怎么来的这儿?”他嘴唇动了动,
声音像是被掐住喉咙挤出来的:“别去……”“什么别去?”我追问。
他又说:“不能说……”话没说完,远处传来一声钟响。铛——全镇一下子静了。
走路的人停下,开门的缩回屋,连风吹树叶的声音都没了。赵三福眼神忽然空了一下,
像断了线的木偶,然后猛地站起来,拍拍裤子:“新来的?跟我走。”我没拒绝。
现在能说话的人太少了。他带我往镇中心走,路上递给我一块粗布巾,“新来的人该有的。
”他说。我没接,他也不恼,塞进我怀里就继续走。沿路我发现,没人敢直视我。
偶尔有孩子探头,被大人一把拽回去。整条街安静得反常,连狗都不叫。
“这镇子……有什么规矩?”我试探着问。赵三福脚步顿了一下,“第六日之前,别问太多。
”我说不出话了。喉咙突然发紧,像是被什么东西勒住,
连“穿越”两个字都卡在嗓子里吐不出来。我们走到一块石碑前。碑面刻着四个大字:违者,
削指。笔画深得像是用刀凿出来的,边缘还残留着暗褐色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血。
我伸手想去摸,赵三福猛地拍开我的手,“别碰!”他语气第一次有了情绪,
眼里闪过一丝慌。就在这时,钟声又响了。这次是三下。赵三福脸色变了,催我快走。
我没动,盯着石碑看了几秒,悄悄用袖子里藏的炭笔,在内侧画了个“碑+指+禁”符号。
这是我开始记东西的习惯。从上一次……不对,是从醒来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记忆不太对劲。
有些事明明记得,又像没发生过。赵三福把我送到祠堂门口就走了,一句话没多说。
临走前回头看我一眼,那眼神不像关心,倒像在确认什么。我回到供桌下,蜷着身子坐下。
天快黑了,镇上没人走动。门窗紧闭,仿佛入夜后会有东西出来。我正想着,
忽然听见井边有动静。走出去一看,是个穿红袄的姑娘,蹲在井台边上磨刀。
菜刀卡在木板缝里,她一下一下地推着磨石,动作很稳,嘴角挂着笑,可那笑一点都不热。
她叫陆小满,镇西裁缝家的女儿,我在路过她家铺子时听人提过一句。但现在,
她是第一个敢直视我的人。我走近几步,“这井能打水吗?”她停下动作,抬头看我,
目光落在我脖颈上,停了几秒,才开口:“你还没到该问的时候。”声音很轻,
却让我背脊一凉。我没再问,退后两步,袖中手指迅速画下“井+刀+红衣”。
这三个符号并列排开,和之前的“碑+指+禁”一起,成了我袖口的第一组标记。
转身离开时,我忍不住回头。她还在磨刀,但嘴角的笑没了,眼神冷得像井水。我回到祠堂,
天已经全黑。全镇灯火熄灭,没有一点光。我靠着供桌坐下,脑子乱成一团。
赵三福的话、石碑的警告、陆小满的眼神,还有那句“第六日之前,
别问太多”——所有人都知道些什么,只有我不知道。更奇怪的是,
每次我想提起“系统”或者“穿越”,喉咙就像被堵住。这不是巧合,
是规则在压制我说真话。我闭上眼,身体疲惫,可神经绷着。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
屋檐下的铁铃轻轻响了一下。没有风。我睁开眼,盯着那铃铛看了很久。它没再响。
但我记得,第一次在工位昏睡前,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七分。而现在,
我手腕上的旧表显示,时间停在第六日傍晚五点四十三分。差七秒,六点。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不是第一天来这儿。我可能……已经死过。只是现在,
还不敢去想。存活 1 日2第六日傍晚五点三十七分,我蹲在祠堂主梁上,
炭笔在袖口内侧画下第七道刻线。距离上次时间停摆还有六分钟,胎记又开始发烫,
比前两天更烫,像是有人拿烧红的铁片贴在我脖子上。我盯着手腕上的旧表,指针走得正常,
可我知道它快了。昨天这时候,全镇静得连井水都不翻泡,而今天街上还有人走动,
一个穿灰布衫的老头拖着竹筐从钟楼底下经过,影子被拉得老长。不对劲。我挪了挪身子,
木梁咯吱响了一声。这位置能看清整个祠堂,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
我得抓住那个瞬间——如果真像我想的那样,我已经死过,那刚才听见的喘息、刮擦声,
就不是幻觉。五点四十二分。我屏住呼吸。差七秒到六点时,
耳朵里猛地灌进一段声音:先是急促的喘气,接着是手指甲在木板上抓挠的刺啦声,
像要抠穿什么。然后是一滴水落下的回音,深不见底。最后是个女人的声音,
压得很低:“……血手按住了井盖。
”画面跟着炸开——一只沾满暗红的手掌狠狠拍在井口石沿上,指缝间往下淌着黏稠液体,
井盖边缘渗出黑水。三秒后,一切消失。我从梁上滑下来,腿软得差点跪倒。炭笔掉在地上,
滚到供桌底下。我没去捡。刚才那画面太清楚了,不是梦,也不是错觉。
那是我死前看到的最后一幕。可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靠近过井。第二天一早,
我把赵三福给的粗布巾叠好,揣进怀里,往他摊子走去。他正低头补鞋,
鞋锥在皮面上戳得啪啪响。我站定,故意撩起衣领,露出脖颈上的胎记。“你见过这个吗?
”我问。他手一顿,鞋锥扎进手指,血珠冒出来。他没抽手,也没看伤口,
只死死盯着我的胎记,瞳孔缩成针尖。过了两秒,他猛地甩开鞋锥,
声音发颤:“那是煞气烙印,碰了井里的东西会醒。”“什么东西?”“不该问的别问。
”他抓起抹布裹住手,转身收拾工具,动作僵硬得像关节生锈。我没再说话,
把布巾放在摊边,走了。下午我去了一趟镇西,远远看见陆小满还在井台磨刀。她姿势没变,
左手扶刀背,右手推磨石,一下一下,节奏稳定。我躲在墙角看了半晌,她一次都没抬头。
夜里十一点,我摸到赵三福家后窗。屋里有光,还有说话声。
“不能再让他靠近井……第七次了!”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可他已经听见回响!
”这是赵三福,嗓音干涩,“昨晚他在梁上等着,肯定看到了什么。
”“那就让他死在第六日。只要不破七,规则就不会松。”“可要是他这次活着呢?
”屋里突然安静。接着是桌椅挪动的声音,像是有人站起来。我贴着墙根往后退,
脚踩到一根枯枝,咔地断了。屋门开了。赵三福站在门口,左脸覆着一块焦黑的烧痕,
皮肤皱在一起,像被火燎过的树皮。他眼睛空洞,直勾勾看着我藏身的方向,却没喊人,
也没动。我转身就跑。第三天开始,我的皮肤出了问题。先是右臂外侧变得半透明,
能看见下面青紫色的脉络,像藤蔓一样慢慢往上爬。我用袖子遮住,炭笔划在上面,
痕迹比往常深,像是笔尖陷进了肉里。晚上睡觉,胎记烫得睡不着,
耳边全是井水翻涌的声音,哗——哗——,规律得像心跳。
我开始在袖内画新符号:“皮透+青紫+井声”。可写着写着,发现字迹边缘微微凸起,
仿佛皮肤正在排斥这些记录。第四天傍晚,我去了井台。陆小满还在磨刀。夕阳照在刀面上,
映出我扭曲的脸。我走近一步,想看得更清些。刀光一闪,我愣住了。我裸露的手腕上,
那层半透明的皮肤下,浮现出一个手掌轮廓——五指张开,掌心朝下,
和回响里那只血手一模一样。我猛地后退,撞到身后的矮墙。陆小满停下磨刀的动作,
抬起眼。她嘴角微动,没笑,但眼神变了,像是等到了什么。我转身往祠堂跑,
一路撞翻两个晾衣架,木杆砸在地上发出闷响。回到供桌下,我蜷进角落,从怀里掏出炭笔,
在最后一寸袖布上用力写下:“我不是第一次死。”字写完时,笔尖折断。我盯着断口,
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每次轮回,我都穿着这件灰布短打。衣服会磨毛,会脏,但从不会破。
就像我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变成承载记忆的容器,而容器本身,已经开始裂了。3天刚亮,
我从供桌底下爬出来,右臂的皮已经薄得能看见骨头轮廓。
昨晚写下的那句话还在袖口:“我不是第一次死。”字迹边缘发黑,像是渗进了布里。
我没管它,用炭笔在另一处画了个井台符号,
下面加三道横线——这是第三次轮回时撞开神龛后墙的位置。那天我摔进去,摸到个凹槽,
没来得及细看就被赵三福拉了出来。现在想,那地方或许藏着东西。我撑着膝盖站起来,
肩胛骨那一片皮肤绷得发烫,像要裂开。走两步,胳膊就抽一下,疼得人想咬牙。
可我不敢停。血手印还在我皮下,井水声也没断,一直嗡在耳朵里,低得几乎听不清,
但没停过。我绕到主殿侧墙,跪在地上扒神龛后的砖缝。手指抠进上次松动的那块石板边缘,
用力一推,咔的一声,暗格开了。里面塞着一本册子,纸页泛黄,边角卷曲,
像是被人反复翻过又藏起来。我把它抽出来,封面上几个字被磨花了,
只认得出“灰镇规录”四个残痕。翻开第一页,墨迹斑驳,字不成行。
我眯眼辨认:“……代行者七轮不成,魂归灰烬。胎记者,镇之煞,承怨而生,
引灾而行……”我心跳猛地一顿。胎记者。我下意识摸脖子,那里正发烫。
继续往下看:“……每逢第七日,若煞未熄,则启火祭,焚其身以安镇。”我没喘气,
接着翻。后面是名单,歪歪扭扭写着名字,每个名字下面都有一道划痕,有的两道,
最多五道。翻到最后一页,一行新墨字跳进眼里:“第七代代行者:陈观潮。”名字底下,
六道深痕并列排开,像是有人一遍遍划下去,又没擦干净。我盯着那六个叉,脑子嗡了一声。
不是梦,不是幻觉。我真的死了六次。他们都知道。我赶紧合上册子,往怀里塞。
指尖碰到胸口时,忽然一僵——这衣服,前几次轮回我也穿着。没换过,也没破。
就像我的身体,坏了也不烂,只会越来越不像人。门外传来脚步声。我缩到神龛后,
屏住呼吸。门轴吱呀响了一下,没人进来,但有影子贴在窗纸上晃了两下,走了。
我慢慢起身,把炭笔在袖内写下:“残册现名,六划为证,火祭因胎记。”写完一笔,
手臂突然抽搐,皮下一凸一凸,仿佛有什么在爬。我咬牙忍住,往外走。门槛刚迈过一半,
巷口火光一闪。王麻子带着三个人冲过来,手里举着火把,最前面那人提着铁棍,正是他。
“抓代行者!”他吼得脖子青筋暴起,“外乡人脖带胎记者,按祖训当火祭!
”我转身就往祠堂里退,顺手撞翻香案。供果滚了一地,香炉倒下,灰扑腾腾扬起,
遮住视线。我趁机把残册往内衣里塞紧,贴着墙想绕去侧门。可刚拐过供桌,身后风声一响。
我回头,王麻子整个人扑了过来,铁棍砸空,人却撞我腰上。我摔出去,头磕在地砖上,
眼前炸出一片白光。耳朵嗡鸣中,我听见自己喘气声,还有远处火把烧柴的噼啪。
然后一张脸凑近,是王麻子。他蹲下来,一只手掐住我后颈,把我脑袋往上提了提,
嘴角咧开,露出一口黄牙。“第七次了。”他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别人听见,
“还当自己能改命?”我喉咙里涌上一股腥味,想说话,张不开嘴。他松开手,
转头对其他人说:“绑了,抬去老槐树下。今晚就得点火,不能让他活到第七天。
”有人应了一声,脚步朝我靠近。我躺在地上,视线模糊,但还能动手指。
悄悄把炭笔从袖口滑进掌心,用力掐进肉里。疼,说明还没彻底昏过去。他们把我架起来时,
我瞥见巷口站着一个人。陆小满。她穿那件红袄,站在火光照不到的地方,脸一半亮一半暗。
没说话,也没动,就那么看着。我被拖出门槛,膝盖蹭过石阶,磨出血痕。
祠堂外的老槐树影子横在地上,枝杈像爪子。王麻子一边走一边拍我脸:“醒着就好。
你知道为啥非得烧你吗?因为胎记一烫,井里的东西就要醒了。”我嘴唇动了动,
没力气发声。他笑了一声:“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想逃的?前六个,哪个不是临死才知道规矩?
”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残册上的字:“胎记者,镇之煞”。原来他们早把我当灾星。
可如果真是灾星,为什么偏偏是我?他们把我扔在地上,有人拿麻绳捆手。我蜷着身子,
指尖还在抠炭笔,一点点往袖口挪。王麻子蹲下来,掏出一把小刀,
在我面前晃了晃:“割了胎记也得烧。祖训说了,沾过煞气的皮肉,碰火才灵。
”我猛地睁眼。他咧嘴一笑:“怎么,心疼了?”我没答话,
只是看着他左脸那块疤——和赵三福的一模一样。同一把火燎的?我想开口问,
喉咙却被什么堵住,发不出声。他们把我翻过来,脸朝上。天空灰蒙蒙的,没有云,
也没有光。火把映在瞳孔里,跳动着,像要烧进来。王麻子站起身,
对旁边人说:“准备柴堆。”有人应声去搬干草。我躺在地上,手指终于把炭笔移到掌心。
趁着翻身的空档,借力在石板上划了一道。一道短横。这是我第七次标记。
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能活到第六日傍晚,回响里会不会多一段声音?比如,
王麻子刚才说的那句——“第七次了。”这话不该他知道。可他不但知道,
还说得像数日子一样熟。我盯着火把的光,眼皮越来越沉。有人往我头上泼了点水,
凉了一下,清醒些。王麻子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块黑布,说要蒙头。我最后看了一眼巷口。
陆小满不见了。红袄没了。我被拽起来,拖向槐树。树干上刻着一道道竖线,密密麻麻,
数不清多少条。他们把我按在树下,开始堆柴。我靠在树皮上,手藏在背后,炭笔还攥着。
指节发麻。但我记得。记得每一个名字。记得六道划痕。记得血手拍井的声音。
如果再死一次,我会听得更清楚一点。王麻子举起火把,离柴堆还有半尺。我闭上眼。
4火把离柴堆只剩半尺时,我听见了声音。不是王麻子的吼叫,也不是干草燃烧的噼啪。
是一句话,从耳朵深处钻出来,像锈针扎进脑仁:“胎发烧了,煞气就散了。”女声。
冷得像井水。我没睁眼,但身体猛地一抽。火焰已经舔上裤脚,皮肉焦糊的味道冲进鼻腔,
疼得我整条脊椎都在颤。可就在那一瞬,意识断了。再醒过来,是躺在一堆枯草里。
天没亮透,灰蒙蒙压着地面。我翻身坐起,浑身黏着黑灰,衣服破了几处,但没烧穿。
手撑地时掌心一滑,摸到湿泥和碎木炭。四周空荡,老槐树还在,
树干上的刻痕比之前多了三道,柴堆塌了一半,余烬冒着细烟。我活下来了?我抬手摸脖子。
胎记不烫了,反而凉,皮肤表面扎着几根短硬的黑丝,半寸长,焦炭一样。指甲一掐,
断了一根,指尖沾上灰,轻轻一搓就散。这不是头发。我盯着那点灰,喉咙发紧。
上一次死前,最后听见的是王麻子说“第七次了”。这一次,多了一句陌生的话,女声,
像陆小满,又不像。回响变了。我扯开衣领,把剩下的黑丝一根根拔下来,掌心积了小撮灰。
袖口内侧还藏着炭笔,我翻过手腕,在布上写下:“新回响:胎发烧,煞气散。发声者?女,
音似井边人。”写完,又画了个小圈,圈住“七”字。第六日傍晚快到了。如果回响会叠加,
那今晚……我能听两段?正想着,远处巷口有动静。我缩身藏进槐树后,探头看去。
赵三福的修鞋摊空着,工具箱翻在地上,锥子、线团撒了一地。竹凳倒了,
一只鞋底卡在缝隙里,像是他走得太急,连活都没收完。我慢慢靠近,蹲下翻工具箱。
底部有烧过的纸片,只剩半块,边缘焦黑卷曲。我拨开灰,看清一行残字:“……七次必焚,
不可逆”。手指一抖。他们知道第七次。赵三福知道,王麻子也知道。可一个跑了,
一个却亲自点火。我抓起纸片塞进怀里,刚要起身,巷子另一头传来脚步声。三人,
踩着碎石走来。我闪身贴墙,从砖缝往外看。王麻子走在最前,左脸麻子红得发亮,
手里铁棍拖地,身后两人各拿木棒。他眼睛直勾勾盯着槐树方向,嘴角绷着,
不像上一次那样得意。“搜。”他低声说,“他还在这镇上。烧不死,就得绑死。
”我屏住呼吸,慢慢退向祠堂方向。右臂旧伤还在抽,每走一步都像有东西在皮下爬。
路过井台时,红袄一闪,从对岸掠过,停都没停。陆小满。她看见我了,但没出声。
我拐进祠堂侧门,供桌还在原位,香炉倒着,灰没清。我弯腰捡起来,炉底还有余温,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