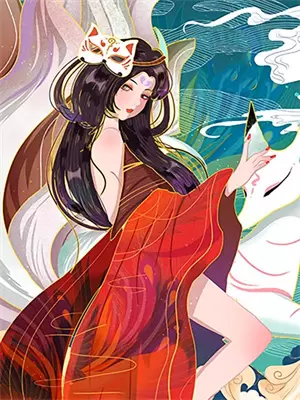1 导语苏婉逐渐听不见了,起初是风声,然后是人声,最后是自己的心跳。
她试着去习惯世界的沉默,却没想到,那些她以为再也听不到的声音,有人在偷偷保存。
七年前,她被那个男人一句“我们不合适”推开。七年后,他成了她的主治医生。
她听不清他说什么,只能看见他嘴巴一张一合,一次次错过可能是“我还爱你”的瞬间。
当她以为一切都来不及了,他却在她最害怕那天,对她说: ——“如果你听不见了,
我就陪你沉默。”她不知道的是,那些她说出口的声音,
他一个都没有错过; 她以为自己在独白,其实他一直在听。
这不是一个关于听力消失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如何被爱听见”的故事。
2 第一章 听力报告单上的红字医院的走廊一如既往地白,像一封尚未落笔的信纸,
安静而空旷。苏婉坐在检查室外的长椅上,手里捏着那张刚刚打印出来的报告单,
纸边已经被她指甲压出了折痕。“渐进性神经性耳聋。”她低头盯着那行字,
像盯着某种判决书。医生刚才在诊室里说了很多专业术语,她只听清了这句。
“这是罕见的耳蜗神经性疾病,属于进行性不可逆类型。”医生语气尽量温和,
“建议尽早开始干预,
比如助听设备的适配、药物调节和日常环境调整……”苏婉像个刚从考场出来的学生,
只会点头。她的脑子并没有处理信息,只是机械地回应。她今年三十岁,单身,未婚未育,
社交圈狭小,工作压力大。她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品牌总监,外界看来是职场精英,
穿着高定西装,踩着恨天高,精致且干练。可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整夜失眠,靠咖啡续命,耳鸣已经持续了快半年,
只是被她一再忽视。直到最近的两次会议,她突然没听清对方的发言,还误解了客户的反馈,
被老板点名批评。她才慌了。于是请了年假,做了一次彻底的体检。
她本以为不过是压力太大,调理一下就好。她甚至打算周末报个瑜伽班,去趟按摩理疗。
她没有想到,是“耳聋”。而且,是会逐步消失听觉、失去世界声音的那种耳聋。
她的耳边开始嗡嗡作响,不知道是病灶还是情绪。医生把手搭在她的病历本上,
说:“苏小姐,我们建议您尽快联系家属,有些治疗环节需要家属配合签署。
”“我没有家属。”苏婉脱口而出。医生顿了下,点点头:“那……朋友也行,紧急联系人。
”她摇摇头,声音淡得几乎听不见:“我自己就可以。”离开诊室时,
走廊的灯比她记忆中还要刺眼。她看见一对母女坐在对面的长椅上,
母亲正低声安慰孩子:“只是中耳炎,别怕。”那个孩子抽泣着,却还是点头说“我不怕”。
她的喉咙发紧,突然羡慕起那个孩子。她快步走进洗手间,把水龙头拧到最大,
冰冷的水流冲刷着她的手背。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妆容完整,气场尚在,
甚至连睫毛膏都没有晕染。可眼神是空的,像一张随时会塌的面具。她抬手摘掉耳环,
把那张报告单折成四折,塞进包里。出了医院,她径直走进旁边的咖啡馆点了一杯美式。
她不需要糖,不需要奶,只需要一点苦味提醒她:你还清醒着,你必须清醒着。
她靠在靠窗的位置,窗外车来人往。人声、汽笛、小贩吆喝,一切仿佛如常。她突然意识到,
这些声音,有一天,她可能再也听不到了。她把手机掏出来,打开录音键,
录下了第一条声音日志。她对着手机说:“2025年6月12日,今天的风很大,
像有人在耳边低语。医生说,我要开始准备和声音告别了。
”3 第二章 主治医生是他苏婉站在电梯前,手里捏着预约单。“耳鼻喉科,专家号,
2号诊室。”她特意提早了半小时,打算看完就走,
不打招呼、不社交、不留一丝多余的情绪。她不想被谁看穿自己这一身伪装,
也不想在医院的灯光下,暴露出半点脆弱。排队时,她习惯性刷着手机,
直到叫号器响起:“苏婉,2号诊室。”她起身,走进诊室,一推门就看见了那个人。
她的步伐顿了一下。诊室内,男人穿着白大褂,正在低头翻看病历。他的头发稍长,
发尾微卷,一副金边眼镜稳稳挂在鼻梁上。他听见门响,抬头,看了她一眼,眉头动了动。
“你是……苏婉?”他先开口。苏婉几乎是脱口而出:“周砚?”空气在那一秒变得稀薄。
时间像回旋的针头,把她带回了七年前。那时她还是个大四学生,在医学院旁听神经解剖课。
他是校外返聘的研究员,也是那年最受女学生追捧的青年讲师。她暗恋了他整整一个学期,
写了三封信,全都没敢交出去。毕业那年,他们在校医院门口擦肩而过,
她鼓起勇气对他说:“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很好的医生。”他点头,笑着说:“谢谢。
”然后转身离开。那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七年之后,在她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他却以主治医生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她面前。“今天的听力评估和干预建议由我来负责。
”周砚的语气稳重而公事公办,像每一个职业医生一样。苏婉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坐到听力设备前。检测开始。“请你戴上耳机,听到声音请按下按钮。”她照做。
耳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音调,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她认真聆听,却发现有些频率,
她根本听不见。她的手指停顿,按钮迟迟没有按下。设备外,周砚眉头皱起。
他一边记录数据,一边观察她的反应。“苏婉。”他忽然开口。她抬头,
眼神清澈却有些空洞。“别紧张,我们只是初步评估,还需要后续检查。”“你不用安慰我。
”她轻声说。“我不是安慰你。”他顿了下,“我是希望你别一个人扛。
”苏婉忽然笑了:“那你打算怎么帮我?写个病情说明?开点药?还是说几句‘你要坚强’?
”周砚没有回答。她站起来,把耳机放回原位,语气恢复平静:“谢谢你,医生。
接下来我可以自行安排。”他张了张嘴,却终究没有再说什么。她的背影离开诊室,
落在白色的灯光下,安静得像从未来过。门轻轻合上,他低头看着病历上她的名字,许久,
叹了口气。4 第三章 你能别装作不认识我吗苏婉走出诊室,脚步没那么快,
她在医院长廊的尽头停了下来。那里有一扇开着的窗,窗外是城市高架的尽头,
车流川行不息,远处的天像一块褪色的布。她站在那里,像是想把情绪吹散在风里。
可风并不听话,它只是卷起她的发丝,吹进她的耳朵,却什么也没有带走。
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很快,很响。也许是耳蜗又出了问题,也许,是气恼。
“你是不是……在生气?”周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比刚才在诊室里低了几分,
像是刻意压低了音量。“你出来干嘛,不要你假惺惺。”她背对着他说,语气很平静。
“我不是假惺惺。”他站在她身后两步远,“我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见到你。
”“你当然没想到。”她转过身来,终于正视他,“你一向很会抽身。”他愣了愣,
“你还记得那年的事?”“我当然记得。”她抬起眼,目光直直地撞上他,
“你以为你消失了七年,我就会忘了吗?”他沉默。“你在我最喜欢你的时候,
对我说你‘不适合谈感情’。”她语调轻快,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现在倒好,我病了,
你是我的主治医生。”“我不是不记得。”他终于低声说,“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距离太远。”“你怕我打扰你。”她接过话,“怕我太投入,
怕我妨碍你未来的医生之路。”“苏婉。”他唤她的名字。她笑了一下,
眼尾有些湿意:“别叫我名字,你这样叫的时候,我会以为你还在意。
”“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吗?”她退后半步,
“因为你从我走进诊室的第一秒起,就在装不认识我。”他喉结滚动一下,
低声说:“我不确定你想不想被提起过去。”“我想不想,是我的事。”风又起了,
吹乱了她的发,吹得她眼角的泪有些发烫。她吸了吸鼻子,
像在努力重新穿好一件披散的外衣。“你是医生,我是病人。我们会有很多次见面,
但别再试图走近我。”她顿了顿,补了一句,“你迟到了七年。”说完,
她转身往楼梯方向走。那背影瘦却挺,像一把紧握的伞骨,被撑在风里,不容折断。
周砚没有追上去,只是看着她离开的方向,半晌才轻声说了一句:“可我没有忘。
”5 第四章 那些听不清的对白苏婉发现,听不清别人说话,比完全听不见更难受。
就像站在雨里看着远处灯光模糊地晃动,你不确定那是不是家的方向,只能靠感觉去猜。
她已经辞掉了工作。老板没有挽留,只说了一句“你好好休息”,
然后很快在群里安排了替代她的新人。她收拾东西的时候格外安静,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有人试图打招呼,但她没听清,对方也就没再重复。她明白,这种不主动沟通的沉默,
会让她越来越像个“局外人”。她搬出了公司配的单身公寓,住进一间老城区的出租屋。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墙壁有些旧,但阳光很好。她喜欢靠窗的位置,喜欢在午后坐在那里,
闭着眼听楼下炸油条的声音、小贩吆喝的声音,还有偶尔经过的猫叫。
她害怕某天这些声音会从她的世界里彻底消失,所以她买了一个便携录音笔,
开始记录每一天的声音。录音第一天,她记录下了雨滴打在阳台护栏的声音,像轻轻敲鼓。
第二天,是锅里水烧开的咕噜声,还有米饭焖熟后“啪”的一声跳闸。第三天,
她录下了路人打电话的片段,有人说:“我明天就回家了。”她不知道那人是谁,
也不知道他要去哪,但那句话莫名戳中了她。她也想回家。可她没有“家”这个地方了。
她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在她初中时离家再未联系,
之后她一路靠奖学金、实习和自己咬牙坚持活下来。“家”对她而言,从来不是避风港,
而是一道反复疼痛的旧伤口。她开始失眠,偶尔也会做梦,梦见自己在水下,
四周都是模糊的声音,她拼命想听清,却只剩下心跳声。她越来越怕人声。有一次去超市,
收银员问她:“您要不要积分卡?”她没听清,说了句“嗯”。结果对方以为她同意了,
给她办了一张卡。她本想解释,但队伍很长,后面的人催促,
她只能咽下那句“其实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回家后她在本子上写下一句话:“失聪,
不是安静的世界,是不断误解世界。”某天晚上,她在听录音的时候,无意中点开了通讯录。
她的指尖划过一个名字:周砚。她没存备注,只是一个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