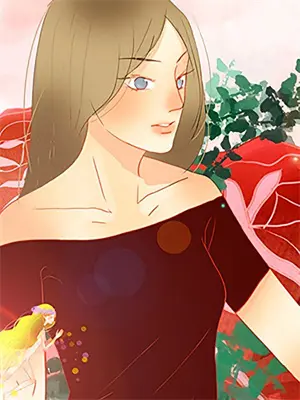
苏晚第一次见到沈砚辞,是在民国二十六年的上海,一场被硝烟味冲淡了奢靡的慈善晚宴上。
彼时她刚从法国回来,身上还带着蒙马特高地的油画气息,穿着月白色的旗袍,
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珍珠胸针——那是母亲留给她的遗物。
宴会厅里水晶灯的光芒晃得人眼晕,
留声机里播放的《夜来香》被窗外偶尔响起的防空警报切割得支离破碎,
她攥着玻璃杯的手指微微泛白,只想快点结束这场压抑的应酬。“苏小姐?
”清冽的男声在身后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苏晚转过身,
撞进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眸里。男人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袖口露出一块精致的怀表链,
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却又偏偏生了一张极为英俊的脸,眉骨锋利,下颌线紧绷,
像是用寒玉雕刻而成。他是沈砚辞,上海滩无人不知的沈老板。传闻他手眼通天,
既做着正当的进出口生意,又与黑白两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闻他心狠手辣,
曾经为了一桩生意,让对手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更有传闻说,他身边从没有过固定的女伴,
对谁都是疏离淡漠。苏晚礼貌地颔首:“沈先生。”沈砚辞的目光落在她领口的珍珠胸针上,
停留了两秒,语气听不出情绪:“苏小姐刚回国?”“是,上周刚到。
”苏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她能感觉到男人的视线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
让她很不自在。“听说苏小姐在巴黎学的是油画?”沈砚辞又问,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酒杯的边缘。“嗯。”苏晚有些疑惑,
她不明白沈砚辞为什么会突然对自己感兴趣。他们之间,本该是毫无交集的两个人。
那晚的对话并没有持续太久,沈砚辞接到一个电话后便匆匆离开,
临走前只留下一句“苏小姐的画,有空想见识一下”。苏晚以为这只是一句客套话,
并未放在心上。可她没想到,三天后,沈砚辞的司机便出现在了她家的门口,
递上了一张请柬——沈砚辞要举办一场私人画展,邀请她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苏晚犹豫了。
她知道沈砚辞这样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对一个刚回国的女学生示好,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她不知道的缘由。可父亲最近在生意上遇到了麻烦,急需一笔资金周转,
而沈砚辞恰好是能帮上忙的人。母亲的医药费也还没有着落,
她没有理由拒绝这个可能带来转机的机会。画展当天,苏晚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旗袍,
带着自己的一幅作品《雾中巴黎》来到了沈砚辞的别墅。别墅坐落在法租界的一处僻静角落,
庭院里种满了梧桐,落叶铺了一地,透着一股萧瑟的美感。画展设在别墅的地下室,
里面挂着的大多是国外的名家作品,只有她的那幅画被单独挂在一个显眼的位置,
旁边放着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写着“特邀嘉宾苏晚作品”。沈砚辞早已在那里等候,
看到她来,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容:“苏小姐来了。”“沈先生。”苏晚点头,
目光扫过那些画作,心里不禁有些感慨,沈砚辞的收藏,果然名不虚传。
“苏小姐的这幅《雾中巴黎》,画得很好。”沈砚辞走到她的画前,语气里带着一丝赞赏,
“雾的朦胧感,还有巴黎街头的那种慵懒,都被你捕捉到了。”苏晚有些意外,
她没想到沈砚辞竟然真的懂画。“沈先生过奖了。”“不是过奖,是实话。”沈砚辞转过身,
看着她,“苏小姐,我有一个提议。”“沈先生请说。”“我想请你做我的私人画家,
帮我画一些东西。”沈砚辞的目光认真,“薪水方面,你可以随便提,另外,
我还可以帮你解决你父亲生意上的麻烦,以及你母亲的医药费。”苏晚的心猛地一跳。
沈砚辞竟然调查了她的情况,这让她有些不安,可他提出的条件,又让她无法拒绝。
父亲的生意,母亲的病,就像两座大山压在她的身上,她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苏晚咬了咬唇,“我需要考虑一下。”“可以。”沈砚辞没有逼她,
“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我的司机还会来这里等你的答复。”那三天,苏晚过得寝食难安。
她问父亲,要不要接受沈砚辞的提议,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晚晚,
你自己做决定吧,无论你选什么,爸爸都支持你。”母亲躺在病床上,意识模糊,
只是紧紧地抓着她的手,嘴里喃喃地说着“别委屈自己”。最终,苏晚还是答应了沈砚辞。
当她告诉司机自己的决定时,司机只是面无表情地说:“沈先生吩咐了,明天早上八点,
我来接你去沈先生的别墅。”第二天,苏晚准时来到了沈砚辞的别墅。
沈砚辞交给她一间宽敞的画室,里面各种画具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她在巴黎时最喜欢用的那几个牌子的颜料。“你的任务很简单,
”沈砚辞站在画室的窗边,背对着她,“帮我画一幅肖像画,还有,
记录下我指定的一些场景。”“肖像画?”苏晚有些疑惑,“是画沈先生您吗?”“是。
”沈砚辞转过身,“不过不是现在,等我通知你。在这之前,你可以先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或者画一些你想画的东西。”接下来的日子,苏晚便在沈砚辞的别墅里住了下来。
她很少见到沈砚辞,大多数时候,他都在书房里处理事务,或者外出应酬。
只有偶尔在晚餐时,他们才能见上一面,简单地聊上几句。沈砚辞对她很客气,
甚至可以说是周到。他会让人按照她的口味准备饭菜,会在她画画累了的时候,
让佣人送上一杯热牛奶,会在她提到想念巴黎的甜点时,
第二天就让人从法租界的西餐厅买来。可这种客气,却像一层无形的屏障,
将两人隔在两个世界,让苏晚始终觉得很不自在。她开始画那幅肖像画,
凭着记忆勾勒沈砚辞的轮廓。他的眉眼,他的鼻梁,他说话时的神情,
都一点点地出现在画布上。画着画着,苏晚发现自己竟然有些着迷于沈砚辞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似乎藏着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悲伤,让她忍不住想要探究。这天晚上,
苏晚画到很晚,走出画室时,发现客厅里还亮着灯。沈砚辞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眼神落寞地看着窗外。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身上,
给他镀上了一层清冷的光晕。苏晚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沈先生,这么晚了,
还没休息?”沈砚辞转过头,看到她,眼中的落寞瞬间消失,
又恢复了平日里的淡漠:“还没。你怎么也还没睡?”“画得有点晚了。
”苏晚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沈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沈砚辞沉默了片刻,
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语气平淡:“没有。只是有点累。”苏晚没有再追问,
她知道沈砚辞不想说,她问再多也没用。客厅里陷入了沉默,
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在空气中回荡。过了一会儿,沈砚辞突然开口:“苏小姐,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苏晚愣住了,她没想到沈砚辞会问这个问题。她想了想,
摇了摇头:“没有。”“是吗?”沈砚辞的目光有些飘忽,“爱过一个人,是很痛苦的事情。
”苏晚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她想问他,是不是曾经爱过一个人,
那个人现在在哪里,可她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她知道,自己和沈砚辞之间,
不该有太多的牵扯。那天之后,苏晚发现沈砚辞对她的态度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待在书房里,偶尔会来画室看她画画,甚至会站在她的身边,
静静地看上好一会儿。“这里的光影处理得不错。”沈砚辞指着她画的一幅风景,
语气里带着赞赏。“谢谢沈先生。”苏晚的脸颊微微发烫,
她能感觉到沈砚辞的气息落在她的颈间,让她有些心慌意乱。“你好像很怕我?
”沈砚辞突然问。苏晚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对上他的目光:“没有,
只是觉得沈先生您……很有距离感。”沈砚辞的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容:“距离感?
或许吧。”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其实,我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苏晚没有说话,只是重新低下头,继续画画。她不知道沈砚辞说的是不是真的,她只知道,
自己对这个男人,似乎产生了一种不该有的情愫。这种情愫,让她感到恐慌,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不会有好的结果。民国二十六年的冬天,
来得比往年早了一些。上海下起了小雪,细密的雪花飘落在梧桐树上,
给光秃秃的树枝裹上了一层白色的绒衣。苏晚站在画室的窗边,看着窗外的雪景,
手里拿着一支画笔,却久久没有落下。她已经在沈砚辞的别墅里住了三个月了。这三个月里,
她和沈砚辞的关系,似乎变得微妙起来。他们不再仅仅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更像是朋友,
偶尔会一起在庭院里散步,一起在书房里看书,一起在晚餐时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沈砚辞很少再提让她画肖像画的事情,也没有让她记录什么场景。苏晚问过他一次,
他只是说:“不急,等我想好了再说。”苏晚知道,沈砚辞是在给她时间,
让她适应这里的生活。她很感激他,可心里的那份情愫,却也在不知不觉中疯长。
她会在看到沈砚辞笑的时候,心跳加速;会在他生病的时候,
担心得坐立不安;会在他外出应酬晚归的时候,忍不住在客厅里等他回来。
她知道自己不该这样,沈砚辞这样的人,身边从不缺女人,她不过是他众多棋子中的一个,
可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这天晚上,沈砚辞回来得很晚,身上带着一身的酒气和寒气。
他走进客厅时,看到苏晚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却没有看,
眼神直直地盯着门口的方向。“怎么还没睡?”沈砚辞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酒后的慵懒。
苏晚猛地回过神,站起身:“沈先生,您回来了。我……我等您回来给您煮醒酒汤。
”沈砚辞看着她,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苏晚很快就端着一碗醒酒汤走了过来,递到沈砚辞的面前:“沈先生,
您快喝了吧,暖暖身子。”沈砚辞接过碗,小口地喝着。醒酒汤熬得很浓稠,
带着一股淡淡的姜香,喝下去之后,胃里顿时暖和了不少。“谢谢你,晚晚。
”沈砚辞突然开口,第一次叫了她的名字,而不是“苏小姐”。苏晚的脸颊瞬间红了,
她低下头,小声地说:“不用谢,沈先生。”沈砚辞喝完醒酒汤,将碗放在茶几上,
然后看着苏晚,眼神认真:“晚晚,你是不是……喜欢我?”苏晚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她抬起头,撞进沈砚辞深邃的眼眸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否认,
可心里的悸动却骗不了人;她想承认,可又害怕被拒绝,害怕失去现在的一切。
“我……”苏晚的声音有些颤抖,“沈先生,您……您别开玩笑了。”沈砚辞没有笑,
他站起身,一步步走到苏晚的面前,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他的手指很凉,
却让苏晚的脸颊变得滚烫。“我没有开玩笑。”沈砚辞的声音低沉而温柔,“晚晚,
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思,其实……我对你,也一样。”苏晚的眼睛瞬间睁大了,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沈砚辞竟然也喜欢她?这怎么可能?“沈先生,
您……”苏晚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有惊喜,有激动,还有一丝不确定。“别哭。
”沈砚辞用拇指擦去她脸上的泪水,语气心疼,“晚晚,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身上有太多的秘密,太多的责任,可能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可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
照顾你。”苏晚扑进沈砚辞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放声大哭。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慌,
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她知道,自己赌对了,沈砚辞是真的喜欢她。从那天起,
苏晚和沈砚辞的关系便确定了下来。沈砚辞不再对她隐瞒什么,他会告诉她自己的生意,
会和她商量一些事情,甚至会带她去见一些他的朋友。苏晚也更加用心地照顾沈砚辞的生活。
她会亲手给他做早餐,会在他加班的时候给他送夜宵,会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陪着他在庭院里散步,听他诉说心里的烦恼。他们的日子过得很甜蜜,
仿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降临在了他们的身上。苏晚甚至开始幻想,等战争结束了,
他们就离开上海,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可她不知道,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悄地向他们逼近。民国二十七年春天,
上海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法租界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
沈砚辞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变得越来越忙,经常几天几夜不回家。苏晚很担心他,
可每次问起,沈砚辞都只是说:“没事,一点小麻烦,很快就能解决。”这天,
苏晚在画室里画画,突然听到书房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她忍不住走过去,贴在书房的门上,
想要听听里面在说什么。“沈砚辞,你疯了吗?你竟然想和日本人合作?
”一个愤怒的声音响起,是沈砚辞的得力助手,陈默。“我没有和日本人合作。
”沈砚辞的声音冷静,“我只是和他们做一笔生意,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生意?
”陈默的声音更加愤怒,“你知道那些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吗?是用来屠杀我们中国人的!
沈砚辞,你不能这么做,你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我知道。
”沈砚辞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可我没有选择。如果不拿到那些东西,
我们的人就会有更多的伤亡。陈默,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不管那么多,
总之你不能和日本人做生意!”陈默的语气坚定。“够了!”沈砚辞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了。”随后,书房的门被猛地打开,
陈默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看到站在门口的苏晚,愣了一下,然后狠狠地瞪了沈砚辞一眼,
转身离开了。苏晚走进书房,看到沈砚辞正靠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眼神疲惫。
她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握住他的手:“沈先生,你没事吧?”沈砚辞抬起头,看到她,
勉强笑了笑:“没事。”“刚才陈先生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苏晚的语气有些担忧,
“你真的要和日本人做生意吗?”沈砚辞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是。”“为什么?
”苏晚不解,“你明明知道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做生意?”“晚晚,
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沈砚辞看着她,眼神复杂,“但我向你保证,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活下去。”苏晚看着沈砚辞的眼睛,她知道他没有骗她,
可她还是很担心。她害怕沈砚辞会出事,害怕他们的幸福会毁在这场战争里。“沈先生,
”苏晚咬了咬唇,“我相信你,可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不能没有你。
”沈砚辞紧紧地抱住她,声音沙哑:“我会的,晚晚,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也会保护好你。
”接下来的日子,沈砚辞变得更加忙碌。他经常和日本人见面,每次回来,
身上都会带着一股压抑的气息。苏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默默地照顾他的生活,给他温暖和安慰。这天,沈砚辞回来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盒子。他走到苏晚的面前,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精致的钻戒,
钻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晚晚,”沈砚辞单膝跪地,眼神认真,“嫁给我吧。
”苏晚愣住了,眼泪瞬间流了下来。她看着单膝跪地的沈砚辞,
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的真诚与珍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沈砚辞见她不说话,握着戒指的手微微收紧,语气里多了几分忐忑:“晚晚,
我知道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战火纷飞,我给不了你一场盛大的婚礼,
甚至可能连安稳的日子都难以保证。可我想让你知道,我想和你过一辈子,
想让你成为我的妻子,名正言顺地护着你。”他的话像温水,一点点漫过苏晚的心尖。
她伸出手,任由沈砚辞将那枚钻戒套在她的无名指上——尺寸刚刚好,
显然是他早就精心算好的。冰凉的钻石贴着皮肤,却让她觉得浑身都暖烘烘的。“我愿意。
”苏晚的声音带着哭腔,却无比坚定,“沈砚辞,我愿意嫁给你。”沈砚辞猛地站起身,
将她紧紧拥入怀中,力道大得像是要将她揉进自己的骨血里。窗外的雪还在下,
可客厅里的空气却滚烫得惊人,连挂钟的滴答声都像是在为他们庆贺。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这场仓促的“求婚”,也没有举办婚礼。
沈砚辞只是找来了一位相熟的牧师,在别墅的小教堂里,举行了一场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仪式。
苏晚穿着自己最爱的月白色旗袍,沈砚辞依旧是那身笔挺的黑色西装,没有宾客,没有祝福,
可当牧师问出“是否愿意无论贫穷富贵、疾病健康,都彼此相守”时,
他们的回答却掷地有声。婚后的日子,像是偷来的蜜糖。沈砚辞只要在家,
便会寸步不离地跟着苏晚——她在画室画画,他就坐在旁边看文件;她在厨房煲汤,
他就从身后环住她的腰,下巴抵在她的发顶;晚上睡觉前,他会给她读诗,声音清冽,
带着催眠般的魔力。苏晚渐渐忘了沈砚辞“沈老板”的身份,忘了他与日本人的周旋,
忘了上海街头的硝烟。她以为这样的幸福能一直延续下去,直到那天,她在沈砚辞的书房里,
发现了那个上锁的抽屉。那天沈砚辞去见日本商会会长,走得匆忙,将怀表落在了书房。
苏晚去送怀表时,无意间撞到了书桌的抽屉,抽屉竟虚掩着一条缝。她本不想窥探,
可里面露出的一张照片,却让她挪不开眼。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
眉眼间竟与她有七分相似,尤其是那双眼睛,清澈又带着几分倔强,
和她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几乎一模一样。女人的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眉眼青涩,
却能看出是年轻时的沈砚辞。两人依偎在梧桐树下,笑容灿烂得晃眼。
苏晚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她颤抖着伸出手,
将照片拿了出来,背面写着一行小字:“予清漪,民国二十年秋。”清漪?
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扎进了苏晚的心里。她突然想起,沈砚辞第一次见她时,
盯着她领口珍珠胸针的眼神;想起他看她画画时,
偶尔流露出的恍惚;想起他叫她“晚晚”时,语气里那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原来,
这些都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另一个人。她像丢了魂一样,将照片放回抽屉,
失魂落魄地回到了画室。画布上,她正在画的沈砚辞肖像,此刻看来竟无比讽刺。
她以为的独一无二,不过是一场替身的闹剧。沈砚辞回来时,
看到的就是苏晚坐在画室的地板上,怀里抱着那幅未完成的肖像,眼睛红肿得像核桃。
他心里一紧,快步走过去,蹲下身:“晚晚,怎么了?”苏晚抬起头,看着他,
声音沙哑得厉害:“沈砚辞,清漪是谁?”沈砚辞的身体瞬间僵住,
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沉默了很久,久到苏晚以为他不会回答,
才缓缓开口:“她是……我以前的爱人。”“以前的爱人?”苏晚笑了,眼泪却流得更凶,
“所以,你接近我,让我做你的私人画家,甚至娶我,都是因为我长得像她,对不对?
”“不是的,晚晚,你听我解释。”沈砚辞想要握住她的手,却被苏晚猛地躲开。
“你不用解释!”苏晚站起身,后退了几步,指着自己的脸,“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你每次看我,是不是都在想她?你给我买的旗袍,喜欢的甜点,是不是都是她以前喜欢的?
沈砚辞,我到底是谁?是苏晚,还是林清漪的替身?”她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
扎在沈砚辞的心上。他无法否认,最初注意到苏晚,确实是因为她与清漪相似的眉眼。
可后来的心动,想要娶她的决心,都是因为苏晚这个人,而不是任何人的替身。“晚晚,
最初我承认,我是因为你像她才注意到你。”沈砚辞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可后来,
我对你的感情,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我娶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是因为我想和你过一辈子,
不是因为任何人的影子。”“我不信!”苏晚摇着头,眼泪模糊了视线,“如果不是因为她,
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的存在?为什么把她的照片藏得那么深?沈砚辞,
你根本就是在骗我!”她抓起桌上的画笔,狠狠摔在地上,颜料溅了一地,
像极了他们此刻破碎的关系。苏晚转身跑出画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将门反锁。
无论沈砚辞在门外怎么敲门、怎么解释,她都没有再开过一次门。那一夜,苏晚坐在床边,
看着无名指上的钻戒,哭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她将钻戒摘了下来,放在了床头柜上。
她想离开这里,离开沈砚辞,可她又舍不得——那些甜蜜的时光,那些温柔的瞬间,
难道都是假的吗?她不甘心。沈砚辞在门外守了一夜,天亮后,他没有再敲门,
只是让佣人给苏晚送了早餐。苏晚没有吃,一直坐在床上,直到中午,她听到了敲门声,
不是沈砚辞,而是一个陌生的女声。“苏小姐,我是沈先生的助理,陈默。
”门外传来一个干练的女声,“沈先生今天要去和日本人谈一笔很重要的生意,
走之前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等他回来,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包括清漪的事情。
他还说,他不会让你受委屈,更不会让你离开他。”苏晚没有说话,门外的陈默停顿了一下,
又说:“苏小姐,其实沈先生对您的心意,我们都看在眼里。
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么上心过,就连对清漪小姐,也没有像对您这样,事事都想着您。
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陈默走后,苏晚坐在床边,心里乱得像一团麻。
她不知道自己该相信谁,该怎么办。直到傍晚,她听到了别墅里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还有佣人的哭声。她心里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快步走出房间,抓住一个佣人,
急切地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佣人哭着说:“苏小姐,不好了!
沈先生……沈先生和日本人谈生意的时候,遇到了袭击,现在还在医院抢救,生死未卜!
”苏晚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她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差点摔倒。
她猛地想起沈砚辞早上离开时的样子,想起他在门外的解释,想起他说会回来给她一个交代。
她怎么能让他出事?怎么能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还在和他赌气?她疯了一样冲出别墅,
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医院。一路上,她不停地祈祷,祈祷沈砚辞没事,祈祷他能平安回来。
她甚至在心里发誓,如果沈砚辞能平安无事,她愿意原谅他,愿意听他解释一切。到了医院,
苏晚看到陈默站在抢救室门口,脸色苍白。她快步走过去,抓住陈默的胳膊:“陈默,
沈砚辞怎么样了?他没事吧?”陈默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摇了摇头:“还在抢救,医生说……情况不太好,子弹打在了胸口,离心脏很近。
”苏晚的腿一软,差点摔倒,陈默连忙扶住她。她靠在墙上,看着抢救室门上的红灯,
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她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沈砚辞的名字,一遍遍地说:“沈砚辞,
你不能有事,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给我解释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抢救室的灯亮了整整三个小时。当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说“手术很成功,
病人暂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观察”时,苏晚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她腿一软,
坐在了地上,眼泪却笑着流了下来。沈砚辞被推进了病房,苏晚一直守在他的床边。
他还在昏迷中,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干裂。苏晚坐在床边,轻轻握住他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