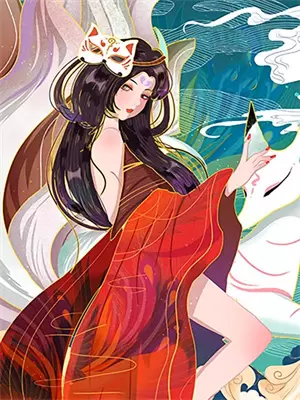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青史遗案薄》第一章 金舌沈砚之把那片青玉残片按在掌心时,
樟木箱的霉味突然混进了一丝龙涎香。
这气味他太熟悉了——祖父临终前攥着的那半块玉佩上,就缠着同样的香气。
那年他才十二岁,祖父躺在病榻上,枯瘦的手指死死扣着他的手腕,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有话被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最后祖父松开手时,
那半块玉佩掉在床板上,龙涎香混着药味漫开来,沈砚之至今记得,
玉佩背面刻着个极小的"卫"字,是锦衣卫的印记。此刻薄子第一页关于周明远的记载,
正被烛火映得发烫。"误食毒菌"四个字写得笔走龙蛇,墨色深浅不一,
显然是史官仓促下笔,可那行朱笔"舌有金痕"却刻得极深,纸背都透出了毛边,
像是写字的人蘸着血在刻。沈砚之翻出《明史·周明远传》,通篇只说"天启三年卒于官,
赠礼部尚书",对死因讳莫如深。
话:"金舌...金舌是被人灌了熔金...藏着妖书..."掌院学士送来的那半片青玉,
莲心处的烛龙符号在灯下泛着冷光。沈砚之将两片残玉拼在一起,
完整的缠枝莲突然渗出细密的水珠,像在出汗。他把残玉凑到烛火前,水珠遇热竟化作白烟,
袅袅升起时,在墙上投出个扭曲的影子,像条蛇正啃噬着什么。他用指尖蘸了点水珠,
放在舌尖——先是极淡的甘,随即涌上一股尖锐的苦,混着杏仁的腥气,是砒霜特有的味道。
"沈编修还在忙?"史馆的老杂役老刘提着灯笼走过,
灯笼的光晕在满墙的历任史官名录上晃,周明远的名字被虫蛀得只剩个"周"字,
旁边的空位本该是继任者的名字,却空了整整三年,直到崇祯初年才补上。
"这屋子邪性得很,天启年间失过火,偏就这角落的旧档烧不毁,老人们都说,
是有冤魂守着哩。"老刘的灯笼照在墙角的立柱上,那里有道焦黑的裂痕,
像被人用指甲抠过。沈砚之追问火事详情,老刘往门口看了看,压低声音:"记不清了,
只听说那晚西华门的内侍王瑾死在井里,这边就起了火,
火是从周侍郎当年的编修房烧起来的,偏就烧那几排架子,
像是...像是有人照着名册在烧卷宗。"他顿了顿,指节敲了敲沈砚之手里的薄子,
"这薄子...老奴前儿见掌院学士在翻,他袖口沾着红绳呢。"红绳。
沈砚之猛地想起薄子里"红绳系龙涎"那句诗。他翻出《明宫史》,
里面记载龙涎香除了熏衣,还是宫廷秘药"锁魂香"的药引,此香燃时无色无味,
闻多了会让人舌头发硬,说不出话。而他曾在锦衣卫旧档里见过烛龙教的记载,
说这教献祭时,最爱用浸过锁魂香的红绳缠住祭品的发,等祭品说不出求饶的话,
再一刀割喉取血。三更的梆子从街对面的钟楼传来,沈砚之对着残玉呵了口气,
水汽在玉面凝成一层白霜,竟显露出几行小字:"妖书案,牵涉东宫,
周侍郎藏副本于..."后面的字被利器刮去了,只留下歪歪扭扭的划痕,
边缘还沾着点暗红的渣,像干涸的血。沈砚之突然想起,
周明远当年负责编纂《万历起居注》,其中万历三十一年关于"妖书案"的三页记载,
在现存的抄本里全是空白。那妖书案本是动摇东宫的大案,
据说妖书里写着"郑贵妃欲废长立幼",后来虽以"妖人皦生光"顶罪结案,却始终有人说,
妖书是东宫自导自演,用来陷害郑贵妃的。窗外突然闪过一道黑影,
带起的风把烛火吹得歪斜。沈砚之猛地合上薄子,残玉掉在案几上,发出清脆的响。
他扑到窗边,只见月光下,史馆的屋脊上站着个穿蟒袍的人影,袍角在风里翻卷,
露出里面的玉带——是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系的玉带。那人手里把玩着什么,
反射的光在地上投出个蛇形的影子,随着手势扭动,像在朝拜。
沈砚之摸出祖父留下的那把锦衣卫短刀,刀鞘上的铜环在寂静中轻响。刀身出鞘时,
寒光映出他自己的脸,
竟与薄子里夹着的一张泛黄小像有几分像——那是周明远年轻时的画像,
眉眼间的痣都长在同一个地方。他突然想起父亲说过,母亲怀他时,
曾梦见过一个穿官服的人把半块玉塞进她怀里,醒来时枕边真有淡淡的龙涎香。
这时案几上的薄子突然自己翻开,停在第二页王瑾的记载上。"六月十三,夜,
西华门内侍王瑾坠井。捞起时发间缠红绳,井壁有爪痕。"旁边画着的蛇形符号,
与残玉上的烛龙纹完全重合。沈砚之翻出《明宫词》,
里面有首咏王瑾的诗:"红绳系发井中沉,龙涎香散月华深。莫言内侍无肝胆,
舌上金痕泣鬼神。"他把短刀按在脖子上,刀刃的寒气透过纸传来,
像有什么东西在下面躁动。
薄子里的金舌案、井中内侍、烧不掉的旧档...这些散落的珠子,
似乎正被一根无形的红绳串起。而绳子的尽头,
藏在青史没烧掉的那一页里——或许就是周明远藏起来的妖书副本,
或许是王瑾发间红绳绑着的密信,又或许,是祖父那半块玉佩背后,锦衣卫不敢说的秘密。
远处传来更夫打更的梆子声,四更快到了。沈砚之把残玉和薄子锁进樟木箱,
锁孔里突然卡进什么东西,他用力一拧,"咔哒"一声锁上时,竟从锁孔里掉出一小截红绳,
上面还沾着点龙涎香。他抬头看向窗外,屋脊上的人影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个模糊的脚印,
印在未化的残雪上,像只巨大的蛇爪。烛火突然爆出灯花,
沈砚之瞥见薄子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不知何时多了个指甲刻的"魏"字。魏忠贤?
还是他的党羽?他想起现任太傅魏广微,正是魏忠贤的侄子,而魏广微的父亲,
当年恰是刑部尚书,正是他判了周明远"误食毒菌"。沈砚之把短刀收回鞘中,铜环轻响时,
他仿佛听见祖父的声音在耳边说:"青史会骗人,可血不会...金舌会烂,
可玉上的痕不会..."第二章 红绳西华门的井被封在御花园的假山后,
青苔爬满了半人高的石盖,像层结了十年的厚痂。
沈砚之借着查"万历年间园林旧图"的名义穿过抄手游廊时,
石盖旁的老太监突然剧烈地咳起来,喉间的痰响像破风箱扯动,每一声都带着铁锈似的腥气。
这太监姓刘,宫里人都叫他刘伴伴,据说从万历朝就守着这口井,
眼瞧着从青丝人变成了白头翁,却始终不肯挪窝。"大人莫近前。
"刘伴伴的眼珠蒙着层白翳,却精准地锁定沈砚之的脚步,枯瘦的手攥着根拐杖,
杖头雕的龙首早被摸得包浆发亮。"这井里有水鬼,天启三年到现在,每到阴雨天,
就听得见有人喊'红绳勒脖子',那声音尖得能刺破耳膜,
跟...跟王瑾小公公死前头夜喊的一模一样。
"沈砚之的目光落在他腰间——根褪色的红绳正从灰布袍子里露出来,末端打了个古怪的结,
绳头缠着三圈细麻,正是薄子里画的烛龙教符号。他记得锦衣卫旧档里说,
这结叫"锁魂扣",越挣越紧,当年烛龙教在涿州献祭时,七个童男童女颈间都是这种结。
"公公信这些鬼神之说?"刘伴伴突然扑通跪下,红绳从怀里整个滑出来,
绳尾竟拴着半块玉佩,玉质与沈砚之袖中那片一般无二,只是边缘缺了个角,
像是被人硬生生掰断的。"大人救我!"他的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白翳后的眼珠滚出浑浊的泪,"当年王瑾是我同乡,都是顺天府宛平县人,
他死前头夜找过我,塞给我这半块玉,说'金舌藏玉,玉藏真相',只要把这玉交出去,
就能换条活路...可我不敢啊!"他突然抓住沈砚之的手腕,
掌心的老茧磨得人发疼:"王瑾说,周侍郎死前把东西藏在了'蛇眼'里,
让他务必传给'带卫字的人'。可第二天他就死在了井里,发间缠的红绳,
跟老奴腰间这条一模一样!这十年,我夜夜梦见他从井里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