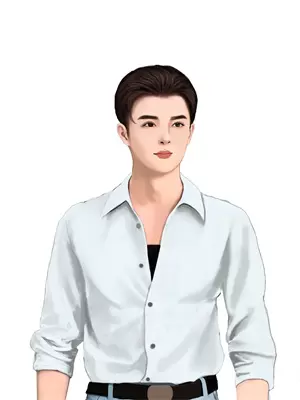南阳唐河县文物局来了个北大实习生。 领导让她去修一本乾隆年的唐河县志。
全县都等着用这本县志申请历史文化名城。 她却发现县志最后一页被撕掉,
粘上了民国时期的报纸。 报纸上报导的正是唐河大旱人相食的惨剧。
而县志编纂者的第七代孙,现在正是县里的主管领导。七月流火,
蝉鸣撕扯着中原小城午后凝固的空气。唐河县文物局那座五十年代建的苏式小楼里,
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烫的。沈芷,
一个顶着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光环的实习生,
此刻正对着一桌的镊子、软毛刷、pH试纸和一堆散发着陈旧气味儿的故纸堆,
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她是三天前到的。从北京西站到南阳东,
再坐上一个多小时颠簸的中巴,窗外的景致从连绵的华北平原过渡到伏牛山余脉的浅丘陵,
空气里尘土和庄稼的气息渐渐浓重。唐河县城比她想象的还要安静些,
老城区青灰色的屋檐挨挨挤挤,一条叫唐河的河水泛着黄绿色的光,缓缓穿城而过。
文物局就在河边,红砖墙爬满了常春藤,倒有几分不合时宜的雅致。带她的老师姓王,
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子,瘦,戴一副深度眼镜,话不多,整个人像他终日摩挲的那些古籍一样,
沉静,带着被时光浸透的颜色。局里上下,从局长到看门的大爷,
都知道沈芷是“北大的高材生”,目光里混杂着好奇、客气,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她明白,自己在这儿的一举一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那个遥远的学术殿堂的脸面。
任务下来得很快,也极其明确。王老师把她领到库房最里间一个恒温恒湿的柜子前,
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深蓝色的布面函套,动作轻柔得像对待婴儿。“小沈啊,
交给你个重要任务。”他推了推眼镜,语气是少有的郑重,
“修复这本乾隆三十八年纂修的《唐河县志》。”函套打开,
一股更浓烈的樟木混合着纸张老化特有的酸涩气味扑面而来。县志的本子比想象中要厚重,
开本阔大,纸色已然泛黄发脆,边缘多有虫蛀鼠啮的痕迹,线装的书脊也松散了,
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彻底散架。“这可是咱们县申请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关键证据’之一。
”王老师压低了声音,像是怕惊扰了书里的魂灵,“里头记载了唐河从建制沿革到风物人情,
尤其是明清时期的鼎盛状况,很多是孤本。省里的专家评审组下个月就要来,
全县上下都指望着它呢。”他顿了顿,看着沈芷,“时间紧,任务重,但一定要细致,
千万不能出岔子。”沈芷感到肩头一沉。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修复实习,
更像是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考试。她点了点头,没多说话,心里却绷起了一根弦。
修复工作就在二楼那间朝东的小工作室进行。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高大的梧桐树叶,
在磨石子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时,沈芷已经换上了白大褂,戴上薄棉手套,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先去打一盆蒸馏水,调试好修复用的纸浆补纸的pH值,
然后才轻轻打开那函套。修复古籍是门极需耐心的手艺。先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
对脆弱的页角进行加固,再用特制的薄如蝉翼的补纸,蘸上按古法调制的浆糊,
一点一点填补虫蛀的空洞。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轻柔、精准,呼吸都要控制。
她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有手指尖细微的动作和窗外不知疲倦的蝉鸣相伴。
县志的内容确实详实。
赋役物产、官师人物、烈女节妇……用精炼的文言文勾勒出一个传统农业县城的肌理与血脉。
她读到唐河作为南阳盆地重要水陆码头的昔日繁华,“舟车辐辏,
商贾云集”;也读到历代地方官兴修水利、鼓励农桑的政绩。字里行间,
是乾隆盛世的太平光景,是一种从容不迫的秩序感。
她甚至能想象出当年那些穿着长衫的编纂者,在县衙的厢房里,如何字斟句酌,
将一方水土的历史荣光凝结于笔墨。时间在纸页的翻动和修复中悄然流逝。
沈芷逐渐习惯了唐河的节奏。中午去机关食堂吃饭,
能听到同事们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闲聊,家长里短,物价房价,
偶尔也会提到“申名”工作,语气里满是期待。主管文化的副县长姓李,叫李文革,
据说对这事抓得特别紧,三天两头过问进度。沈芷在局里的宣传栏上见过他的照片,
五十岁上下,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很有几分干练的气质。有老同事私下说,
李副县长是本地人,祖上好像还出过读书人,对唐河的历史文化有很深的感情。
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那天下午,她修复到了县志的最后一卷。
这一卷主要是“杂记”和“附录”,记录一些无法归入前面各类的遗闻轶事、祥瑞灾异。
前面的修复都很顺利,纸张状态相对较好。当她翻到最后一页,
准备进行常规的清洁和加固时,手指触碰到书页的根部,一种异样的感觉让她停了下来。
这一页,似乎比前面的都要厚实一点,手感也略有不同。
她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尖端轻轻拨开页脚。果然,靠近书脊装订线的地方,
原本应该是一张完整书页的边缘,出现了不自然的、参差不齐的毛边。而在这毛边之上,
覆盖着另一层纸张,用一种颜色发暗、质地也更粗糙的浆糊粘合着。这不是原装的。
这是一页被撕掉后,又被人精心地粘贴上了一页别的纸。她的心猛地一跳。
古籍修复最怕遇到这种情况——人为的篡改或破坏。这通常意味着隐藏着什么。
她深吸一口气,稳住有些微颤的手,将工作台的侧灯角度调整好,拿起放大镜,
凑近了仔细观察那层覆盖上去的纸。透过泛黄且脆弱的纸背,
能看到下面透出的模糊字迹和纸张的纹理。覆盖的纸张明显年代晚于乾隆时期的开化榜纸,
更像是民国以后机制纸的质感。她一点点移动放大镜,辨认着被覆盖处边缘残存的墨迹,
似乎是几个笔画繁复的字,但无法连成句。关键是被粘上去的这页纸的正面,写的是什么?
或者,它本身是什么?粘合处非常牢固,历经岁月,浆糊已经老化发硬,直接揭开风险极大,
很可能造成两面纸张的同时损毁。沈芷犹豫了。按照标准的修复伦理,对于后人的添加物,
尤其是可能具有历史信息价值的,不能轻易去除。但眼下,
这个添加物明显掩盖了县志的原始内容,而这部县志又关乎全县的重要工作。
她想起了王老师郑重的嘱托,想起了李副县长锐利的眼神,想起了同事们对“申名”的期盼。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这个发现,像一颗埋藏在平静表象下的地雷。思考再三,
她决定暂时不动它。先记录下来,然后向王老师汇报。她拿出相机,
从不同角度拍摄了这处异常的细节,包括那隐约透出的字迹和粘合处的状态。然后,
她尝试着更轻柔地处理覆盖页的正面,希望能看清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覆盖的纸张是一张残缺的旧报纸的一角。版面模糊,铅字排列紧密。
她用药棉蘸取极少量的纯净水,轻轻点在纸张边缘非文字区域,待其微微湿润软化后,
再用镊子极小心地将卷曲的边缘展平。放大镜下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报纸的报头残缺,
只能辨认出“……中原……报”几个字。日期部位恰好有破损,但根据字体风格和纸张判断,
应是民国时期的出版物。最大的标题字迹较大,虽然墨色脱落严重,
但还能勉强认出:“……唐河……大旱……惨绝人寰……”下面的小字报道更为模糊,
她屏住呼吸,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自去岁秋徂今夏,滴雨未降,赤地千里,
唐河水竭,禾稼枯焦……民掘草根、剥树皮殆尽……乃至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饿殍载道,
户口减半……实为百年未有之奇灾……”“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这八个字像烧红的烙铁,
烫得沈芷几乎拿不稳放大镜。民国时期的报纸,用最触目惊心的字眼,
记录了一场发生在唐河的、惨烈到人相食的大旱灾。而这页报道,被谁,又为了什么,
如此隐秘地粘贴在了这本宣称记录“太平盛世”的乾隆县志的最后一页?
那被覆盖、被撕掉的原始最后一页,又写了什么?巨大的疑问和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她。
这本被视为“荣光”象征的县志,它的尽头,竟然粘附着一页如此惨痛的记忆。这绝非偶然。
她立刻去找了王老师。王老师正在库房里整理一批新收来的民俗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