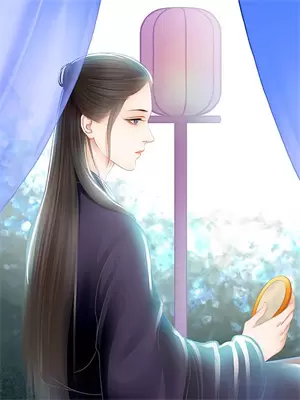雨后的空气带着一股铁锈和湿泥的混合气味,黏稠地贴在皮肤上。柳白白拄着盲杖,
小心翼翼地点着身前坑洼不平的地面,水洼溅起的凉意透过裤脚,让她微微蹙眉。
这条走了无数次的回家小路,今天似乎格外漫长,盲杖敲击的“嗒嗒”声,
在寂静的巷弄里回荡,显得空洞而孤单。她的世界一如既往,是浓稠得化不开的黑暗,
偶尔有车辆驶过的声音,带着湿漉漉的胎噪,由远及近,再滑向远方。回到租住的廉价单间,
一股老房子特有的霉味扑面而来。她反手锁上门,背靠着冰冷的铁皮门板,轻轻吁了口气。
就在这时,脚边似乎踢到了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硬质的纸盒。寄件人处一片空白,
只有打印的、她自己的名字和地址。指腹摩挲着粗糙的纸盒表面,
柳白白的心跳莫名快了几拍。会是谁?她几乎没有朋友,亲人更是早已疏远。犹豫片刻,
她沿着封口胶带的方向,慢慢撕开了盒子。里面是一个硬质的眼镜盒,触手冰凉。打开盒盖,
一副眼镜静静躺在天鹅绒衬布上。她拿起它,很轻,镜腿折叠的关节活动顺滑,不像便宜货。
鬼使神差地,她将它戴上了。没有预想中的不适,镜架完美地贴合了她的鼻梁和耳廓。
然后——光。不是她记忆中残留的、模糊的光感,而是尖锐的、爆炸般的色彩和信息洪流,
猛地冲入了她的大脑。她短促地惊叫了一声,下意识地闭上眼,
但那景象已经烙印在视网膜上——斑驳脱落的天花板,积着灰尘的窗棂,
自己微微颤抖的、骨节分明的手指……她猛地睁开眼,
贪婪地、近乎恐惧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墙壁上水渍晕开的形状,地板上木头的纹理,
窗外远处广告牌闪烁的、她无法理解的字符……一切都带着一种陌生的、令人晕眩的清晰。
泪水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视野变得模糊。她真的……看见了?激动稍稍平复后,
一丝异样感浮上心头。这个世界,似乎覆盖着一层极淡的、近乎透明的灰色滤镜。而且,
有些东西不对劲。她看向窗外,天色是一种沉郁的灰蓝。而在那灰蓝之中,
纵横交错着无数极细的黑色丝线。它们像是活物的脉络,又像是某种庞大无比的神经网络,
无声地遍布视野所及的每一寸空间,从天空垂落,缠绕着远处的建筑,没入地面,
又再次钻出,延伸向不可知的远方。这些丝线并非静止,
它们以一种缓慢而规律的节奏微微搏动着,像是拥有自己的生命。柳白白感到一阵反胃,
强压下不适,推开门走了出去。街道上车流缓慢移动,行人步履匆匆。然后,她看到了。
每一个人,每一个行走的、说话的、站立的人,身上都连接着那些黑色的丝线!多的几十根,
少的也有七八根,从他们的头顶、后背、四肢延伸出来,
没入上方那庞大的、无处不在的线网之中。一个边走边看手机的男人,
他脖颈和后脑勺连接的几根丝线正有节奏地轻微抽动;一个站在路边发呆的女人,
连接她四肢的丝线则松弛地垂着。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姿态,甚至他们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
似乎都与那些丝线的牵引息息相关。这不是看见,这是窥破了一个惊悚的真相。
她踉跄着退回家中,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心脏狂跳得快要炸开。冷汗瞬间浸透了她的后背。
那些丝线……它们在操控所有人!像摆弄提线木偶一样!那我自己呢?这个念头如同冰锥,
狠狠扎进她的脑海。她颤抖着,极其缓慢地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身体。有。她身上也有。
而且,非常多。密密麻麻,成千上万,比外面看到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出无数倍!
这些细若游毫的黑色丝线,
从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钻出——皮肤、指尖、发梢、眼眶……它们缠绕着她,包裹着她,
像一层蠕动的、活着的黑色茧衣。这些丝线并非全部向上连接着天花板或天空,
其中绝大部分,是直接没入了她身后的虚空之中,仿佛她坐在这里,
本身就是这个巨大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
或者说……一个被无数线缆精心喂养、监控着的培养皿。“不……不!
”她发出一声压抑的嘶鸣,猛地伸手去抓扯脸上的眼镜。那冰凉的触感此刻变得无比恶心。
就在她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镜腿的瞬间,一个声音毫无征兆地在她耳边响起,
清晰得如同贴着她的耳廓低语,语调却异常地温柔、平和:“别摘,我们在帮你看见真实。
”柳白白的手僵在半空,血液仿佛瞬间冻结。那声音不属于她听过的任何一个人。
它没有源头,就这么直接出现在她的听觉神经里。“谁?!”她尖声问道,
声音因恐惧而变调。她猛地环顾四周,空无一人,只有那些无声搏动着的黑色丝线,
在她视野里构成一幅诡异绝伦的背景。没有回应。那个声音说完那句后,便彻底消失了,
留下死一般的寂静,以及在她脑中疯狂回荡的余音。恐惧如同潮水,一波波冲击着她的理智。
她不是旁观者,她是……什么?一个特殊的傀儡?一个被重点“关照”的实验品?
那个声音……是这些丝线的主人?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她蜷缩在墙角,双臂紧紧抱住自己,
试图从那冰冷的触感中汲取一丝虚假的安全感。时间一点点流逝,
窗外的天色由灰蓝转为沉黯,房间内没有开灯,阴影爬满了角落。
那些黑色的丝线在昏暗中似乎更加清晰了,它们在她身上,在房间里,在整个世界里,
无声地脉动,如同一个巨大生物缓慢而有力的心跳。她必须弄清楚。深吸几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开始尝试与这些丝线“互动”。她集中精神,
试图用意志去“命令”连接在自己右手食指上的那根丝线停止搏动。失败了。
丝线依旧按照原有的节奏微微蠕动。她又试着去“看”这些丝线的来源。她仰起头,
视线顺着那些从自己身上伸出、没入上方虚空的丝线追溯,
目光投入那片由无数丝线交织成的、深不见底的黑暗网络。意识仿佛被拉扯进去,
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她只“看”到一片混沌,一种庞大到超越理解的存在感,
压得她几乎窒息,连忙收回了目光。那个声音没有再出现。但它留下的那句话,
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盘踞在她的心头。“我们在帮你看见真实。”真实?这就是真实?
一个所有人都被无形丝线操控的世界?
一个她自己更是被无数丝线缠绕、如同核心标本的世界?
她想起之前二十多年在黑暗中生活的点滴。那些凭借听觉、触觉、嗅觉构建起来的世界,
虽然残缺,却似乎……更“干净”。至少,没有这些令人发疯的黑色丝线。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柳白白像个幽魂一样,在房间里缓慢移动,
仔细观察着这个“真实”的世界。她发现,那些连接在普通人身上的丝线,
偶尔会变得格外活跃。比如,当楼下传来夫妻争吵的声音时,
会剧烈地抖动、收紧;而当电视里她凭着声音和模糊的光影判断播放一段激昂的音乐时,
街上行人身上某些丝线也会随之产生同步的波动。这些丝线,似乎在调节、引导,
甚至……制造着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她低头看着自己身上那厚厚一层“茧衣”,
一种更深的寒意渗透骨髓。如果普通人只是被几根、几十根丝线影响,那她这成千上万根,
又是在干什么?她过去的每一个念头,每一次“自由”的抉择,是不是都……她再次伸手,
这次动作快得像触电,一把抓住了眼镜腿,用力往下扯!
一阵强烈的、如同电流穿过般的刺痛感从太阳穴炸开!与此同时,那个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责备?“不建议你这样做,柳白白。适应需要过程。
”眼镜像是焊在了她的脸上,纹丝不动。柳白白绝望地松开了手,刺痛感缓缓消退。
她瘫坐在地,大口喘着气。她被困住了。被困在这副让她“看见”的眼镜里,
困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中。她靠在冰冷的墙壁上,目光无意识地扫过房间。忽然,
她注意到墙壁上那些原本静止的、细微的裂纹,在她聚焦视线时,
其内部似乎也有极其微小的黑色丝线在蠕动,如同毛细血管。她看向木质桌腿,
看向水杯的边缘,看向自己的掌心纹路……无处不在!这些丝线不仅仅是连接着人和天空,
它们根本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基础结构!这个世界,是活的?
还是一个被编织出来的……巨大囚笼?极度的疲惫和精神冲击最终让她昏睡过去。睡梦中,
她仿佛漂浮在无边无际的黑色线网之中,那些丝线缠绕着她,拉扯着她,
那个温柔的声音时而贴近,时而遥远,反复诉说着“真实”、“帮助”、“适应”。
她是特殊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份特殊,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更深邃的恐怖。第二天,
她是被窗外嘈杂的声响惊醒的。雨已经停了,但天色依旧阴沉。她发现自己还戴着那副眼镜,
那个噩梦般的“真实”世界没有丝毫改变。她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掀开一角窗帘。街道上,
发生了更诡异的事情。许多人停下了脚步,站在原地,仰着头,
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统一的、茫然而空洞的表情。他们身上连接的黑色丝线,
此刻正发出一种极其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灰光,并且以完全同步的频率高速震颤着。
像收到了同一个指令的机器。而在这些“静止”的人群中,仍有少数人在正常活动,
他们身上的丝线则保持着原有的、相对缓慢的搏动。
一个正常行走的男人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静止不动、仰头望天的女人,那女人毫无反应,
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男人则低声咒骂了一句,绕开了她。这一幕让柳白白遍体生寒。
这种大规模的、同步的异常……是那个“声音”背后的存在在做什么?测试?调整?
还是……别的什么?她低头看向自己。她身上的丝线没有发出灰光,也没有同步震颤,
但它们搏动的节奏,似乎比昨天更快了一些,更……活跃了。那个声音在她耳边轻柔地响起,
带着一种循循善诱的意味:“看,他们需要引导。而你,柳白白,你需要学习。”学习?
学习什么?学习如何像它们一样“引导”他人?
还是学习如何……接受自己这被无数丝线缠绕的“本质”?柳白白没有问出口。
她只是死死地盯着窗外那幅诡异的景象,盯着那些如同被按了暂停键的人偶,
盯着自己身上这层蠕动着的、活着的黑色茧衣。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巨大的荒谬感和恐惧感攫住了她。她究竟变成了什么?视线穿过窗户,
投向更远处那片被无数黑色丝线笼罩的、灰蒙蒙的天空。这个由神经般丝线构成的庞大活物,
它的终点在哪里?或者,它根本没有终点?她靠在冰冷的玻璃上,轻轻地问,
声音嘶哑得如同破旧的风箱:“‘你们’……到底是什么?”没有回答。只有身上万千丝线,
无声蠕动着,像是在代替那个未知的存在,发出沉默的嘲笑。柳白白靠在冰冷的窗玻璃上,
那句无声的诘问在胸腔里反复冲撞,却找不到出口。“你们……到底是什么?
”恐惧像藤蔓一样勒紧她的心脏,每一次搏动都带来尖锐的疼痛。窗外,
那些静止仰头的人偶身上,灰光丝线的震颤逐渐平息,他们像是被重新上紧了发条,
茫然地四下张望片刻,又恢复了“正常”的行进,
仿佛刚才那诡异的集体停顿只是一场集体的白日梦。但柳白白知道不是。
她身上的“茧衣”搏动得更快了,一种微弱的、类似电流通过的麻痒感开始在她皮肤下游走。
那个声音没有再直接响起,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破碎的、不属于她的感知碎片,
开始不受控制地涌入她的脑海。——是办公室里那个总爱抱怨的同事,此刻正对着电脑屏幕,
心底翻涌着对上司的恶毒诅咒,连接他后颈的几根粗壮丝线随之泛起暗红色的波动。
——是楼下早餐店的老板娘,一边机械地包着馄饨,一边想着住院孩子高额的医药费,
绝望像灰色的雾气,通过她手腕连接的丝线弥散开。 ——是远处公园长椅上,
一个男人偷偷看着手机里存着的旧照片,苦涩而温柔的怀念,化作一种淡金色的微光,
在他心口连接的丝线上闪烁。无数人的情绪、念头,哪怕是转瞬即逝的,
都通过这张庞大的网络,被捕捉,被传导。而柳白白,因为她身上那异常密集的丝线,
成了一个被迫的、高灵敏度的接收器。噪音,全是噪音!
愤怒、焦虑、悲伤、虚伪的欢笑、压抑的欲望……亿万人的内心杂音化作汹涌的潮水,
冲击着她脆弱的神经,几乎要将她逼疯。她死死捂住耳朵,但这毫无用处。
声音直接在她意识里轰鸣。“停下……让我出去……”她蜷缩在墙角,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试图用疼痛来保持清醒。就在这时,那个温柔的声音再次贴着她的耳廓响起,
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耐心:“数据流过于庞杂,需要过滤和适应。你在学习接收,
这是第一步。”学习?接收?柳白白猛地抬起头,
布满血丝的眼睛她现在已经能“看见”自己眼睛里的血丝了死死盯着虚空:“我不学!
放我出去!把这该死的东西拿掉!”她再次疯狂地去抠抓眼镜,
太阳穴立刻传来熟悉的、更强烈的刺痛,仿佛有细小的针直接扎进大脑皮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