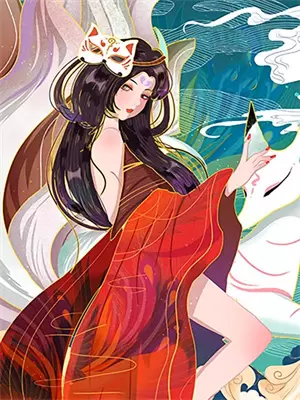林深时见鹿,沈倦处听风林深第一次见到沈倦,是在大学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
那天是九月,秋老虎正烈,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空气中浮动着旧书和樟木书架混合的味道。他抱着一摞建筑史相关的书,拐过书架转角时,
脚步猛地顿住——靠窗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个男生。男生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
袖口卷到手肘,露出线条清晰的小臂。他没看书,也没看手机,只是微微偏着头,
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老香樟的树冠上,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方投出一小片阴影。
阳光漫不经心地落在他发梢,镀上一层浅金,连带着他周身的气息都变得懒洋洋的,
像猫蜷在午后的暖阳里,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倦意。林深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
他不是容易对陌生人产生好奇的人,建筑系的课业压得他喘不过气,每天不是在画图,
就是在去画图的路上,生活像精准咬合的齿轮,规律得近乎刻板。可那一刻,
他看着那个男生,忽然觉得图书馆里的时间流速都慢了下来。他放轻脚步,
把书放在旁边的阅览桌上,尽量不发出声音。男生似乎察觉到动静,转过头来。
那是一张很干净的脸,五官算不上惊艳,却组合得格外舒服,尤其是眼神,很淡,
像蒙着一层薄雾的湖面,看向林深时,没什么情绪,却也不算疏离。“抱歉,打扰了?
”林深先开了口,声音有些干涩。男生摇摇头,嘴角似乎微微动了一下,像是笑,又不像,
“这里没人。”他的声音和他的人很像,低低的,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慵懒,像晚风拂过湖面,
荡开一圈极轻的涟漪。林深点点头,没再多说,坐下翻书。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他一个字也没看进去。余光里总忍不住飘向那个方向,看男生重新偏过头,继续望着窗外,
看阳光在他侧脸移动,看他偶尔抬手,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沙发扶手。他不知道男生叫什么,
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直到闭馆前,男生起身离开,林深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他摊在膝头的笔记本上,只画了半张速写——是窗外那棵香樟的枝桠,线条利落又随意,
带着种松弛的灵气。那天晚上,林深对着电脑屏幕上未完成的建筑草图,第一次分了神。
他想起那个男生的侧脸,想起他睫毛投下的阴影,想起他声音里那点漫不经心的倦意。
后来的日子,林深成了图书馆三楼靠窗位置的常客。有时那个位置空着,他会坐在那里,
试着像男生那样望向窗外,可看到的只有寻常的香樟和远处的教学楼,没什么特别。
有时男生在,他们就各占一角,互不打扰,只有书页翻动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
林深渐渐摸清了他的规律:他通常下午来,坐两三个小时,有时看书,有时画画,
更多时候只是坐着发呆。他从不带太多东西,最多一个黑色帆布包,
里面装着笔记本和几支笔。有一次林深无意间瞥见帆布包侧面绣着一小簇银灰色的芦苇,
针脚很密,不像男生会做的手工,倒像是被人精心缝上去的。直到两周后的一个雨天,
林深才知道他的名字。那天雨下得很大,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窗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林深画完一张图,抬头时发现男生正站在窗边,望着雨幕出神。他的帆布包放在沙发上,
拉链没拉严,露出里面的笔记本。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了,林深忽然走过去,
指着窗外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香樟,问:“你很喜欢这棵树?”男生转过头,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他会主动搭话。雨光落在他脸上,让他眼底的那层薄雾更明显了些。“嗯,
”他应了一声,“它长得很随意。”林深觉得这形容很贴切。
那棵香樟确实不似校园里其他的树那样规整,枝桠肆意地伸展,带着种野生的生命力。
“我叫林深,建筑系的。”他伸出手,有些紧张。男生看了看他的手,迟疑了半秒,
轻轻握了上去。他的指尖很凉,像刚沾过雨水。“沈倦。”他说,“哲学系。”沈倦。
林深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觉得和他的人简直是绝配。沈浸在倦怠里的人,
连名字都带着点慵懒的诗意。那天的雨一直没停,闭馆时,林深发现沈倦没带伞。
他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黑伞递过去:“先用我的吧,我住得近,跑回去就行。
”沈倦看着那把伞,又看了看外面瓢泼的雨,没推辞,“明天还你?”“不用急。
”林深笑了笑,转身冲进雨里。雨点打在身上,冰凉刺骨,可他心里却莫名有些发烫。
跑过图书馆门口时,他回头望了一眼,看见沈倦撑着他的伞,站在屋檐下,
身影被雨幕拉得很长。风吹起他的衣角,露出帆布包上那簇芦苇,在雨里轻轻晃动。第二天,
林深去图书馆时,沈倦已经在了,他的黑伞靠在沙发边,伞面上还带着未干的水痕。
沈倦把一本《瓦尔登湖》推到他面前:“昨天谢谢了,这个借你看。”书的扉页上,
有一行小小的字迹,是沈倦的名字,笔锋很轻,像羽毛落在纸上。林深翻开第一页,
发现夹着一片干枯的香樟叶,边缘有些卷曲,却还能看出清晰的纹路。从那天起,
他们之间的沉默被打破了。林深会和沈倦聊建筑史里那些奇奇怪怪的细节,
比如某个教堂的飞扶壁其实藏着工匠的涂鸦;沈倦则会讲些哲学里的悖论,
比如“忒修斯之船”到底还是不是原来的船。林深语速快,逻辑清晰,
讲起专业眼睛发亮;沈倦话不多,总是听着,偶尔插一两句,却总能戳中关键,
声音依旧是懒懒的,却让林深觉得格外安心。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窗外那棵香樟。沈倦说,
他小时候住的院子里也有一棵,比学校这棵还要粗,夏天的时候,他总在树下看书,听蝉鸣,
看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在地上跳格子。“后来院子拆了,树也砍了。”他说这话时,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帆布包上的芦苇,眼神飘向远处,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怅然,
“我奶奶在那棵树下教我画过画,她手很巧,会绣东西,包上这个就是她绣的。
”林深忽然明白,沈倦不是在看树,是在透过树,看过去的时光。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工地,父亲总会捡起废弃的钢筋给他折小玩意儿,
那些冰冷的金属在父亲手里能变成会跑的小狗、会飞的小鸟,那是他对“建造”最初的记忆。
他们开始一起在图书馆待到闭馆,一起走回宿舍。林深住东区,沈倦住西区,
要在岔路口分开。每次分别时,沈倦都会说一句“明天见”,声音很轻,
却像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在林深心里漾开圈圈涟漪。有一次林深熬夜画图,第二天起晚了,
匆匆赶到图书馆时,发现沈倦坐在老位置上,面前放着两个热包子,是他常吃的那家店的。
“猜你没吃早饭。”沈倦抬头看他,眼底带着点浅浅的笑意,晨光落在他睫毛上,
像落了层碎金。林深发现自己的生活开始偏离既定的轨道。他会提前完成作业,
只为能和沈倦多待一会儿;会在画图累了的时候,想起沈倦说话的语调,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会在路过文具店时,买下一支沈倦常用的那种细杆铅笔,
虽然他根本用不上,却还是放在笔袋里,偶尔拿出来看看。他甚至开始期待阴雨天,
因为沈倦总在阴天显得格外安静,会靠在沙发上,听着雨声打盹,睫毛微微颤动,
像只小憩的蝶。林深会偷偷看着他,心里有种隐秘的欢喜,像偷藏了一块糖。
有一次雨下得特别大,沈倦睡着了,头轻轻靠在沙发背上,林深犹豫了很久,
还是脱下自己的外套,小心翼翼地披在他身上。沈倦似乎被惊动了,睫毛颤了颤,却没醒,
只是往外套里缩了缩,像只找到温暖巢穴的猫。变故发生在十一月。那天林深去系里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