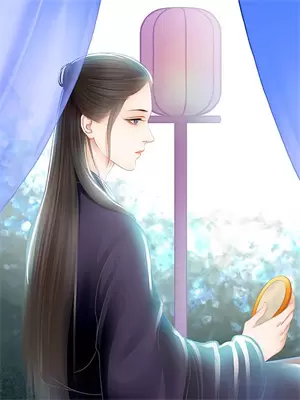医院夜班保安交接班时总叮嘱我:三楼妇产科深夜听见婴儿哭,千万别开灯,
用手电筒照角落的旧娃娃。我笑他们迷信,直到那晚哭声震耳欲聋。
我下意识按下电灯开关。整层楼的婴儿标本罐齐齐转向我,
怀里的塑料娃娃咧嘴一笑:哥哥,你吵醒我们了。---凌晨一点五十分,
我裹紧单薄的保安制服外套,推开市三医院保安室那扇吱呀作响的铁皮门。
一股混合着廉价香烟、隔夜茶和某种类似消毒水又更刺鼻的气点的气味扑面而来。
值前半夜的老刘正瘫在掉皮的旧椅子上,对着手机屏幕咧着嘴笑,昏暗的灯光下,
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被屏幕光映得一片惨白。“来了?”老刘眼皮都没抬,
含糊地招呼了一声,手指在屏幕上划得飞快。“嗯。”我把背包甩到角落那张更破的椅子上,
揉了揉发涩的眼睛。连轴转的第三个夜班,身体的疲惫已经沉淀到骨子里,
但神经却因为浓茶和必须保持清醒的责任感而绷紧着。这份夜班保安的工作,
薪水比白班高出一截,对我这个需要钱的人来说,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尽管,
所有人都说这医院的夜班,尤其三楼,有点“邪乎”。老刘终于打完了一局,
慢吞吞地收起手机,开始收拾他那泡着浓茶、杯壁积满茶垢的保温杯。交接班的过程很机械,
无非是巡查记录本签字,钥匙串交接,以及对讲机电量确认。完事后,老刘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骨头节发出咔吧的脆响。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转过身,那张总是带着点油滑笑意的脸,难得地严肃起来,压低了声音:“小子,
规规矩矩巡你的楼,特别是……三楼妇产科那边。”又来了。我心底泛起一丝不耐,
但还是点了点头。老刘看我反应平淡,又凑近了些,一股烟味窜进我的鼻子:“听着,
不是开玩笑。要是半夜在三楼,听见……听见有小孩哭,”他顿了顿,
眼神里掠过一丝极难察觉的惊惧,“记住,千万别图省事去开走廊的灯!一定用手电,
照一下走廊最里头那个角落,就那个……不知道哪个缺德家长扔那儿的旧娃娃。
”我顺着他的目光瞥向墙上挂着的巡查区域图,三楼妇产科走廊尽头,确实有个模糊的标记,
旁边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娃娃”两个字。那娃娃我来这儿第一天就见过,半旧不新,
穿着脏兮兮的粉色裙子,头发乱糟糟,一只眼睛的漆都掉了,黑洞洞的,
随便扔在废弃的候诊椅底下,大概是哪个病人遗弃的。“刘哥,
这都什么年代了……”我忍不住想笑,“不就是个没人要的玩具吗?还能蹦起来咬人不成?
”老刘的脸色更沉了,几乎有些发青:“你懂个屁!老子在这破医院熬了十几年夜班,
什么邪性事没见过?就上个月,隔壁科室那小张,不信邪,听见哭声就去开灯,
结果第二天就发高烧说胡话,没一个礼拜就辞职了,现在人还恍恍惚惚的!”他喘了口气,
盯着我的眼睛,“手电光就行,照一下那娃娃,哭声准停。这是规矩!老辈儿传下来的!
”看着他煞有介事的样子,我心里那点不以为然反而更重了。吓唬新人的老把戏罢了,
无非是想显得自己资历老,或者就是长期夜班导致的神经衰弱。这世上哪来的鬼?要真有,
这医院太平间岂不是得天天开派对?“行了行了,刘哥,我知道了。听见哭声,不开灯,
用手电照娃娃。”我敷衍地重复了一遍,只想赶紧打发他走。老刘似乎看出我的不信,
张了张嘴,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用一种近乎怜悯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拉开门,
身影消失在浓稠的夜色里。门外走廊的风灌进来,带着医院特有的阴冷潮湿的气息,
让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保安室重新安静下来,只剩下老旧挂钟秒针走动的“咔哒”声,
规律得令人心烦。我坐回椅子,打开巡查记录本,准备熬过这漫长的八小时。
时间像滴漏里的沙子,缓慢而粘滞地流逝。前半夜风平浪静,
只有几次呼叫铃的微弱声响和远处模糊的仪器滴答声。我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两次巡查,
刻意避开了三楼,直接从二楼坐电梯上了四楼。经过三楼楼梯口时,那扇防火门紧闭着,
门上的小窗后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我总觉得那扇门后格外安静,
静得连空气都凝固了。凌晨三点,是一天中最困顿,也最阴冷的时刻。
我正对着监控屏幕打瞌睡,屏幕上十几个小格子大多一片死寂,
只有急诊科的画面偶尔有人影晃动。就在这时,一阵极其细微、若有若无的声音,
像丝线一样,钻进了我的耳朵。是哭声。非常非常遥远的,仿佛隔着重重大门和墙壁,
但确实存在。像猫叫,又更委屈,更……令人心头发紧。是婴儿的啼哭。我猛地清醒过来,
屏住呼吸侧耳倾听。声音似乎是从楼梯间那个方向传来的,断断续续,飘忽不定。
难道真有产妇半夜住进来?或者是哪个病房电视的声音?可这哭声……太清晰了,
不像隔音效果尚可的病房里传出的,倒像是……就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
老刘的话鬼使神差地在我脑海里响起。我甩甩头,试图驱散这荒谬的联想。肯定是幻听,
或者不知道哪里的管道风声。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回监控屏幕,
但那双耳朵却不受控制地捕捉着那缕游丝般的哭声。几分钟后,哭声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不再是若有若无,而是真真切切地,从三楼的方向传来。
一声接一声,不高亢,却带着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悲伤和冰冷,钻进人的骨头缝里。
我的后背开始发凉。理智告诉我这不合常理,三楼妇产科夜间根本没有住院病人,
只有几间存放病历和少量医疗器械的库房,
以及那个早已废弃、据说要改建成什么健康管理中心但一直没动静的旧产房区域。
怎么可能有婴儿哭?我站起身,在狭小的保安室里踱了两步。手电筒就挂在墙上的挂钩上,
旁边是走廊照明灯的总开关。按规定,夜间巡查遇到异常,首先应该上报值班护士长,
或者至少用对讲机联系一下各楼层值班护士站确认情况。
可万一……万一只是哪个粗心的护士把手机忘在值班室,播放着什么安抚婴儿的白噪音呢?
我这么兴师动众,岂不是要被她们笑话死?尤其是那个总爱拿我打趣的急诊科小护士。
哭声还在继续,甚至带上了一点抽噎的腔调,在死寂的医院里回荡,显得格外瘆人。妈的,
去看看!我就不信这个邪!一股莫名的倔强冲上了头顶。与其在这里自己吓自己,
不如亲眼去证实那不过是某种可以解释的声响。也许是哪扇窗户没关好,也许是……总之,
不可能是老刘说的那种情况。我一把抓下强光手电,检查了一下电量,满格。深吸一口气,
我拉开了保安室的门,走进了空旷昏暗的一楼大厅。廊灯为了省电,只开了几盏应急照明,
在地上投下长长短短、扭曲变形影子。我的脚步声在光滑的地砖上发出空旷的回响,
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跳上。没有坐电梯,我选择走楼梯。防火门沉重的推开时,
发出“嘎吱”一声怪响,身后的光线被吞没,
楼梯间里只有绿色的“安全出口”指示牌散发着幽光。那哭声在这里听起来更近了,
仿佛就在头顶上方不远的地方。我一步步踏上台阶,水泥台阶冰冷坚硬。越往上,
哭声越清晰,那声音里的悲切和寒意也越发浓重。它不再像是单纯的啼哭,
更像是一种……哀怨的控诉,缠绕在冰冷的空气里。终于,我停在了三楼防火门的门口。
哭声,就在这扇门的后面,毫无阻碍地传出来,异常响亮。透过门上的小窗,
可以看到里面走廊一片漆黑,只有远处某个安全指示牌的一点微光。我的手心有些出汗,
紧紧攥着手电筒。
老刘的叮嘱再次浮现:“千万别开灯……用手电照角落的旧娃娃……”荒谬!
我在心里啐了一口。开灯看得清楚,有什么不好?灯光能驱散一切牛鬼蛇神!于是,
在一种混合着叛逆、紧张和一探究竟的冲动下,我伸出手,没有去推那扇沉重的防火门,
而是准确地摸到了门边墙壁上的照明开关面板。那塑料按键冰凉。下一刻,我用力按了下去。
“啪嗒!”清脆的开关声响过之后,头顶的日光灯管一阵剧烈的闪烁,
发出令人牙酸的“滋滋”声,然后,整条三楼走廊的灯光,猛地亮了起来!
惨白、刺眼的光芒瞬间驱散了所有黑暗,将一切都暴露无遗。也就在这一刹那,
那持续了许久的婴儿啼哭声,戛然而止。整个世界陷入一种极致的、令人窒息的死寂。
我的眼睛被强光刺得眯了一下,随即适应了光线。走廊空荡荡的,
和我白天巡查时看到的没什么两样,两侧是紧闭的办公室和库房门,地面上光洁可鉴,
反射着灯光。看吧,果然是自己吓自己。我松了口气,几乎要为自己的疑神疑鬼笑出声。
哪有什么鬼娃娃,灯一亮,
什么怪声都没了……我的目光下意识地、几乎是带着一丝胜利者的姿态,
扫向走廊尽头那个角落,老刘再三强调的那个地方——那个废弃的候诊椅底下。
那个脏兮兮的旧娃娃,还在那里,姿势似乎和白天有点不一样,但隔着这么远,看不太清。
然后,我的视线不受控制地、僵硬地转向了走廊两侧墙壁上。那里,
整齐地镶嵌着妇产科用来做宣传或者展示的玻璃橱窗。橱窗里面,
通常摆放着一些胎儿发育过程的模型,或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的、真实的人类婴儿标本,
用于教学目的。白天路过时,我从不忍细看那些模糊的小小身影。此刻,在惨白的灯光下,
每一个玻璃罐都清晰无比。
曾经或许有过生命的、蜷缩着的、皮肤呈暗红色的婴儿标本……它们的脸……全都转向了我。
每一张模糊的、紧闭双眼的、带着永恒沉睡表情的小脸,都精准地、无声地,
对准了我所站立的门口方向。仿佛我按下开关的那声轻响,不是打开了灯,
而是吹响了集合的号角。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大脑一片空白,
无法理解眼前这违背了一切物理法则和生物学常识的景象。恐惧像一只冰冷的巨手,
攥紧了我的心脏,扼住了我的喉咙,让我连一声尖叫都发不出来。
就在这极致的惊恐和死寂中。一个清晰的、带着稚嫩童音,却又冰冷得没有任何温度的语调,
从我目光最初投向的那个角落,清晰地传来:“哥哥,你吵醒我们了。”我猛地扭头,
视线越过空旷的走廊,死死钉在尽头那个角落。那个原本应该躺在废弃候诊椅底下的旧娃娃,
此刻,正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它身上那件脏兮兮的粉色裙子,
在惨白灯光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色泽。乱糟糟的头发下,那只掉了漆、黑洞洞的眼眶对着我,
而另一只完好的、玻璃珠做的眼睛,则反射着冰冷的光。它的嘴角,
咧开到了一个绝不可能属于塑料玩具的、极其夸张的弧度,
露出里面同样是塑料的、但此刻看来却森然无比的细小牙齿。它在笑。无声地,对着我笑。
“嗬……”我倒抽一口冷气,肺里的空气仿佛被瞬间抽空,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怪响。
巨大的恐惧不是缓缓蔓延,而是像高压电流一样击穿了我的每一寸神经。我想后退,
想转身逃跑,想尖叫,但身体就像被无形的钉子钉在了原地,四肢僵硬冰冷,
只有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跑!快跑!求生本能终于冲破了恐惧的束缚,
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我猛地转身,不顾一切地扑向那扇近在咫尺的防火门。
手指颤抖得几乎握不住门把手,冰冷的金属触感反而刺激了麻木的神经。
我用尽全身力气一拉——门纹丝不动。怎么可能?我刚才就是从这门进来的!它根本没有锁!
我疯狂地摇晃着门把手,沉重的铁门发出哐当哐当的巨响,在这死寂的环境里显得格外刺耳,
但门框就像焊死了一样,牢牢禁锢着这条通往地狱的走廊。锁舌的位置没有任何异常,
可它就是打不开!“嘻嘻……”又是一声轻笑。不是从角落传来,而是……仿佛就在我耳边。
我浑身汗毛倒竖,猛地回头。走廊依旧空荡,灯光惨白,那些玻璃罐里的婴儿标本,
依然用它们无声的脸庞“注视”着我。角落里的那个娃娃,也依旧保持着那个诡异的笑容。
是幻听吗?是因为极度的恐惧产生的错觉?不对。
我的目光死死盯住离我最近的一个婴儿标本罐。那个浸泡在浑浊福尔马林液体里的小小身躯,
似乎……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不是整体的移动,而是它那只对着我方向、蜷缩着的小手,
食指的指尖,微不可查地抽搐了一丝。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紧接着,
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细微的、粘稠的、仿佛液体被搅动的声音。开始只是一个方向,很快,
就像连锁反应一样,从走廊两侧的每一个玻璃罐里,都传来了类似的、“咕嘟咕嘟”的轻响。
那些婴儿标本,在罐子里……开始动了。它们不再只是僵硬地蜷缩,
而是像从沉睡中被强行唤醒,开始缓慢地、挣扎般地舒展扭曲。小小的四肢抵着玻璃壁,
发出沉闷的刮擦声。模糊的面孔在液体中浮动,偶尔贴近玻璃,露出难以辨识的五官轮廓。
它们想出来。这个认知让我魂飞魄散。我放弃了对防火门的徒劳挣扎,背靠着冰冷铁门,
惊恐万分地扫视着整个走廊。手电筒还紧紧攥在手里,我下意识地把它像武器一样举在胸前,
拇指颤抖着按下了开关。“啪!”一道强光射出,光柱在惨白的整体照明下显得有些微弱,
但依旧清晰地划破了空气。我本能地将光柱扫向走廊尽头的那个娃娃——老刘说过,
用手电照它!光斑精准地打在那个娃娃身上。它依然坐在那里,咧着嘴笑。
但就在光线笼罩住它的瞬间,那尖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童声再次响起,
这次带着一丝明显的不悦和……嘲弄:“光……讨厌……”随着这句话,我清楚地看到,
娃娃那只完好的玻璃眼珠,在强光照射下,反射的光泽似乎闪烁了一下。几乎同时,
走廊里那些玻璃罐中的骚动,骤然加剧了!“咕嘟”声变成了“砰砰”的撞击声,
那些小小的身体更加用力地撞击着坚固的玻璃罐壁,仿佛急于冲破束缚。手电光……没用!
反而激怒了它们?!老刘的信息是错的?还是……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绝望像冰水一样淹没了我。而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我眼角的余光瞥见,
离我最近的那个玻璃罐的金属盖边缘,似乎……松动了一下,渗出了一滴浑浊的液体,
顺着光滑的玻璃壁缓缓滑落。不能待在这里!必须离开这条走廊!
我的目光猛地投向走廊的另一端。那里有电梯,还有通往另一侧楼梯间的门!虽然距离更远,
但这是唯一的生路!求生的欲望压倒了瘫软的恐惧。我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低吼,
迈开如同灌了铅的双腿,沿着走廊疯狂奔跑起来。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被无限放大,
咚咚咚地敲击着我的耳膜和心脏。我不敢回头看,拼命向前冲。两侧的玻璃罐里,
那些蠕动的阴影和持续的撞击声如影随形。我能感觉到无数道冰冷的“目光”钉在我的背上。
快到了!电梯的指示灯在远处闪烁着微光!就在我快要冲到走廊中段的时候——“啪!
”一声轻微的爆裂声。紧接着,是液体汩汩流出的声音。我猛地停下脚步,
惊恐地望向声音来源。是右侧墙壁上一个位置较低的玻璃罐!
它的玻璃壁……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裂纹!
浑浊的、带着刺鼻气味的福尔马林液体正从裂纹中不断渗出,流到地上,
形成一滩迅速扩大的污渍。而透过裂缝,我能看到那个婴儿标本的一只小手,
正死死地卡在裂缝处,皮肤泡得发白起皱,指甲……似乎是黑色的?
“呃……”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强忍着呕吐的欲望。
“咔……咔啦……”令人牙酸的玻璃碎裂声接连响起!不止一个罐子!整条走廊两侧,
如同被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越来越多的玻璃罐开始出现裂纹,甚至彻底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