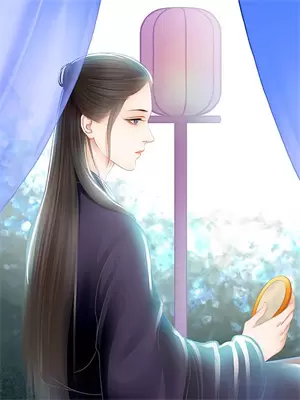雨下得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
不是那种淅淅沥沥、带着诗意的雨,而是狂暴的、混沌的、带着摧毁一切气势的暴雨。沉重的雨点密集地砸在越野车的挡风玻璃上,雨刮器疯了似的左右摇摆,刮开一片清晰视野的下一秒,立刻又被浑浊的雨水彻底糊住,周而复始,徒劳无功。窗外,是浓得化不开的墨色,车灯竭力刺破的有限范围内,只能看见被雨水打得趴伏下去的乱草,和扭曲、光秃的树枝在风中狂舞的影子,更远处,便是一片吞噬一切的虚无。
陈瑾舟双手紧握着方向盘,指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色。他身体前倾,额头几乎要抵到冰凉玻璃上,试图从那一片混沌中分辨出路的痕迹。泥泞的山路在车轮下打滑,传来令人不安的黏腻声响,车身不时轻微地左右晃动,像一艘在惊涛骇浪里挣扎的小船。
“妈的,这鬼天气!”副驾驶座上的夏泽辰低低咒骂了一声,他体格壮硕,此刻却有些烦躁地松了松领口,似乎车内的空气也因为这恶劣的天气而变得凝滞压抑。他不停地摆弄着手机,屏幕的光映亮他线条硬朗、此刻却写满焦灼的脸,“还是没信号!一格都没有!导航从半个小时前就他妈卡在原地不动了!”
后座传来细微的啜泣声,是江晚棠。她蜷缩在角落里,双臂紧紧抱着自己,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坐在她旁边的沈屿哲试图安慰,拍了拍她微微颤抖的肩膀,自己的眉头却也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望向窗外那令人心悸的黑暗,嗓音干涩:“老陈,这么开下去不是办法,油还够吗?而且这路……太危险了。”
陈瑾舟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扫过仪表盘,油量指示已经滑向了红色区域的边缘。危险,他何尝不知道危险?每一次轮胎在泥泞中空转,每一次车身不受控制地侧滑,都让他的心悬到嗓子眼。但他不能停,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停下来意味着什么,他不敢细想。
“再往前开开看,”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强行压抑下的平稳,透出金属般的疲惫质感,“总会找到能避雨的地方。”
坐在他斜后方的慕容令瑶伸出手,轻轻搭在他紧绷的右肩上。她是他妻子,一名心思细腻的心理咨询师,此刻她的指尖冰凉,带着轻微的颤意,但声音却努力维持着镇定:“瑾舟,慢一点,安全最重要。”
她的触碰像是一道细微的电流,短暂地驱散了一些盘踞在陈瑾舟心头的寒意。他嗯了一声,算是回应,目光依旧死死锁定在前方那片被雨幕和黑暗统治的世界。
时间在车轮碾过泥泞的黏滞感中,一分一秒地流逝,缓慢得近乎残酷。希望如同车外的光线,一点点被黑暗蚕食、吞没。车内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只有暴雨永无止境的咆哮和引擎沉闷的呜咽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曲绝望的交响。
就在陈瑾舟几乎要放弃,准备冒险将车停在路边等待天明时,一直紧盯着窗外的慕容令瑶忽然低呼出声:“光!那边有光!”
所有人的精神猛地一振,几乎是同时朝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
在右侧浓密树影的缝隙深处,一点昏黄、微弱的光晕在雨幕中顽强地闪烁着,如同溺水者眼中最后一点求生的星火。
“有救了!”夏泽辰瞬间坐直了身体,声音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狂喜。
陈瑾舟没有犹豫,立刻打转方向,操控着有些不听使唤的越野车,艰难地朝着那点亮光驶去。车轮碾过更加颠簸不平的路面,溅起浑浊的水花。
离得近了,那栋建筑的轮廓逐渐从黑暗中剥离出来。
那是一栋庞大而古旧的建筑,沉默地匍匐在山坳的阴影里,如同一头蛰伏的巨兽。整体的灰白色调在雨水经年累月的冲刷下,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病态的斑驳与污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窗户,绝大多数都黑洞洞地敞开着,或是紧密地关闭着,上面安装着锈迹斑斑、扭曲变形的铁栅栏,像是巨兽口中参差不齐的利齿。建筑的棱角线条呈现出一种早已过时的、笨重而冷硬的设计风格,仅仅是远远看着,就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唯一的光源,来自大门上方悬挂着的一盏老旧的、罩着磨砂玻璃的门灯,那昏黄的光晕在风中摇曳,勉强照亮了下方一块深色的木质招牌。
招牌上,是用深褐色、仿佛干涸血迹般的颜料书写的四个大字——
栖神旅舍。
那字迹带着一种刻意模仿的、扭曲的优雅。
“旅舍?”江晚棠的声音带着哭腔,透出深深的恐惧,“这……这地方看起来……”
她没能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她的未尽之语。这地方看起来根本不像能住人的旅舍,倒更像是……
“总比在车里淋一晚上雨,或者在山里喂野兽强。”夏泽辰打断她,语气强硬,但眼神深处也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迟疑。他率先推开车门,冰冷的雨水夹杂着寒意瞬间涌了进来,让他打了个寒噤。
其他人也陆续下车,冰冷的雨水立刻打湿了头发和衣衫,黏腻地贴在皮肤上,带来刺骨的寒意。他们小跑着冲上几级布满湿滑苔藓的石阶,来到那扇厚重的、漆色剥落的深棕色木门前。
陈瑾舟深吸了一口冰冷潮湿的空气,抬手,叩响了门上的黄铜门环。
沉闷的叩击声在寂静的雨夜里传出老远,仿佛被这栋庞大的建筑吞噬了进去。
几秒钟的等待,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就在陈瑾舟准备再次敲门时,门内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然后是钥匙插入锁孔、缓慢转动时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咔哒”声。
“吱呀——”
厚重的木门被从里面拉开一道缝隙。
一张脸,从门缝后露了出来。
那是一个看起来约莫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身材瘦削,穿着一身熨烫得异常平整、甚至显得有些僵硬的深灰色制服。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油光锃亮。脸上带着一种格式化的、恰到好处的微笑,嘴角上扬的弧度仿佛经过精密计算。
但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浑浊,颜色极淡,像是蒙着一层永远擦不干净的薄翳。它们看着门外的五个落汤鸡,那笑容没有丝毫抵达眼底,反而透出一种冰冷的、审视般的意味,让人联想到爬行动物毫无温度的目光。
“欢迎光临栖神旅舍。”他的声音平滑,语调没有任何起伏,像是一条流淌在平坦河床上的死水,“这样的夜晚,能找到这里,各位客人真是幸运。”
他的目光缓缓从五人惊魂未定、狼狈不堪的脸上扫过,那审视的意味更加明显,嘴角的弧度似乎微妙地加深了一丝。
“请进吧,”他侧身让开通路,动作带着一种刻板的迟缓,“外面的风雨太大了。”
门内透出昏黄的光线和一股混杂着霉味、消毒水以及某种难以名状的、若有若无的甜腻香气的气息。
陈瑾舟迟疑了一瞬,与身旁的慕容令瑶交换了一个眼神,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不安。夏泽辰已经不耐烦地率先挤了进去,沈屿哲扶着瑟瑟发抖的江晚棠紧随其后。
慕容令瑶轻轻拉了拉陈瑾舟的衣袖。
陈瑾舟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那股莫名的不适与寒意,迈步跨过了那道门槛。
就在他踏入旅舍内部的瞬间,身后的老板,用那种平滑无波的语调,轻轻地、仿佛自言自语般地补充了一句,声音不高,却清晰地钻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这里的客人,有些是来玩的……”
他顿了顿,浑浊的目光似乎在他们身上某个看不见的点停留了一瞬,那格式化的微笑纹丝不动。
“……有些,是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