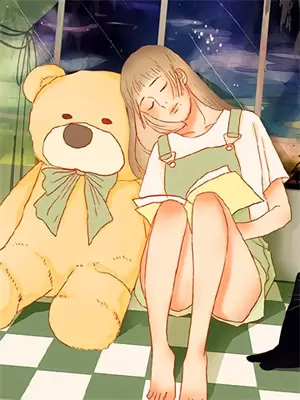
简介:暴雨将至时,我和村花玉娥在山上采野菌。一阵妖风突然掀起她火红的裙摆,
露出白皙双腿。我慌忙移开视线,她却死死抓住我的手:“阿诚,你得娶我。
”第二天全村都传遍我轻薄了玉娥,村长带人堵在我家门口。“要么娶玉娥,要么打断腿!
”村长眼神阴鸷。玉娥突然扑通跪在众人面前:“求你们别逼阿诚哥!”我被锁进柴房那晚,
窗缝塞进一张带血的布条:“别喝菌汤。”第七天警车开进村,村长全家中毒身亡。
玉娥站在警车旁对我笑:“那些毒菌子,是我特意采的。”十年后我成了菌类专家,
在集市遇见玉娥。她指着当年那片山:“那阵风,是我最后的求救信号。”天空又飘起细雨,
我脱下外套披在她肩上:“这次换我主动负责。”---正文:暴雨欲来的闷热,
沉甸甸地压在青牛山浓稠的绿意上。空气像一块吸饱了水、来不及拧干的旧布,紧紧裹着人,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泥土和腐烂落叶蒸腾出的腥气。我,十六岁的阿诚,
背着个磨得发亮的旧竹篓,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玉娥身后。玉娥是青牛村公认的村花,
人如其名,玉般温润,娥眉秀目。她今天穿了件簇新的火红裙子,
是村长爹托人从山外捎来的料子做的,在满山沉郁的绿里,像一团跳跃的、不安分的火焰,
灼人眼目。她纤细的身影灵活地在密匝匝的林木间穿行,裙裾拂过湿漉漉的蕨草,
留下细微的沙沙声。“阿诚哥,快点儿呀!”她回过头,声音脆生生的,
带着少女特有的娇憨,“再磨蹭,好菌子都被露水打烂了,雨也要下来了!
”我胡乱应了一声,赶紧埋头看路,不敢多看那张在晦暗光线下依旧明艳的脸。
心口像揣了只不听话的兔子,扑通扑通撞得肋骨生疼。玉娥是村长的独生女,
是村里小伙子们夜里做梦都不敢轻易梦见的存在。能和她一起上山捡菌子,
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好运,此刻却紧张得手心冒汗。山势渐陡,林木愈发幽深。
浓密的树冠遮天蔽日,光线被筛成破碎的、摇曳的光斑,投在铺满厚厚腐殖层的地上。
空气里的腥气更浓了,混合着某种菌类特有的、若有似无的甜香。
玉娥似乎对这片林子格外熟悉,她不再催促我,而是微微躬着腰,
目光专注地扫过树根、苔藓覆盖的岩石缝隙,寻找着那些藏在腐叶下的山珍。
她的动作异常轻巧,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我学着她的样子,也努力在潮湿的落叶堆里翻找。
红菇、牛肝菌、鸡油菌……偶尔能捡到一两个品相不错的,小心地放进竹篓里。
但更多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总是不自觉地溜向那抹跳跃的红色。
玉娥的篓子似乎比我的沉一些。我看见她蹲在一棵巨大的、根系虬结的老榕树下,
裙摆铺开在深褐色的泥土上,像一朵盛开的红花。她小心地拨开一层厚厚的、湿漉漉的落叶,
露出下面几朵颜色异常艳丽、伞盖饱满的菌子。那菌子红得近乎妖异,
伞盖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色斑块,在幽暗的光线下,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玉娥,
这……”我忍不住出声提醒,总觉得那菌子看着不太对劲,村里老人常念叨,
越是好看的蘑菇越碰不得。她飞快地回头瞥了我一眼,眼神有些飘忽,
嘴角却弯起一个浅浅的、意味不明的弧度。“没事的,阿诚哥。”她声音很轻,
带着一种奇异的笃定,“我认得。这是……好东西。”说着,她白皙的手指灵巧地探下去,
小心翼翼地将那几朵艳丽得刺眼的菌子连根拔起,轻轻放进自己的背篓深处,
还用几片宽大的树叶仔细盖好。就在她直起身的刹那,异变陡生!
头顶密不透风的树冠猛地一阵剧烈摇晃,发出海啸般的哗啦巨响。
一股极其猛烈、毫无征兆的妖风,如同从地底深渊喷涌而出,带着刺骨的寒意,自下而上,
狂野地席卷过我们脚下的山坡!“啊——!”玉娥短促的惊呼被狂风撕碎。
那团炽烈的红色火焰——她的新裙子——被这股邪风猛地向上掀起、翻卷!
火红的布料像一面失控的旗帜,呼啦啦地向上飞扬,
瞬间露出了下面两条光洁、白皙得晃眼的小腿,甚至更高……我脑子“嗡”的一声,
全身的血仿佛瞬间冲上了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巨大的羞窘和恐慌攫住了我,
像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心脏。我几乎是本能地、猛地扭过头去,死死闭上了眼睛,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震得耳膜嗡嗡作响。山风来得快,去得更快。
那股彻骨的寒意和喧嚣如同幻觉般骤然消散,只留下满山死寂的绿和更沉重的闷热。
林中只剩下枝叶被摧残后的余悸,发出细微的、痛苦的呻吟。我僵硬地站着,
背对着玉娥的方向,汗水沿着鬓角滑落,脊梁骨一阵阵发凉。
耳朵里全是自己粗重得吓人的喘息声。完了,闯大祸了!轻薄村长的女儿,
这罪名……我几乎不敢想下去。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阿诚哥……”身后传来玉娥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却又异常清晰,
像冰凌碎裂在寂静的山谷。我浑身一僵,艰难地、一寸寸地转过身。
眼睛只敢盯着她脚下的泥土。她站在几步之外,那身火红的裙子已经服帖地垂落下来,
遮掩住了一切。她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看不清表情。
一只手紧紧攥着裙摆的布料,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另一只手,却微微抬着,
指尖似乎还残留着刚才采菌时沾上的湿润泥土。空气凝固得如同铅块。突然,她猛地抬起头!
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杏眼,此刻却像是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幽暗、冰冷,
里面翻涌着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极其复杂的情绪——有屈辱,有决绝,
甚至……还有一丝疯狂的、孤注一掷的光芒?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她动了。不是后退,
也不是掩面哭泣,而是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小兽,猛地朝我冲了过来!带着一股决绝的狠劲。
我惊得下意识想后退,脚却像被钉在了原地。冰凉、带着泥土腥气和微微汗湿的手指,
像铁钳一样,死死地、不容抗拒地抓住了我的手腕!那力道大得惊人,捏得我骨头生疼。
我愕然抬头,撞进她近在咫尺的眼瞳里。那里面燃烧的火焰,比她的红裙更加炽烈,
更加……绝望。“阿诚哥,”她的声音压得极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
带着一种奇异的、冰冷的重量,狠狠砸进我的耳朵里,“你看到了……你看到了,对不对?
”我喉咙发干,舌头像是打了结,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呃……啊……”声,
巨大的恐惧让我浑身发冷。她抓着我的手猛地收紧,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皮肉里,
那双眼睛死死锁住我,里面的光疯狂跳跃:“你得娶我!”这句话,像一道惊雷,
毫无预兆地在我头顶炸开!“轰隆——!”几乎是同时,酝酿已久的暴雨终于倾盆而下。
豆大的雨点砸在树叶上、泥土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噼啪声,
瞬间将我们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水汽之中。冰冷的雨水浇头盖脸,
却丝毫浇不灭我心底那骤然升起的、刺骨的寒意。娶她?村长王德贵的女儿?
那个在青牛村说一不二、手段狠辣的土皇帝的掌上明珠?
手腕上的剧痛和玉娥眼中那孤注一掷的疯狂,让我如坠冰窟,四肢百骸都冻僵了。
雨水顺着额发流进眼睛,又涩又痛,模糊了玉娥近在咫尺的脸,
却模糊不了她眼中那份令人心悸的决绝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求?“我……”我试图开口,
声音被滂沱的雨声彻底吞没。玉娥的手像烧红的烙铁,死死箍着我的腕子,
指甲几乎要抠进皮肉里。她不再说话,只是用那双燃烧着复杂火焰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仿佛要把我的灵魂都吸进去,烙印上她的印记。雨水冲刷着她苍白的脸颊,汇聚成小溪,
沿着她紧绷的下颌线滑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走!”她猛地低吼一声,
声音被雨幕切割得支离破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她不再看我,拽着我的胳膊,
以一种近乎粗暴的力道,拖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冲下山坡。泥泞湿滑的山路在脚下打滑,
好几次我都差点摔倒,全靠她那只冰冷铁钳般的手死死拽着才没滚下去。
竹篓里的菌子颠簸着,撞在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路沉默,
只有震耳欲聋的雨声和粗重的喘息。雨水模糊了视线,也模糊了思绪。
玉娥那声“你得娶我”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反复轰鸣。恐惧像冰冷的藤蔓,
从脚底缠绕上来,勒得我喘不过气。村长王德贵那张阴鸷刻薄的脸在我眼前晃动,
他护短是出了名的,更何况是他视若珍宝的独女?
他那些对付“不听话”村民的手段……我打了个寒颤,不敢再想下去。回到村口时,
天已黑透,只有几户人家透出昏黄的灯火,在雨幕中摇曳。玉娥终于松开了手。她站在雨里,
浑身湿透,红色的裙子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单薄而倔强的轮廓。她没再看我,只是低着头,
用极快的、几乎带着逃难意味的速度,
朝着村子东头那座最高、最气派的青砖大瓦房——她家的方向跑去,很快消失在雨幕深处。
我失魂落魄地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冰冷的雨水顺着脖子灌进衣领,冻得我牙齿咯咯打颤。
手腕上被玉娥抓过的地方,留下几道清晰的、深紫色的指痕,火辣辣地疼。心,
却沉到了无底深渊。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一夜,
我在家里那张吱呀作响的破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屋外的雨声敲打着瓦片,
像无数只冰冷的手在叩击我的心门。玉娥幽深的眼,村长阴鸷的脸,还有那句“你得娶我”,
在黑暗中反复交织、放大。恐惧像毒蛇,噬咬着我的神经。迷迷糊糊间,几次被噩梦惊醒,
冷汗浸透了单薄的被褥。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而粗暴的拍门声,
像重锤一样砸碎了清晨的寂静,也彻底砸碎了我最后一丝侥幸。“阿诚!滚出来!小兔崽子,
滚出来!”门外是几个粗野的男声,混杂着愤怒的咆哮。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
心脏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手脚冰凉,胡乱套上衣服,哆哆嗦嗦地拉开了门闩。门外,
黑压压地站了七八个人,都是村里的青壮,平日里跟着村长跑腿的。
为首的是村里的会计王癞子,一脸横肉,眼神凶狠。他们堵在门口,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
清晨微凉的空气瞬间被他们的怒气熏得灼热。“就是他!就是他这个不要脸的畜生!
昨天在山上,欺负了玉娥妹子!”王癞子指着我,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呸!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村长家的闺女你也敢动?活腻歪了!
”“打断他的狗腿!”污言秽语如同冰雹,劈头盖脸地砸过来。我眼前发黑,
耳朵里嗡嗡作响,想辩解,喉咙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半点声音。
巨大的恐慌和屈辱让我浑身筛糠般抖个不停。完了,玉娥……她真的……“让开!
”一声低沉的、极具威压的喝斥从人群后面传来。堵在门口的人群如同被劈开的潮水,
刷地一下向两边分开,露出后面的人。村长王德贵。他穿着一身浆洗得发硬的靛蓝色旧褂子,
背着手,一步一步地踱了过来。他个子不高,精瘦,脸上没什么肉,颧骨突出,
一张脸像是用刀削出来的,线条冷硬。眼睛不大,微微眯着,
里面没有村民常见的愤怒和暴躁,只有一种深潭般的阴冷和沉静,像毒蛇盯住猎物时的凝视。
他走到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停下,目光像两把冰冷的锥子,直直地钉在我脸上。
周遭瞬间安静下来,连那些叫嚣的青壮都噤了声,只余下压抑的喘息。王德贵没说话,
只是看着我。那目光像是带着实质的重量,压得我脊梁骨嘎吱作响,几乎要当场跪下去。
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的衣衫。几秒钟的死寂,漫长得像一个世纪。终于,他开口了,
声音不高,却像带着冰碴子,清晰地钻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也狠狠刺进我的心脏:“阿诚小子,”他嘴角似乎扯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却比哭更瘆人,
“两条路,你自己选。要么,风风光光地娶了我家玉娥进门,给我当女婿。
要么……”他顿了顿,那双阴鸷的眼睛扫过我的腿,冰冷的语气没有一丝波澜,
却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要么,就留下你这两条腿,以后爬着走。”“轰”的一声,
我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眼前一阵发黑,天旋地转。娶玉娥?当村长的女婿?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留下腿……我看着王德贵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毫不怀疑他真的会说到做到!巨大的恐惧和荒谬感让我浑身冰冷,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
腿软得几乎支撑不住身体。就在这时——“爹!
”一个带着哭腔的、尖利的女声猛地刺破了凝重的气氛。是玉娥!
她不知何时从家里冲了出来,头发有些散乱,脸色苍白得像纸,眼睛红肿,显然哭过。
她跌跌撞撞地拨开人群,像一只扑火的飞蛾,不管不顾地冲到王德贵和我之间。“爹!
别逼他!”她嘶声喊道,声音因为激动而变调,带着绝望的哭腔,“不关阿诚哥的事!
是……是我自己……是风……”她语无伦次,泪水汹涌而出,混着脸上的雨水未干的痕迹。
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她爹王德贵。
他那张阴沉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眉头狠狠拧了起来。“玉娥!你胡闹什么!
给我滚回去!”王德贵厉声呵斥。玉娥却像没听见,她猛地转过身,面对着所有堵门的村民,
眼神扫过一张张或愤怒、或鄙夷、或看热闹的脸。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
她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动作!“扑通!”她竟然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双膝重重地砸在门口冰冷的泥地上。“求求你们!”她抬起头,泪水在苍白的脸上纵横,
声音凄厉而绝望,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哀求,“求求你们别逼阿诚哥!是我……都是我不好!
求你们放过他吧!”她一遍遍地磕着头,额头重重地撞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那身簇新的红裙子沾满了泥污,狼狈不堪。她瘦弱的肩膀在清晨的寒气中剧烈地颤抖着,
像狂风暴雨中即将折断的芦苇。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震惊了所有人!整个场面死寂一片,
只剩下玉娥额头撞击地面的闷响和她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村民们都呆住了,
面面相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困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动摇。王德贵的脸,
瞬间变得铁青!额角青筋暴跳,眼神阴鸷得能滴出水来。
他死死盯着跪在地上、卑微到尘埃里的女儿,那眼神,不再是愤怒,
而是一种被彻底背叛和羞辱后的、火山爆发前的恐怖死寂。“好!好!好!
”他连说了三个“好”字,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冰渣子,带着蚀骨的寒意。
他不再看玉娥,那双淬了毒似的眼睛猛地转向我,里面的杀意几乎凝成实质。“阿诚小子,
”他的声音反而平静了下来,却比刚才的咆哮更令人胆寒,“你本事不小啊!
把我女儿迷得五迷三道,连脸都不要了!”他猛地一挥手,指向旁边一间低矮破旧的柴房,
那是我们家堆放杂物的地方,门板歪斜,里面堆满了柴草和农具。“把他给我关进去!
”王德贵的声音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裁决,“没我的话,谁也不准放他出来!
一粒米、一口水都不准给!我倒要看看,是这小畜生的骨头硬,还是我王德贵的规矩硬!
”王癞子等人立刻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粗暴地扭住我的胳膊,
不顾我的挣扎和玉娥撕心裂肺的哭喊“爹!不要!”,
像拖死狗一样把我拖向那间散发着霉味和腐朽气息的柴房。“砰!
”沉重的、带着铁链的门板在我身后被狠狠摔上、闩死!
巨大的声响震得柴房顶簌簌落下灰尘。最后一丝天光被隔绝,
眼前瞬间陷入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搡倒在地,
摔在冰冷坚硬、布满柴草碎屑的泥地上。手肘和膝盖传来火辣辣的疼痛,
但比起心头的绝望和恐惧,这点痛楚微不足道。黑暗像浓稠的墨汁,瞬间将我吞噬。
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浓重的霉味、尘土味和腐烂木头的味道,呛得人喘不过气。外面,
玉娥凄厉的哭喊声和王德贵暴怒的呵斥声隐约传来,渐渐远去,最终被死一般的寂静取代。
我被彻底抛弃在了黑暗里。时间在绝对的黑暗中失去了意义。
恐惧、寒冷、饥饿、还有对未来的绝望,如同无数只冰冷的蚂蚁,啃噬着我的意志。
王德贵那句“一粒米、一口水都不准给”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我。他真的要活活饿死我?
还是打断我的腿?玉娥……她怎么样了?她爹会不会迁怒于她?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是为了救我?还是……无数个念头在昏沉的脑海里翻滚、碰撞,头痛欲裂。
我蜷缩在冰冷的角落,背靠着粗糙扎人的柴草堆,
听着自己粗重而绝望的呼吸声在死寂中回响。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天,也许只有半天,
饥饿感如同烧红的铁钳,开始搅动我的肠胃,带来一阵阵抽搐的绞痛。喉咙干得冒烟,
像被砂纸磨过。就在我意识开始模糊,
几乎要被这无边的黑暗和绝望彻底吞没的时候——极其细微的声响!不是老鼠,也不是风声。
是柴房那扇歪斜、破旧的门板最下方,靠近地面的地方,
传来一阵极其轻微的、悉悉索索的刮擦声。那里有道很宽的缝隙,是门板变形留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