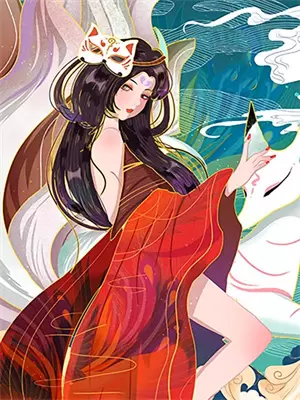天色是铅灰色的,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旧棉絮,沉甸甸地压下来,闷得人心里发慌。
昨天是我三十六岁生日,府里摆了宴,庆贺丈夫沈敬言晋升户部侍郎。宾客闹到半夜才散,
偌大的沈府静下来,我一个人在后厨,把堆成山的碗碟洗出来。腰像是折了,我拿手捶着,
扶住冰冷的灶台,把一双泡得发白,满是口子的手伸进冷水里。
那股凉意顺着指尖钻进骨头缝,我打了个激灵,人也清醒了些。二十年了。
我本是江南绣坊的一个绣娘,跟着还是个穷书生的沈敬言,一路从水乡到了这京城。
我当了陪嫁的首饰,凑钱给他打点关系;我熬红了眼给他浆洗衣裳,
好让他体体面面地去见那些大人。我陪着他,从一间漏雨的破屋,
住进了今天这座朱漆大门的府邸。我总想着,苦日子到头了,好日子,该来了吧。“苏绣!
你给我滚出来!”婆婆的声音又尖又细,像一根烧红的铁签子,一下子扎破了这深夜的寂静。
我不敢慢,胡乱在身上擦了擦手,小跑着去了前厅。前厅的灯还亮着,
把那些名贵的紫檀木家具照得油光水滑,地上的波斯地毯,软得能把人陷进去。这一切,
都和我身上这件洗得看不出本色的旧袄子格格不入。沈敬言直挺挺地跪在地上,我婆婆,
沈老夫人,坐在太师椅上,一张脸拉得老长,拿眼刀子剜我。“母亲。”我低下头,
小声叫她。“我担不起你这声母亲!我沈家没你这么个上不得台面的媳妇!
”她把手里的茶杯往桌上“咚”地一放,滚烫的茶水溅出来。
“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今天在宴席上的那副穷酸样!相国夫人不过是跟你拉句家常,
你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利索!我沈家的脸,都被你这个商贾出身的女人丢尽了!
”我把手攥得死紧,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的老茧里。我不是紧张,我是累。为了这场宴席,
从买菜备菜到收拾残局,我三天没怎么合眼,哪里还有精神头去应付那些贵夫人们。
可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说。说了也没用,没人信,也没人在乎。“敬言,
”婆婆看都懒得再看我,对着她儿子说,“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堂堂户部侍郎,
往后的前程好着呢!这么个女人,只会拖你的后腿!”沈敬言还跪着,头埋得很低,
声音闷闷的,听着倒像是有几分不忍心:“母亲,绣娘她……跟了我这么多年,
没功劳也有苦劳……”“苦劳?”婆婆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冷笑一声,
“她占着我们沈家主母的位置二十年,连个蛋都下不出来,这算哪门子的苦劳?七出之条里,
光‘无子’这一条,就够我把她休了!”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原来,
这才是她真正想说的。婆婆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甩在沈敬言面前。
“休书我早就叫人写好了,你签个字,按个手印,明儿一早就让她滚蛋!
相国府的赵小姐早就递了话,只要你这边利索了,她立马就嫁过来。
有相国大人给你当老丈人,你还怕官做不大吗?”那张纸,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却像一块千斤巨石,把我这二十年来的苦熬和指望,全压碎了。我看着沈敬言,
看着这个我爱了半辈子,也扶了半辈子的男人。他终于抬起头,看向我,眼睛里有泪,
脸上全是难受和舍不得。可我知道,他不是为我难受,
他是为他自己马上要背上“抛弃糟糠之妻”的坏名声而难受。他的痛苦,他的挣扎,
全是为了他自己。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就静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辛酸,好像一下子都散了。
我累了。真的累了。不等沈敬言开口,我慢慢走过去,弯腰捡起了那封休书。“别为难了。
”我的声音很轻,屋里的人却都愣住了。我看着沈敬言,一字一句,
说得清清楚楚:“沈敬言,这二十年,我给你操持这个家,伺候你母亲,
让你安心在外头奔前程。我没后悔过。但从今天起,你和我,再没关系了。”我没哭,
也没闹。我只是把那封休书小心地叠好,放进怀里,好像那不是一纸羞辱,
而是我下半辈子安身立命的凭据。然后,我转过身,挺直了那根酸疼了半辈子的腰杆,
一步一步,走出了这座我亲手建起来,却再也不属于我的牢笼。门外,
冷雨“噼噼啪啪”地打在青石板上,也打湿了我的脸。
第二章:绝处逢生从沈家大门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就一件单衣,怀里揣着那封休书。
管家大概是得了婆婆的吩咐,从门缝里扔出个小荷包,砸在地上,发出几声闷响。我捡起来,
里面是几两碎银子。二十年的夫妻情分,到头来,还不如打发一个要饭的。
我不敢回苏州老家。爹娘年纪都大了,当年我嫁进沈家,他们逢人就说我有了依靠,
后半辈子不用愁了。如今我这个样子回去,不是往他们心上捅刀子吗?我不能再拖累他们。
我在京城最南边的瓦市,找了个三教九流混住的地方,花光了身上大半的银钱,
租了间勉强能挡风雨的小破屋。一推开门,一股子烂木头混着潮气的霉味就扑面而来,
墙角挂着灰扑扑的蜘蛛网。屋顶破了个洞,晚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冷风一吹,
那破窗户就“吱呀吱呀”地响,好像随时要散架。夜里冷得厉害,我只能抱紧胳膊缩在墙角,
身上这点布料根本不顶用,那寒气跟针扎似的,一个劲儿往骨头里钻。肚子空得咕咕叫,
可心里的冷,比身上的冷要难熬一万倍。我一闭上眼,眼前就晃过沈家那烧着地龙的卧房,
还有那又软又暖和的被子。真是可笑,就算睡在那样的床上,我这心里,
又何曾真正暖和过一天?人到了绝路上,脑子就容易犯浑。我想,就这么死了,
是不是就什么都不用愁了?不用再挨饿受冻,也不用再看人脸色了。就在这时候,
我的手碰到了包裹里一个硬邦邦的方盒子。那是我离开沈家时,
唯一从自己屋里带出来的东西,
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一个装满了各色绣线的旧木匣子。我哆哆嗦嗦地把它打开。
一排排的丝线,红的、绿的、黄的、紫的……整整齐齐地躺在里头,
在从房顶漏下来的那点月光下,泛着一层柔光,好像睡了二十年的一个梦。
我从匣子里摸出那枚戴了多年的顶针,冰凉的铁疙瘩硌在指尖,却让我的心狠狠地跳了一下。
我想起了我娘。她曾是苏州城里手艺最好的绣娘,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
上气不接下气地跟我说:“绣儿,你记着,女人的手,不光能给男人洗衣做饭,
也能给自己挣出一片天。这世上,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双手实在。”那时候,
我正想着要嫁给沈敬言,要做他的好媳妇,压根没把这话听进去。我以为,
我找到了能靠一辈子的男人。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真是傻得可怜。我拿起一根绣花针,
针尖还亮着,没生锈。这二十年,我这双手,和过面,搓过山一样的衣服,掌过勺,
伺候过一大家子,就是再没碰过这根针。我差点都忘了,在被人叫“沈夫人”之前,
我的名字,叫苏绣。我是苏州绣坊里,最有灵气的那个姑娘。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涌上眼眶,
说不清是委屈,还是不甘心。我凭什么要认命?我凭什么就要像条没人要的狗一样,
死在这臭水沟里?沈敬言,还有沈家的那些人,他们都以为我苏绣离了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我偏要活下去。不但要活,我还要活得比在沈家的时候,更体面,更舒坦!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干柴见了火星子,一下子就在我心里烧了起来。我胡乱抹了把脸,
把那个匣子死死抱在怀里,像是抱住了我的命。第二天,天刚麻麻亮,
我就拿着身上最后那几十个铜板,去集市上扯了最便宜的粗棉布,又买了最普通的几束绣线。
卖布的大婶看我穿得单薄,人也实在,还好心多裁了一尺给我。回到那间破屋,
我把布铺在唯一的烂桌上,就着从房顶漏下来的那点天光,穿针,引线。二十年没碰了,
手都生了。可当第一针扎下去,再拉起来的时候,我的心,忽然就定了。
屋外是乱糟糟的叫卖声,屋里,就只有我和这一方小小的绣布。
我不知道这块布能绣出个什么花样,不知道能卖几个钱,更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儿。
但我清楚,从我重新拿起这根针的这一刻起,我苏绣的命,就攥回了自己手里。
就算吃不饱饭,就算前头没路,我也要一针一针地,给自己绣出一条活路来。
第三章:锦绣合盟城南的瓦市,是京城里最挤、最乱、也最活泛的地方。
我找了个没人要的墙角,铺开一块洗得发白的旧蓝布,
把我熬了好几个晚上绣出来的几方帕子,小心翼翼地摆好。帕子上的花样都是我自己想的,
不像外头卖的那么大红大绿,我只在帕子角上,拿细细的丝线绣一枝小小的迎春花,
或是一只翅膀正要扇动的蝴蝶。针脚细密,颜色也清清淡淡的。我心里想着,东西好,
总会有人识货。可一整天下来,太阳都快下山了,问的人不少,可一听一方帕子要三十文钱,
都摇着头走了,扭头就去旁边摊子上买那些针脚粗得能跑马,花样俗气却只卖十文钱的。
我心里头刚燃起的那点火苗,像是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冷水,凉透了。眼看着天色暗下来,
我正准备收摊,一个清清冷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这绣法,是苏绣里的‘平针走绣’,
可针脚里又带着乱针绣的影子,倒是巧得很。”我猛地抬起头,看到一个瘦瘦的女人。
她穿着一身素净的长裙,裙子洗得旧了,上面还有个小补丁,但补得很整齐,人也站得笔直,
不像这市井里的人。看年纪跟我差不多,但那眼神,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精明。
“姑娘……好眼力。”我心里一惊,没想到在这地方还有人能说出这种门道。
她拿起一方绣着兰草的帕子,用指尖细细地摩挲着,又问:“卖得不好吧?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点了点头。她笑了笑,那笑里好像什么都明白:“东西是好东西,
可惜,地方卖错了,价钱也定错了。”她抬手指了指周围吵吵嚷嚷的人,“来这儿的人,
图的是便宜,能用就行,你这点精细功夫,他们看不懂,也舍不得花这个钱。你这手艺,
该卖给那些官家小姐,富家太太,一方帕子,就是卖三百文,她们也抢着要。”我听了,
只能苦笑:“我现在这个样子,哪有门路认识那些贵人。”她看着我,
眼里闪过一丝说不清的滋味,刚想再说什么,旁边突然传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臭娘们!
这个月的地租该交了!”三个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的地痞围了上来,领头的那个独眼龙,
一脚就踹在我的摊子上,那几方我当宝贝似的白帕子,一下子就掉进了泥水里。
我吓得往后一缩,脸都白了。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高大的影子猛地冲了过来,
一把就将那独眼龙推了个趔趄。“大白天的,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我定睛一看,
是个穿粗布短打的妇人,手脚粗壮,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一双眼睛却亮得吓人。
她手里还提着个麻袋,看样子是刚从码头扛活回来。“张阿莲?你少管闲事!
”那独眼龙认出了她,嘴上横,脚下却有点虚。那叫张阿莲的妇人把麻袋往地上一扔,
两手往腰上一叉,冷笑一声:“老娘今天就管定了!有本事冲我来,
别在这欺负一个没力气还手的姐妹!”她那股泼辣劲儿,竟真把那三个地痞给镇住了。
他们看讨不到便宜,只敢在嘴上骂骂咧咧地走了。我赶紧跟她道谢,
她却满不在乎地一摆手:“谢啥!咱们女人家,在外头不容易,就该拉一把!”话音刚落,
天说变就变,豆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就砸了下来。集市上的人“哄”地一下就乱了,
我们三个也被浇了个透心凉。我急得大喊:“快!到我屋里躲躲雨!”我那间破屋子,
头一次有了客人。雨下得跟瓢泼似的,屋顶的破洞往下漏水,
我们只能挤在不漏雨的那个墙角。我找出米缸里最后剩下的一点米,
熬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又摸出几根咸菜。三个人就着一盏快要灭了的油灯,
捧着热乎乎的粥碗,身上总算有了点暖气。屋外是哗哗的雨声,屋里,三个人谁也没说话。
最后,还是那个叫陆晚晴的瘦弱女子先开了口,她看着我,轻声问:“看姐姐的样子,
不像是一直过这种苦日子的人。”也许是这碗热粥暖了心,也许是大家都是女人,我没瞒着,
把被沈家赶出来的事,一五一十地都说了。我说完,张阿莲“啪”地一拍大腿,
狠狠地骂道:“那个沈侍郎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天底下的男人,就没几个好东西!
我那个死鬼男人也是,喝了酒就拿我撒气,上个月他弟弟喝多了想对我动手动脚,
我抄起扁担打断了他的腿,就被他们一家子赶了出来!”陆晚晴听着,眼圈也红了。
她放下碗,声音发着抖:“我……我也是和离出来的。他为了个小妾,天天给我没脸,
我实在受不了,就自己求了休书。我爹说我丢尽了读书人的脸,把我赶出家门,
一个铜板都没给我。”原来,我们都是被男人抛弃的女人。一个,是给家里当牛做马半辈子,
老了,生不出儿子,就被一脚踹开的糟糠妻。一个,是为了脸面,不愿跟小人低头,
自己选择离开的读书人小姐。一个,是为了不被人欺负,奋起反抗,
却被当成泼妇赶出家门的苦命人。我们的命不一样,可那份被人当成破烂一样扔掉的疼,
却是一样的。那一刻,我们看着对方,就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我们不能就这么认命!
”陆晚晴忽然开口,她的眼睛里像是烧起了两团火。她看看我,又看看张阿莲,
一字一句地说:“苏绣姐姐,你有这满京城都找不出的好手艺;阿莲大姐,
你有这一身力气和胆量,没人敢欺负我们;我呢,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可也读过几年书,
在那些大户人家里见过些眉眼高低,懂得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算账。”她深吸一口气,
声音更坚定了:“我们三个,为什么不能合在一起,自己干出一番事业?就开一间绣坊,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锦绣阁’!”“锦绣阁……”我跟着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敲了一下。“对!”陆晚晴的眼睛越来越亮,“你来当师傅,出绣品,
也教那些跟我们一样没地方去的苦命姐妹一门手艺;我来当掌柜的,管账,
跑门路;阿莲大姐,你就给我们看家护院,保我们锦绣阁上上下下的平安!”窗外的雨声,
好像小了点。这破屋子里,我们三个女人的心,却被这几句话烧得滚烫。
我看着陆晚晴那双透着精光的眼睛,又看看张阿莲那双能扛起麻袋的胳膊,再低下头,
看看自己这双还能穿针引线的手。是啊,我们为什么不能靠自己?我端起碗,
把剩下的一口热粥喝干净,像是喝下了一股力气。然后,我抬起头,重重地点了下去:“好!
就叫锦绣阁!”第四章:挣来的热包子我们盘下了城南那间最便宜的铺子,小得可怜,
但好歹有个顶。陆晚晴花钱请了个老秀才,写了块“锦绣阁”的牌匾。挂上去那天,
没放鞭炮,也没人来道贺,就我们三个,还有张阿莲从犄角旮旯里捡回来的五个和我们一样,
没地方去的苦命女人。铺子前面卖东西,后面连着个小院子,就是我们八个人的家。白天,
这里是干活的绣坊;到了晚上,我们在两间大通铺上挤着睡,耳边是旁边人轻轻的呼吸声,
这心里头,竟有了多少年没感受过的安稳。来的姐妹们,大多是苦出身,别说摸过绣花针,
有几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要是按我以前在绣坊学艺那套教法,没个三年五载,
根本出不了师。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姐妹们得吃饭,得活命。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
饭都顾不上吃,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我娘教过的那些针法。我把那些复杂的绣法,
什么双面绣、乱针绣,全拆开来,琢磨里头的门道,
再跟村里妇人纳鞋底、缝衣服用的最简单的平针法揉在一起,在破布头上试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还真让我琢磨出了一套新绣法。我管它叫“家常绣法”。针脚简单,学起来快,
绣出来的花样,虽然比不上那些给贵人做的贡品那么精细,可也活灵活现的,有股子新鲜气。
最要紧的是,出活快,手脚麻利点的,三五天就能绣好一方帕子。我手把手地教她们,
从怎么穿针引线,到怎么把绣布绷平不起皱。有个叫小草的姑娘,才十四岁,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爹要把她卖去窑子里换钱,被张阿莲半道上拦下来救了。她手最笨,
学得也最慢,急得直掉金豆子。我就拉着她的手,带着她一针一针地走,跟她说:“别怕,
绣错一针,拆了重来就是了。人活一辈子,哪有不走错路的时候?只要这双手还在,这日子,
就总有盼头。”陆晚晴也没闲着。她把我们绣出来的帕子、荷包、扇套,分成三等。
最普通的,卖给街坊邻居,结实好看;稍好一点的,卖给那些小门小户的姑娘,
攒着当嫁妆;最好的,就由我亲自动手,花样也更精巧些,专卖给那些识货,不差钱的客人。
她还想出个“定做”的法子。谁家有喜事,可以来我们这儿定做绣品,
比如给新嫁娘的荷包上,绣上夫妻俩的名字;给刚满月的娃娃做的小肚兜上,
绣个长命锁的图样。这在当时的京城,可是头一份的新鲜事。慢慢地,锦绣阁在城南这块儿,
还真有了点小名气。来光顾的,大多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女人。她们喜欢我们这儿的东西,
更喜欢我们这儿的人气。有时候,买完东西也不走,就坐在我们铺子门口,一边帮着择菜,
一边聊几句自家的难心事。在这里,她们不用看男人和婆婆的脸色,
能踏踏实实地喘口舒心气。一个月后,陆晚晴把账本放在我们面前,她拨着算盘珠子,
那“噼里啪啦”的声音,比唱戏还动听。最后,她停下来,抬起头,
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这个月,刨去咱们的吃穿用度和买布买线的本钱,
我们……我们净赚了二两银子!”屋里一下子就静了,随即“轰”的一声,炸开了一片欢呼。
小草抱着我,又哭又笑,把眼泪鼻涕全蹭我身上了。我攥着那二两碎银子,手都在抖。
在沈家二十年,我管着家里的账,手里过的银子成百上千,可没有一个铜板是真正归我的。
而这二两银子,每一个铜板,都带着我们自己的汗水,干干净净,揣在怀里,心里踏实!
我拿着钱,想都没想,就冲到街对面的包子铺,把人家刚出笼的肉包子,全给包圆了。
那天晚上,我们八个人,就在院子里,围着那张破桌子,就着月光,吃着热气腾腾的肉包子。
白面皮,肉馅儿足,一口咬下去,油都顺着嘴角往下流。姐妹们吃得狼吞虎咽,
一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那是我从没见过,打从心底里透出来的笑。我吃着包子,
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想起在沈家的日子,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可每一口饭,
都吃得提心吊胆,都得看人家的脸色。哪有今天这个肉包子香?哪有今天这样,
想怎么笑就怎么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用自己双手挣来的热饭,才是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