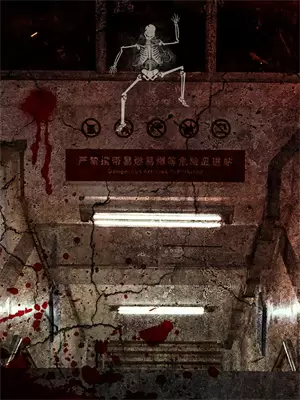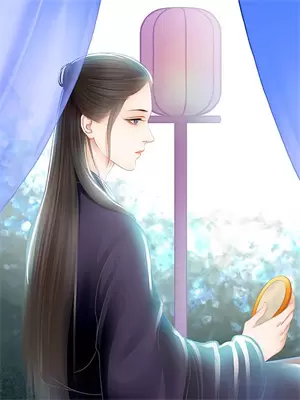我们总以为黑暗是绝对的,是光的缺席。但在那个名叫“烛阴”的县城,老人们会说,
黑暗是有质感的,有时甚至是温润的、粘稠的,带着一种……被精心炼制过的气息。
因为那里,曾流传着一种以人脂为烛的古老秘术,烛光所及,照见的并非光明,
而是深不见底的人心幽暗。莫小羽收到那封匿名信时,
窗外正下着这个滨海城市罕见的、带着土腥气的细雨。信纸粗糙泛黄,
像是从某个陈年账簿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墨水洇开,
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甜腻又腐败的怪味:“烛阴县,永寿街73号,他们在用人油做蜡烛。
”落款处,画着一支扭曲的蜡烛,火苗却奇异地呈现出一种幽蓝色。
莫小羽是一名民俗杂志《大河诡事录》的特约撰稿人,
专攻那些荒诞不经、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奇风异俗。这封信的内容太过骇人听闻,若是往常,
他大概率会将其归为恶作剧,扔进废纸篓。但“烛阴县”这个名字,像一根冰冷的针,
刺了他一下。他记得,几年前整理一批清末民初的档案时,
曾零碎地看到过关于这个偏僻小县的记载。说法很模糊,
有的说那里古时曾有一种特殊的殡葬习俗,会用特殊方法处理先人遗体,以求“肉身不腐,
福泽后代”;还有的野史笔记里,提过一句“烛阴有奇烛,光照幽冥,可见不可言说之物”,
但语焉不详。当时他只当是古人臆想,未曾深究。如今这封诡异的信,
将“烛阴县”和“人油蜡烛”这两个元素粗暴地拼接在一起,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诱惑力。
是耸人听闻的谣言,还是某个被时光掩埋的恐怖民俗的冰山一角?职业的好奇心,或者说,
是某种对未知黑暗的本能探寻欲,驱使着莫小羽。他简单查询了一下,烛阴县地处本省边缘,
群山环抱,交通不便,经济滞后,几乎是个被现代化浪潮遗忘的角落。
网络上的信息少得可怜,最新的新闻还是一年前关于扶贫工作的报道。他没有犹豫太久,
简单收拾了行李,带上录音笔、相机和那封作为唯一线索的信,
踏上了前往烛阴县的长途汽车。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的开阔逐渐变为山地的逼仄,
天空也仿佛被连绵的灰绿色山峦压低了。空气潮湿闷热,
带着一股植物腐烂和泥土混合的气息。长途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将近八个小时,
才终于将莫小羽抛在了烛阴县汽车站。所谓的汽车站,不过是一片坑洼的水泥地,
几间破败的平房,以及几个目光浑浊、蹲在墙角抽烟等活儿的摩的司机。
县城的景象比莫小羽想象的还要陈旧。街道狭窄,两旁的建筑大多保留着几十年前的样式,
墙皮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偶尔有几栋贴着白色瓷砖的新楼,也显得不伦不类,
像是硬生生嵌进去的。时间在这里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甚至带着一种凝滞感。他按照地址,
找到了永寿街。这是一条更显破败的老街,青石板路面湿滑,长满了青苔。
两旁的木制房屋歪歪斜斜,屋檐低垂,遮挡了大部分光线,即使是在白天,
街道也显得异常昏暗。73号是一间临街的铺面,没有招牌,木门紧闭,
门板上积着厚厚的灰尘,门环锈迹斑斑,看上去废弃已久。莫小羽试着推了推门,纹丝不动。
他从门缝往里窥视,里面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
只有那股信纸上类似的、若有若无的甜腻腐败气味,似乎更浓郁了一些。他不动声色地退开,
在街对面一家生意冷清的面馆坐了下来,点了碗面,顺便和头发花白、满脸褶子的店主搭话。
“老板,打听个事儿,对面那家73号,以前是做什么的?”店主正慢吞吞地擦着桌子,
闻言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瞥了对面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含混地说:“哦,那家啊,
早些年是个做蜡烛的作坊,老手艺了,后来没人用蜡烛了,就关了。”“做蜡烛的?
”莫小羽心中一动,“您知道那家主人叫什么吗?或者,他们家做的蜡烛,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店主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抬眼看了看莫小羽,
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外地来的?问这个做啥?都是老黄历了,
主家也早搬走了,没影儿的事了。”他的语气带着明显的回避。莫小羽没有继续追问,
只是装作随意地吃面,心里却更加确定,这73号绝不简单。那种刻意的不愿多谈,
往往比滔滔不绝的讲述隐藏着更多的秘密。接下来的两天,
莫小羽以采风者的身份在烛阴县四处走访。他去了县文化馆,馆藏寥寥,
关于本地民俗的记载仅限于舞龙灯、唱山歌等大众项目,对所谓的“奇烛”只字未提。
他试图找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聊天,但一旦话题稍微触及“特殊的蜡烛”或者“老作坊”,
老人们要么摇头表示不知,要么就脸色微变,借口离开。这座小县城表面平静,
内里却似乎笼罩在一层无形的隔膜之下,将他这个外来者牢牢挡在外面。
那种甜腻腐败的气味,
偶尔会在县城的某个角落——比如古老的巷弄深处、废弃的老宅附近——突然飘入鼻腔,
但又转瞬即逝,难以捕捉。直到第三天傍晚,事情才有了转机。
莫小羽在县城边缘的一座小石桥上抽烟,桥下是浑浊的河水,散发着水腥气。
一个穿着破旧、头发乱如鸟窝、眼神有些呆滞的流浪汉凑了过来,伸出脏兮兮的手讨钱。
莫小羽给了他几张零钱,又递了根烟。流浪汉贪婪地吸着烟,咧开嘴,露出黄黑色的牙齿,
嘿嘿地傻笑。莫小羽心中一动,装作不经意地问:“兄弟,
听说过这地方以前有种很特别的蜡烛吗?”流浪汉愣了一下,歪着头,
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光闪烁了一下,他压低声音,
神神秘秘地说:“蜡烛……嘿嘿……人油点的蜡烛,
可亮哩……照得见……照得见鬼哩……”莫小羽的心猛地一缩,尽量保持平静:“哦?
在哪能见到这种蜡烛?”流浪汉伸出手指,
峦:“后山……乱葬岗……老葛家……晚上……他们晚上才去……”说完这些没头没脑的话,
流浪汉像是突然害怕起来,把烟头一扔,嘴里嘟囔着“不能说,说了要倒霉……”,
慌慌张张地跑开了。乱葬岗?老葛家?晚上?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
让莫小羽脊背升起一股寒意。他抬头望向那座大山,夕阳的余晖正迅速被山峰吞噬,
山的轮廓在渐浓的夜色中变得像一头匍匐的巨兽。那个废弃的73号作坊,
和流浪汉口中的“老葛家”、后山乱葬岗,它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强烈的探知欲压过了不安。莫小羽决定,当晚就去后山一探究竟。他回到简陋的旅馆,
准备了一支强光手电、一把匕首防身,等到夜色完全笼罩了烛阴县,便悄悄出了门。
县城入夜后异常寂静,只有少数几盏昏黄的路灯亮着,光线勉强勾勒出房屋和街道的轮廓。
大多数人家早早熄了灯,整个县城仿佛沉睡了,或者说,是隐藏在黑暗中,屏息凝神。
按照流浪汉模糊的指向,莫小羽沿着一条崎岖不平、长满荒草的小路往后山爬去。越往上走,
空气越凉,那股甜腻腐败的气味也时隐时现。山路两旁是影影绰绰的树木和坟包,
有些坟已经塌陷,露出黑洞洞的缺口。夜枭的叫声偶尔响起,更添几分阴森。
走了约莫半个多小时,他隐约看到前方山坳处有微光闪烁。他关掉手电,借着稀疏的月光,
小心翼翼地靠近。那是一片相对平坦的洼地,中间孤零零地立着一间低矮的石头房子,
没有窗户,只有一扇窄小的木门。微光正是从门缝里透出来的,
是一种……异常稳定、甚至有些凝固的昏黄光晕。空气中那股甜腻味在这里变得格外浓烈。
莫小羽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走到石屋旁,将耳朵贴在冰冷的石墙上。里面静悄悄的,
听不到任何声音。他犹豫了一下,轻轻推了推那扇木门。门没有锁,发出“吱呀”一声轻响,
开了一道缝。一股更浓郁、几乎让人作呕的甜腻气味扑面而来。莫小羽稳住心神,
透过门缝朝里望去。屋内的景象,让他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石屋中央,
点着一支粗大的蜡烛。那蜡烛的颜色并非常见的乳白或淡黄,
而是一种诡异的、半透明的蜡黄色,隐隐能看到内部有些浑浊的絮状物。
烛火燃烧得极其稳定,火苗几乎不动,散发出那种昏黄而粘稠的光晕,将整个小屋照亮。
而小屋的角落里,堆放着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那似乎是某种……经过处理的脂肪组织,
泛着油腻的光泽。旁边还有一些简陋的模具和工具。最让莫小羽头皮发麻的是,
在烛光映照下,墙壁上竟然投映出了一些模糊扭曲的影子,那影子不像人,
也不像任何已知的生物,蠕动着,变幻着,仿佛有生命一般!就在这时,
他身后传来一个冰冷、沙哑的声音:“外乡人,你不该来这里。”莫小羽猛地回头,
只见一个佝偻着背、面容干枯得像老树皮的老太婆,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他身后。
她手里提着一盏小油灯,昏黄的灯光照在她沟壑纵横的脸上,那双眼睛深陷,
却锐利得如同鹰隼,直勾勾地盯着他。莫小羽的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几乎要撞破肋骨。
他猛地转身,手电光下意识地扫向声音来源。昏黄的油灯光晕下,
那张布满深刻皱纹的脸如同风干了的核桃,一双深陷的眼睛却异常锐利,
没有任何老人常见的浑浊,反而像两口幽深的古井,映着跳动的灯火,仿佛能吸走人的魂魄。
老太婆的身材佝偻得厉害,穿着一身浆洗得发硬的深蓝色粗布衣裤,
整个人像是从身后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剪出来的一个影子。她提着的那盏小油灯,
灯焰也是稳得异乎寻常,发出的光与石屋里那支蜡烛的光晕如出一辙,只是范围小了许多。
“我……我是来采风的,迷路了。”莫小羽迅速镇定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
同时身体微微侧开,保持着警惕,右手悄悄摸向了别在腰后的匕首。
老太婆的嘴角似乎极其轻微地扯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更像是肌肉无意识的抽搐。
她的声音干涩沙哑,像是砂纸摩擦着朽木:“迷路?后山乱葬岗,可不是采风的好地方。
外乡人,这里的路,不好走,走错了,就回不去了。”她的目光越过莫小羽,
投向那扇虚掩的石门,眼神复杂,有警惕,有某种难以言喻的……眷恋?
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这屋里……点的是什么蜡烛?味道很特别。
”莫小羽试探着问,目光紧紧锁住老太婆的脸。老太婆收回目光,重新聚焦在莫小羽身上,
那锐利的眼神让他感到皮肤有些刺痛。“祖传的手艺,息魂蜡。”她答得简短,
语气不容置疑,带着一种此地主人般的权威,“给睡在这片山岗下的人点的,
让他们睡得安稳些。外人沾了这烛光,会做噩梦。”“息魂蜡?
”莫小羽想起墙上那些扭曲蠕动的影子,那可一点也不像能让人安魂的样子。
他注意到老太婆的措辞——“睡在这片山岗下的人”,而非简单的“死人”,
这细微的差别让他心头更沉。“老人家,您贵姓?是这烛阴县的人吧?
我听说县城里以前有个老蜡烛作坊,在永寿街73号……”莫小羽决定单刀直入,
观察她的反应。听到“永寿街73号”,老太婆的眼皮猛地跳了一下,
提着油灯的手也微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灯焰随之晃动,在她脸上投下摇曳的阴影,
使得她的表情更加阴晴不定。“那地方,早废了。”她的声音陡然变得冰冷,“陈年旧事,
提它做什么?外乡人,好奇心太重,不是好事。这烛阴县,有些东西,不该你看,不该你问,
更不该你想。”她向前逼近一步,虽然佝偻,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压力。“趁着你还能走,
赶紧离开。天黑透了,山里的路就更不好认了。”逐客令下得毫不客气。
莫小羽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反而可能激怒这个神秘莫测的老太婆。他点了点头,
装作顺从的样子:“好,我这就走,打扰了。”他侧身从老太婆身边走过,
能清晰地闻到她从里到外都浸透的那种甜腻腐败的气味,比石屋里的更浓烈,
仿佛她已经与这种气味融为一体。他沿着来路往回走,
能感觉到背后那道冰冷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拐过一个弯,消失在树影后,
那如芒在背的感觉才稍微减轻。但他没有真正离开。
他在不远处的密林里找了个隐蔽的角落躲藏起来,屏息凝神,观察着石屋的动静。
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石屋那边传来了轻微的响动。老太婆提着她那盏小油灯走了出来,
仔细地锁好了那扇破旧的木门——用的是一把老式的铜锁。她并没有立刻下山,而是提着灯,
在石屋周围缓慢地踱步,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的动作看似老迈迟缓,
但每一步都踩得异常沉稳。接着,她做了一件让莫小羽头皮发麻的事情。
她走到石屋旁一个不起眼的土堆前——那看起来像个小小的坟包,但没有墓碑。她蹲下身,
从怀里掏出什么东西,轻轻放在了土堆前。由于距离和光线,莫小羽看不清那具体是什么,
但隐约觉得像是一个小碟子。然后,老太婆就那样静静地蹲在土堆前,一动不动,
仿佛化作了一尊石像。只有她手中油灯那稳定得诡异的光晕,
和她周身散发出的那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沉寂,表明她是个活物。她在祭奠谁?
那个土堆里埋着什么?和这制作“息魂蜡”的秘术又有什么关系?莫小羽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在冰冷的夜风中潜伏着,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心底不断滋生的寒意。又过了许久,
老太婆才缓缓站起身,提着油灯,步履蹒跚地朝着下山的方向走去,
她的身影很快就被浓密的树林吞噬。确认老太婆走远后,莫小羽才从藏身处出来,
活动了一下冻得有些发麻的四肢。他没有再去尝试进入石屋,那把铜锁不是他能轻易弄开的。
但他记下了这个地方,以及那个奇怪的土堆。下山的路比上山时更觉阴森。或许是心理作用,
他总觉得两旁的树影里似乎有东西在窥视,那甜腻的气味也仿佛一直萦绕在鼻端。
回到旅馆时,已是后半夜,旅馆老板早已睡下,整个县城死寂得如同一座巨大的坟墓。
第二天,莫小羽改变了策略。他不再直接打听蜡烛作坊或者“人油蜡烛”这种敏感话题,
而是试图从侧面了解那个老太婆和“老葛家”的信息。他去了县城里唯一的一家小茶馆,
里面坐着几个消磨时光的老人。他点了一壶最便宜的茶,坐在角落里,假装看书,
耳朵却捕捉着周围的闲聊。机会很快来了。两个老人聊起了后山的乱葬岗。
“……听说昨晚后山又有动静了?”一个缺了门牙的老人压低声音说。“还能有谁,
肯定是葛家婆子呗。”另一个戴着毡帽的老人叹了口气,“几十年了,雷打不动,
真是造孽啊……”“唉,也是没办法,老葛家就剩下她一个了,守着那点祖传的东西,
也是可怜。”“可怜?我看是魔怔了!那玩意儿邪性得很,沾上了就没好下场。你看她家,
以前多风光,现在呢?断子绝孙,就剩个疯婆子守着个破石屋子……”“嘘!小声点!
别瞎说!让葛婆子听见了,没好果子吃!”话题到这里就戛然而止,
老人们似乎对“葛婆子”和她家的事讳莫如深,但语气中透露出的信息却让莫小羽心跳加速。
葛家婆子?老葛家?看来那个老太婆就是流浪汉口中的“老葛家”的人。听老人们的意思,
葛家曾经是本地的大户,但因为某种原因而没落,
只剩下这个被称为“葛婆子”的老太婆守着祖传的秘密。而且,她每晚去后山石屋,
似乎是一种持续了几十年的固定行为。
“断子绝孙”、“邪性”、“没下场”……这些词汇更加深了“人油蜡烛”传闻的可信度。
莫小羽又试探着向茶馆老板打听葛家。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闻言脸色微变,
摆摆手:“客人,打听那家干嘛?不吉利。他们家的事,县里没人愿意提,你也别问了,
对你没好处。”几乎所有人都对葛家避之不及。这种集体性的沉默和恐惧,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下午,莫小羽决定再去永寿街73号看看。白天光线好些,
或许能发现昨晚遗漏的细节。白天的永寿街依旧昏暗潮湿。73号作坊的门依旧紧锁。
莫小羽这次更加仔细地观察周围环境。他注意到,作坊旁边的墙壁上,
似乎有一些模糊的刻痕。他凑近去看,由于年代久远和风雨侵蚀,刻痕已经很难辨认,
但隐约能看出是一些扭曲的符号,不像文字,倒更像某种原始的图腾或符咒。其中一个符号,
有点像那封匿名信上画的扭曲蜡烛。他还发现,作坊门楣上方的砖缝里,似乎塞着什么东西。
他踮起脚,小心翼翼地用树枝将其拨弄出来。那是一个小小的、已经干枯发黑的布包,
拆开来,里面是一撮灰白色的头发和几片指甲一样的东西,上面还用朱砂画着奇怪的纹路。
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这是某种民俗中的辟邪物?还是……诅咒用的东西?
为什么会塞在这里?是为了封印什么,还是警告外人不要靠近?
这个发现让73号作坊显得更加诡谲。它不仅是一个废弃的作坊,
更像是一个被某种力量标记和封锁的禁忌之地。就在莫小羽凝神思考时,
他眼角的余光瞥见街角似乎有个人影一闪而过。他猛地转头,
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迅速消失在巷口。那背影有些熟悉,似乎……是昨天面馆的那个店主?
他在监视我?莫小羽的心沉了下去。看来他的调查,已经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
这个看似平静闭塞的小县城,水面之下已经开始暗流涌动。夜幕再次降临。
莫小羽没有再去后山冒险,他知道葛婆子肯定会在那里。他待在旅馆房间里,
这两天收集到的碎片信息:烛阴县葛家掌握着一种可能使用特殊材料制作“息魂蜡”的秘术。
这种蜡烛具有燃烧稳定、光晕奇特、可能映照出诡异影子的特性。葛婆子,葛家最后的传人,
行为古怪,每晚去后山石屋守烛,对家族往事守口如瓶,对外来者充满警惕。
永寿街73号、后山乱葬岗石屋、神秘土堆。 县城居民对葛家之事集体沉默恐惧,
可能有本地人在暗中监视外来者的动向。 匿名信寄送者的身份和目的?
葛婆子警告中“回不去”的真正含义?石屋墙上影子的真相?
那种甜腻腐败气味的来源究竟是什么?线索似乎越来越多,但核心的迷雾却丝毫没有散开,
反而更加浓重。莫小羽感到自己正站在一个巨大谜团的边缘,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葛婆子那句“好奇心太重,不是好事”像一句谶语,在他耳边回响。他拿出那封匿名信,
再次审视那个扭曲的蜡烛图案。寄信人显然知道内情,并且希望有人来揭开这个秘密。
但这个人是谁?是出于正义感,还是别有用心?莫小羽意识到,要想揭开真相,
不能只在外围打转,必须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
或许就在那个对葛家之事似乎知情的面馆店主身上,或者……需要想办法再次接近葛婆子,
用更巧妙的方式获取信息。窗外,烛阴县的夜漆黑如墨,
连零星灯火都仿佛被这浓稠的黑暗吞噬。只有那若有若无的、甜腻而腐败的气息,
依旧顽固地渗透进房间,提醒着莫小羽,他正身处一个被古老而邪恶秘密缠绕的漩涡中心。
而他的闯入,或许已经惊醒了某些沉睡的东西。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像附骨之疽,
缠绕了莫小羽一整夜。他甚至能感觉到,黑暗中有一双,或者不止一双眼睛,
正透过旅馆薄薄的窗帘缝隙,冷冷地注视着他这个不速之客。
面馆店主那张看似憨厚、实则闪烁不定的脸,在他脑海里反复出现。不能再被动等待了。
突破口,或许就在那碗面的热气之后。第二天一早,
莫小羽再次走进了那家位于永寿街对面的面馆。时间尚早,店里没有其他客人。
店主正背对着门口,在灶台前忙碌,佝偻的背影在蒸腾的水汽里显得有些模糊。听到脚步声,
店主回过头,看到是莫小羽,脸上闪过一丝极不自然的僵硬,
随即又堆起那种生意人惯有的、略带讨好的笑容:“哟,客人这么早?吃面?”“嗯,
老样子。”莫小羽在昨天那个靠里的位置坐下,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店内的陈设。
店面狭小、陈旧,桌椅油膩,墙壁被经年的烟火熏得发黄。
一切都符合一个偏远县城老店的样貌,除了……过于干净的地面,
以及角落里那个与整体格调不符的、崭新的小型冰柜。冰柜工作时发出低沉的嗡鸣,
在这寂静的早晨显得格外突兀。面很快端了上来,热气腾腾。店主放下碗,却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用那块看不出本色的抹布,反复擦拭着莫小羽面前的桌子,动作缓慢而刻意。
莫小羽没有动筷子,他抬起眼,直视着店主那双躲闪的眼睛:“老板,贵姓?”“啊?
哦……姓王,街坊都叫我老王。”店主愣了一下,答道。“王老板,”莫小羽声音平稳,
却带着不容回避的力量,“我昨天去了后山。”老王擦拭桌子的手猛地一顿,
指关节有些发白。他抬起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紧张和恐惧的神色:“后……后山?客人,你去那儿干啥?
那地方不干净!”“我去找永寿街73号的主人,葛家。”莫小羽步步紧逼,
观察着老王脸上的每一丝细微变化,“我听说,葛家做的蜡烛很特别,用的是祖传的手艺。
”老王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眼神慌乱地瞟向门口,
仿佛害怕有什么东西会突然闯进来。“你……你胡说什么!什么葛家!什么蜡烛!早没了!
都过去了!”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色厉内荏的尖锐。“过去了?”莫小羽冷笑一声,
从口袋里掏出那封匿名信,摊开在桌上,手指点着那个扭曲的蜡烛图案,“那这个呢?
有人告诉我,他们在用人油做蜡烛。王老板,你在这条街上开店几十年,
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看到那封信和图案,老王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后退一步,
撞翻了身后的凳子,发出刺耳的响声。他惊恐地瞪着那封信,又看看莫小羽,
呼吸变得粗重起来。“这……这东西你从哪里来的?!快收起来!不能看!不能提!
”他几乎是嘶吼着,冲上来想要抢走那封信。莫小羽抢先一步将信收起,
冷冷地看着他:“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葛家,关于那种蜡烛。否则,
我不保证这封信的内容,会不会出现在县城的公告栏上,或者……送到该送的人手里。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莫小羽在赌,赌老王对这件事的恐惧,赌他知情,
并且害怕秘密被公开。老王的胸口剧烈起伏着,他死死地盯着莫小羽,
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恐惧。汗水从他额角滑落,滴进衣领。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
面馆里只剩下冰柜低沉的嗡鸣和老王粗重的喘息。终于,他像是被抽干了力气,
颓然地靠在灶台上,
声音沙哑得如同破风箱:“你……你这是在找死啊……”老王走到店门口,
紧张地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了店门,甚至从里面插上了插销。
面馆顿时昏暗下来,只有灶台残余的火光和从门缝透进的几缕微光,
营造出一种压抑的密室感。他拖过一张凳子,坐在莫小羽对面,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
压低了声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
惹上葛家的事,都没好下场……”“说具体点。
”莫小羽不动声色地按下了口袋里的录音笔开关。“葛家……以前是烛阴县的大户,
听说祖上是明朝时候从外面迁来的,就是靠着做蜡烛的手艺发的家。”老王的眼神开始恍惚,
陷入了回忆,“他们家的蜡烛,那时候是贡品,听说皇帝都用过……点上之后,特别亮,
而且有种特别的香味,能安神,还能……还能让东西看起来更鲜亮。”“香味?
是不是一种甜腻腻,又有点像是……东西放久了的味道?”莫小羽追问。老王猛地点头,
脸上恐惧更甚:“对!就是那个味!你也闻到了?那味道……邪门得很!”他咽了口唾沫,
继续道:“后来……大概是清末的时候,出过一档子事。具体什么事,老一辈人也说不清,
只说跟蜡烛的用料有关。从那以后,葛家就败落了,作坊也关了,家里人丁也越来越少。
到了葛婆子这一代,就只剩下她一个了。”“用料?”莫小羽紧紧抓住这个词,
“是不是……用了不该用的东西?”老王的脸扭曲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
几乎成了气音:“都……都那么传……说他们家的蜡烛,光特别‘实’,
是因为掺了……掺了‘人油’……特别是……是未足月夭折的婴孩……那样炼出来的油,
最是‘纯净’,点的烛光能照见……照见平常看不见的东西……”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亲耳从本地人口中听到这个骇人听闻的说法,莫小羽还是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和寒意。
匿名信的内容被证实了。“葛婆子现在还在做这种蜡烛?”“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老王慌忙摆手,“我只知道,她晚上经常会去后山那个老石屋,
那是葛家祖上传下来的地方,听说以前就是炼制蜡烛胚子的地方。县里没人敢靠近那里,
连乱葬岗都绕着走。”“那封匿名信,”莫小羽拿出信,“是谁写的?你知不知道?
”老王茫然地摇头:“不知道……县里没人会写这种东西,也没人敢写……这是催命符啊!
”“你昨天为什么跟踪我?”莫小羽突然问道。老王浑身一颤,
低下头:“我……我不是跟踪你。是……是有人让我看着点,
有没有外地人来打听葛家的事……”“谁?”陈铭追问。老王却死死地闭上了嘴,
无论莫小羽再怎么问,他只是摇头,脸上露出极度的恐惧,仿佛说出那个名字就会大祸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