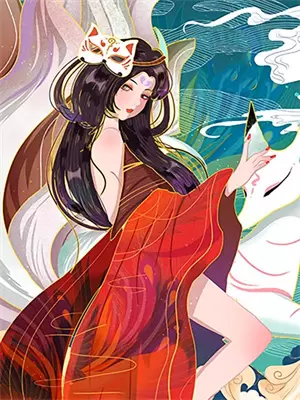我会永远记得那晚的沿江西路。河面上破碎的灯光,像被谁不经意撒了一把碎玻璃,
浮在暗流之上,随波晃荡。对岸的高楼在夜色里摇摇欲坠,轮廓模糊,
仿佛随时会塌进江水里。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潮湿的凉意,拂过我的耳际,
也拂过我心底那根早已绷紧的弦。不远处,有人只言两语地唱着情歌,声音断断续续,
像被风吹散的烟。那调子我听不懂,却莫名觉得熟悉,像是从很远的过去飘来的回音。
打火机“啪”地一声亮起,火光短暂地照亮了少年的脸——他低着头,睫毛颤动,
眼眶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我站在他身后半步的距离,没有说话。那一秒,
心脏传来清晰的刺痛,像有人用钝刀慢慢剜进去,不急着取走什么,只是反复搅动。
我扶住栏杆,指尖冰凉,却感觉不到冷。江水在脚下流淌,无声无息,像时间本身。
那是2007年的冬夜,广州的冬天从不真正冷到刺骨,但那晚的风,却像是从北方吹来的。
我和陈皮糖的初遇,其实并不浪漫。那天我刚从图书馆出来,抱着一摞书往宿舍走,
天色阴沉,空气里压着一层看不见的湿气。我走得急,书堆得太高,遮住了视线,
结果在转角处撞上了一个人。书散了一地。“对不起!”我慌忙蹲下捡,手忙脚乱。“没事。
”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深灰色毛衣的男生,蹲在我对面,
正把我的书一本本捡起来。他的手指修长,动作很稳,却在碰到一本《海子诗选》时顿了顿。
“你也喜欢海子?”他问。我愣了一下,“嗯……高中时读过一点,现在……只是随便翻翻。
”他没再说话,把书递给我,目光却停在我脸上几秒,才转身离开。我站在原地,
看着他背影消失在教学楼拐角,忽然觉得那一眼,像是一道无声的叩问。后来我才知道,
他叫林知夏,外文系大三,大家都叫他“陈皮糖”。没人知道这外号从哪来,
有人说是因为他总在口袋里揣一包陈皮糖,讲课时含一颗,说能提神;也有人说,
是因为他性格像陈皮糖——表面甜,内里苦,嚼久了还有点涩。我第一次听人这么形容他时,
笑了。可后来我才明白,那不是形容,是命运。我和他的第二次相遇,是在沿江西路的江边。
那天我逃了晚课,一个人沿着江边走。天快黑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江面泛着微光。
我坐在石阶上,掏出那本《海子诗选》,翻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念到这里,我停住了。幸福是什么?
我忽然想不起上一次真正开心是什么时候。父母离异,母亲远走,父亲酗酒,
大学读着不喜欢的专业,暗恋的人从没正眼看过我……我像一株被遗忘在角落的植物,
勉强活着,却从没真正舒展过。“你也觉得这首诗假吗?”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回头,
是林知夏。他穿着那件深灰色毛衣,手里捏着一颗陈皮糖,正剥开糖纸。“不是假,
”我低声说,“是太理想了。我们这种人,连‘明天’都不敢想。”他在我身边坐下,
没说话,只是把那颗陈皮糖递给我。“吃吗?”我摇头。他笑了笑,自己含了进去,
“我小时候,每次难过,我妈就给我一颗陈皮糖。她说,苦的东西含久了,反而会回甘。
”我看着他侧脸,路灯的光落在他睫毛上,投下一片阴影。“那你现在还难过吗?
”他没回答,只是望着江面,良久,轻声说:“快到春分了。”我不懂。他转头看我,
“你知道吗?陈皮,是晒干的橘子皮,要放三年才够味。我妈说,有些东西,得等。
”我忽然觉得鼻子发酸。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关于诗,关于孤独,关于那些说不出口的夜晚。
他告诉我,他母亲早逝,父亲再婚,他从小跟外婆长大。外婆总说,人要像陈皮糖,
苦过才甜。“可我现在,还是只尝到苦。”他笑着说,可那笑,比哭还让人心疼。我看着他,
忽然想抱抱他。但我没动。我们约定,以后每周五晚上,都在沿江西路见面。他总是先到,
坐在石阶上等我,手里捏着一颗陈皮糖。有时他带吉他来,断断续续地弹几句,从不完整,
像是在等某个人来接下一句。“你会唱歌吗?”他问过我一次。我摇头,“五音不全。
”他笑,“那我唱给你听。”他唱的歌都很老,
周华健、张信哲、齐秦……那些我以为早已过时的旋律,从他嘴里唱出来,
却像重新活了过来。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沙哑,像深夜电台的主持人,
温柔地诉说别人的遗憾。我常常听得入神,忘了时间。有一次,
我问他:“你为什么总唱情歌?”他低头拨弦,轻声说:“因为我不敢对谁说喜欢。
”我心跳漏了一拍。风从江面吹来,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乱了我的呼吸。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周五的江边,陈皮糖,碎光,情歌,和他偷偷红了的眼眶。
可命运从不给人太多准备时间。那天是2月28日,离春分还有六天。他没来。
我等了两个小时,江风冷得刺骨。我给他发短信,打电话,都没回。第二天,
我在图书馆门口遇见他。他瘦了一圈,眼睛下有明显的青黑,整个人像被抽走了力气。
“你去哪了?”我问。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家里有点事。”我没再问。
可那天晚上,我又去了沿江西路。我想等他。十点,十一点,十二点……江边空无一人。
我正准备走,忽然看见他从远处走来,脚步踉跄,像是喝醉了。“林知夏!”我跑过去。
他抬头看我,眼神涣散,下一秒,整个人软倒在我怀里。我扶着他,闻到他身上浓重的酒气,
还有……血的味道。“你受伤了?!”他没说话,只是死死抓着我的手臂,指节发白。
我把他拖到石阶上坐下,借着路灯的光,看见他右手手背上有一道深深的划伤,血已经凝固,
可边缘还在渗。“谁干的?!”我声音发抖。他忽然笑了,笑得极轻,极冷,
“我爸……说我不配活着。”我脑子“嗡”地一声。他靠在我肩上,
声音轻得像梦呓:“我妈走那天,也是这样的夜。她说,等春分,
橘子树就开花了……可她没等到。”我抱着他,眼泪无声地往下掉。“别怕,我在。”我说。
他抬起手,轻轻擦掉我的泪,“傻瓜……你才是需要被安慰的那个。”那一夜,
我们谁都没睡。他断断续续地讲完了一切——父亲酗酒家暴,母亲为救他被推下楼梯,
脑溢血去世,他被亲戚收养,可没人真正关心他。他努力读书,弹吉他,写诗,
只是为了在某个瞬间,感觉自己还活着。“我就像那颗陈皮糖,”他苦笑,“被晒干,
被遗忘,被时间慢慢磨出苦味。”我握紧他的手,“可你还在等回甘,对吗?”他没回答,
只是望着江面,喃喃道:“快到春分了。”我忽然明白,他等的不是春天,是某种救赎。
从那天起,我开始陪他去心理辅导,陪他写申诉材料,申请独立监护权。
我陪他熬过每一个失眠的夜,听他梦呓里喊“妈”,看他偷偷吃抗抑郁药,
看他对着镜子练习微笑。他渐渐好起来。三月十四日,春分前五天,他第一次牵我的手。
那天我们坐在江边,他剥开一颗陈皮糖,放进我嘴里。“尝到了吗?”他问。我嚼了嚼,
先是苦,然后,一丝极淡的甜在舌尖蔓延。“有点甜了。”我说。他笑了,眼睛亮得像星星。
“等春分那天,我带你去老城区的陈皮作坊,”他说,“我外婆以前就在那儿晒陈皮。她说,
三年的陈皮,才够味。”我点头,“好。”可春分那天,我没等到他。早上六点,
我收到一条短信:“对不起,我走了。别找我。”电话打不通,宿舍没人,
外文系说他办了休学。我疯了一样找他,问遍所有认识的人,
甚至去了他外婆的老宅——门锁着,院子里橘子树光秃秃的,像被抽走了魂。我蹲在树下,
哭得喘不过气。我以为他放弃了。直到三年后,我在一家小书店的角落,发现一本诗集,
署名“林知夏”。翻开第一页,是一首题为《未及春分》的诗:我在冬夜等一场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