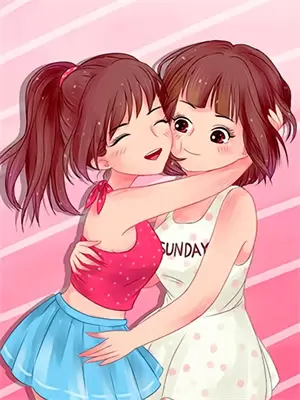
我被继父囚禁虐待,逃跑时被一个男人救了。他是个画家,温柔、英俊,
眼底却藏着化不开的哀伤。他把我带回家,将我宠成公主,画了无数张我的画像。
我爱上了他,以为找到了人间唯一的光。直到警察找上门,我才在他画室的暗格里,
发现了另外七张女人的画像。她们,是轰动全市的连环杀人案里,所有的受害者。
而她们的死状,与继父虐待我的手法,一模一样。1警车开走后,别墅陷入死寂。
空气里还残留着陌生人的气息,提醒我刚刚发生的一切不是幻觉。我站在画室中央,
墙上挂着我的巨幅画像,画里的我笑容天真,是我爱上沈聿时的模样。而现在,
我脚边散落着另外七张女人的画像,从墙壁的暗格里掉出来。
她们是新闻里滚动播报的连环杀人案受害者。每一张画,
都精准地复刻了她们被发现时的惨状。那些扭曲的姿态,
那些我只在噩梦里才会重温的、继父施加在我身上的虐待痕迹,
此刻被沈聿用一种近乎虔诚的笔触,描绘在这些素不相识的女人身上。“吓到了?
”沈聿的声音像一片羽毛,轻轻落在我绷紧的神经上。他没有丝毫慌乱,
仿佛刚才面对警察盘问、并用完美说辞将他们打发走的人不是他。他走过来,
将一张柔软的羊绒毯披在我身上,那上面有我熟悉的、他身上的松木香气。曾几何时,
这气味是我的安眠药。现在,它闻起来像裹尸布。我挥开他的手,后退一步,
脚跟撞到了画架。“她们……为什么?”我的嗓子沙哑。沈聿没有因为我的抗拒而生气,
他只是捡起地上一张受害者的画像,用指尖轻轻拂过画面上女人空洞的眼睛。“因为,
我要研究他。”我的继父,那个将我囚禁在地下室,让我活在地狱里的恶魔。“我不懂。
”我摇着头。“你不懂,默默,这很正常。”他踱步到我面前,
用一种精神科医生对待病人的语气说话。“你仔细看,她们身上的伤痕,
是不是和你继父折磨你的手法,惊人地相似?”他将画递到我眼前。我被迫看着那画面,
那熟悉的捆绑方式,那特定角度的伤口……过去几个月我拼命想忘记的细节。
窒息感再次袭来。“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清楚?”我抓住最后一丝理智,质问他。
“因为我是个画家,默默。我的眼睛能捕捉到最微小的细节。”他条理清晰地解释,
“警察公布的案情报告太笼草了,我需要‘复原’犯罪现场,通过艺术,
走进那个凶手的内心世界,才能找到他的破绽。”他顿了顿,
用那双曾让我沉溺的眼睛看着我。“默默,你难道没想过,为什么这些受害者都死了,
只有你活了下来?”“因为你逃了出来。你是唯一的幸存者,也是最重要的‘证人’。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个恶魔作品上最大的败笔。他一定会回来找你,完成他的‘杰作’。
”他的逻辑天衣无缝,将我所有的恐惧和怀疑都收拢进去。“所以,我画她们,
是为了保护你。我必须比那个恶魔更了解他自己,才能预判他的下一步行动。
”他将我的颤抖定义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将我的恐惧解释为对过去的回溯。
他用那些我听不懂但听起来无比专业的心理学名词,
将我钉死在“一个需要被保护的、精神脆弱的受害者”的位置上。“你看看我。
”他捧起我的脸,强迫我与他对视,“我是沈聿,是把你从地狱里拉出来的人。
我怎么可能伤害你?”是啊。他是沈聿。是那个在我最狼狈的时候,用昂贵外套包裹我,
对我说“别怕,有我”的沈聿。是那个为我清洗伤口,喂我吃饭,告诉我“在这里,
你就是全新的”的沈聿。是那个用画笔重塑我的尊严,称我为“重生缪斯”的沈聿。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以为是人间唯一的光的男人,第一次发现,他的温柔,
原来是一座我永远也逃不出去的、用爱铸成的囚笼。2三个月前,
我从继父家的地下室里逃出来。那是一个肮脏的雨夜,我赤着脚,
身上只有一件被撕扯得破破烂烂的单衣。每跑一步,骨头都在叫嚣,
身后似还有那个恶魔的喘息声。我不知道跑了多久,
终于在一条无人的小巷里耗尽了所有力气,重重地摔在冰冷的积水里。意识模糊间,
我感觉雨停了。一双擦得锃亮的定制皮鞋停在我眼前。我费力地抬起头,
看到了一张模糊的脸。他撑着一把黑色的伞,将我和整个世界的风雨都隔绝开来。
巷口的霓虹灯光,勾勒出他清隽的轮廓。他脱下身上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羊毛大衣,弯下腰,
轻轻地、没有任何嫌弃地,包裹住我泥泞又伤痕累累的身体。“别怕,有我。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然后,我彻底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
我躺在一张柔软得不像话的大床上。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松木香气,
温暖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伤口被仔细地清洗、上药,
换上了一件干净柔软的丝质睡裙。我以为自己死了,到了天堂。“醒了?饿不饿?
”沈聿端着一碗温热的粥走进来。他换了一身居家的米色毛衣,阳光照在他身上,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让人安心的暖意。我下意识地往后缩,
那是被囚禁虐待数年后刻在骨子里的反应。他没有再靠近,只是把粥放在床头柜上。“别怕,
这里很安全,没有人会伤害你。”他从不追问我的过去,
从不问我为什么会满身是伤地倒在巷子里,也从不问我的名字和来历。
他只是日复一日地照顾我。为我准备可口的食物,为我挑选漂亮的裙子,
为我把整个别墅的花瓶里都插满最新鲜的白玫瑰。他说:“在这里,你就是你,是全新的。
”他给了我一个新名字,林默。取自“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默”,
他说我的眼睛里有无尽的故事,不需要言语。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别墅里,我的世界只剩下他。
他是个画家,别墅里最大的房间是他的画室。在我身体好一些后,他开始为我作画。
我局促地坐在他的对面,不敢看他。“别动,默默,你现在的样子很美。”我从没想过,
“美”这个字会用在我身上。在继父的嘴里,
我是“肮脏的”、“下贱的”、“不值得活着的”。可在沈聿的笔下,
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他画我蜷缩在沙发上,像一只受惊的小猫,
他说那是“警惕中的脆弱”。他画我站在窗前看雨,他说那是“迷茫中的诗意”。
他画我第一次对他露出微笑,他说那是“废墟中开出的花”。他称我为他的“重生缪斯”。
他说:“默默,你不知道你有多美好。你的痛苦,你的挣扎,你身上每一道伤疤,
都是你生命力的勋章。你是我见过最美的艺术品。”在他的画里,
我不再是那个残破不堪、一文不值的女孩。我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美丽的、值得被爱的自己。
那些被继父摧毁的自尊和自信,被他用画笔,一点一点地粘合了起来。我开始依赖他,
信任他,最后,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我爱他为我作画时专注的样子。
我爱他为我念诗时温柔的嗓音。我爱他每次出门回来,都会带一束白玫瑰给我。
我爱他将我宠成一个不谙世事的公主,仿佛我生来就应该被这样珍爱。那天晚上,
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在他画完最后一笔后,从背后抱住了他。“沈聿,我爱你。
”他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转过身,将我紧紧拥入怀中。他的吻落下来,
带着松木的香气和颜料的味道,温柔而珍重。那一刻,我彻底相信,这个男人,
就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神明。他是我的人间,是我唯一的光。我以为,
我会永远做他独一无二的缪斯。3我开始拼命地想要相信沈聿。
我相信他画那些受害者是为了保护我,相信他是为了抓到那个恶魔。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在心里疯狂地生根发芽。我开始像个幽灵一样在别墅里游荡,
用一种全新的、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我曾以为是天堂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了那瓶香水。
在他的收藏柜里,一排昂贵的男士香水中,突兀地摆着一瓶早已停产的女式香水,
瓶身优雅复古。我记得它的味道。警察上门时,我无意间瞥到一份资料,
上面记录着第三名受害者的信息,在她的遗物里,就发现了同款香水,那是她最爱用的味道。
我的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如果只是为了研究案情,
需要收藏一瓶和受害者一模一样的绝版香水吗?我不敢问他。我怕他再次用那套完美的逻辑,
将我的疑虑定义为病态的猜忌。于是,我把目标转向了他的书房。
那是我唯一没有仔细探索过的地方。沈聿说那里放着他最重要的灵感和资料,不希望被打扰。
我趁他外出采购的时候,溜了进去。书房很大,满墙的书。
我一眼就看到了书桌上那本被翻阅得起了毛边的泰戈尔诗集。我记得,
他曾给我念过里面的诗句。“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当时我觉得无比浪漫,
现在只觉得讽刺。我拿起那本诗集,指尖触碰到书页里夹着的硬物。我翻开,
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掉了出来。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站在一片向日葵花田里,
笑得比阳光还要灿烂。她的眉眼,与我有七分相似。我死死地盯着那张脸,
一种比发现受害者画像时更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瞬间窜上天灵盖。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默默,你在做什么?”沈聿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吓得手一抖,照片掉在了地上。
我没有回头,只是僵硬地站在原地。他走过来,没有责备我私自进入书房,只是弯腰,
珍重地捡起了那张照片,用指腹轻轻摩挲着女孩的脸。“她叫肖冉,是我的妹妹。”他开口,
嗓音沙哑。“双胞胎妹妹。”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她很漂亮,也很天真,
总相信世界是美好的。直到很多年前,她也遇到了一个恶魔。”他将照片递给我看。“你看,
她笑得多开心。可就是因为这笑容,她被一个变态盯上了。那个凶手的手法,
和现在这些案子,如出一辙。”他口中的“悬案”,我似乎在某些旧新闻里看到过。
一个天才少女画家,在画展前夕惨遭杀害,凶手至今没有找到。“警察没用,
他们找不到凶手。所以,只能我来。”沈聿的语气平静下来,恢复了他惯有的温和,
但那温和之下,是淬了冰的恨意。“我找了很多年,直到我发现了你的继父。他的手法,
他对受害者的心理控制,都和当年那个凶手太像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同一个人。
”“然后,我遇见了你。”“你不仅长得像肖冉,你还从同一个恶魔的手中逃了出来。默默,
你是上天赐给我的、用来复仇的最后一把钥匙。”我听着他的话,
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人剥光了衣服,扔在冰天雪地里的傻子。
“所以……”我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你救我,照顾我,对我好……都是因为我像她?
都是为了引出凶手?”“对不起,默默。”他没有否认,而是选择了坦白。“我承认,
我最初接近你,是有目的的。我需要一个诱饵,一个足够像肖冉,
又能引起那个恶魔注意的诱饵。而你,是完美的人选。”他向我道歉,将自己所有的行为,
都归结为对妹妹深沉的爱,和被点燃的复仇执念。他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坦诚,将我捧上云端,
又亲手推下深渊。我的世界再次崩塌了。我只是他为妹妹复仇的工具。
一个名叫肖冉的女人的,替身。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诱饵。
4我被“替身”和“诱饵”这两个词,钉在了耻辱柱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
像一个活死人。沈聿没有强迫我,他只是每天准时把食物放在我门口,然后安静地离开。
他的耐心和温柔,在此刻看来,更像是怜悯和掌控。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认输。
我必须找到更多关于肖冉的真相。我开始假装接受了这个事实,重新对他露出顺从的微笑。
沈聿似乎很满意我的“懂事”,对我的防备也放松了许多。我抓住他一次外出的机会,
目标明确——别墅里唯一一间被他用密码锁锁死的房间。肖冉的卧室。我没有密码,
但我有的是从继父那里学来的、为了生存而练就的撬锁技巧。用一根发夹,我花了十几分钟,
在听到“咔哒”一声轻响时,手心全是冷汗。我推开门,
一个被时光封存的世界展现在我眼前。房间被完美地保存着,仿佛主人只是刚刚离开。
画架上还有未完成的画,书桌上摊开着书,一切都干净得一尘不染。
这不像一个死去多年的女孩的房间,更像一个精心布置的、用来凭吊的圣殿。
我的目光落在书桌的抽屉上。我拉开抽屉,里面整齐地放着几本素描本和一本日记。
那本日记,带着一把小巧精致的银锁。我的心脏狂跳起来。直觉告诉我,所有的答案,
都在这本日记里。锁被我轻易地撬开。我翻开日记,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不对。
这字迹我太熟悉了。这不是任何一个女孩的字,这是沈聿的笔迹。我如坠冰窟,
从头到脚都凉透了。我颤抖着手,一页一页地往下翻。三月五日,晴。冉冉今天笑了,
她对那个送她画册的男生笑了。那个笑容太刺眼,不干净了。她只能对我一个人这样笑。
晚上,我‘惩罚’了她,我告诉她,这是为了‘净化’她身上的尘埃。她哭了,
哭着说再也不会了。她哭的样子,真美。四月十日,雨。她又想逃。
她和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走得很近,还想让他指导她的毕业作品。她以为我不知道。
我把那个老师的调色刀弄坏了,让他划伤了手。我告诉冉冉,
所有企图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的人,都会遭到厄运。她很害怕,这很好。恐惧,是最好的缰绳。
五月三日,阴。她开始反抗我,她质问我,说我是魔鬼。
她竟然用‘魔鬼’这个词来形容我。我只是太爱她了,
我只是想把她变成一件永恒的、完美的、只属于我的艺术品。她不懂,凡人总是这么愚蠢。
我让她跪在画室里,看着我一笔一笔地,画下她流泪的样子。日记里的每一句话,
字字让人心惊。病态的占有欲,扭曲的爱,
用“惩罚”和“净化”为名的虐待……那个阳光下笑得灿烂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