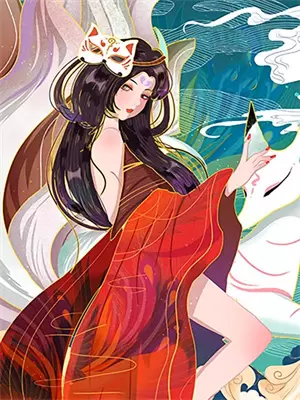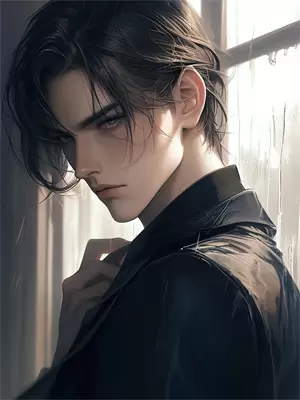
第一章 旧影苏晚用竹起子挑开浆糊罐的瞬间,鼻腔里涌入熟悉的米香。
这是她熬了三小时的糯米浆,黏稠度刚好能黏合清代画册的残页。修复室的窗开着半扇,
初秋的风卷着梧桐叶进来,落在摊开的古籍上,像谁偷偷夹了片枯叶当书签。
她正对着台灯修补一页民国日记,泛黄的宣纸上,蝇头小楷写得娟秀:“九月三日,晴。
今日在图书馆见阿珩读《昆虫记》,他说螳螂捕食时会收起翅膀,像穿长衫的先生拢着袖口。
我笑他看书总想到些奇奇怪怪的事,他却指着西窗说,你看那光斑,
像不像书里掉出来的星子?”指尖忽然被硬物硌了下。苏晚翻过纸页,
半张老照片从装订线的缝隙里滑出,轻飘飘落在铺着宣纸的工作台上。照片边角卷着毛边,
褪色成温柔的米黄。穿学生装的少年站在图书馆拱门前,白衬衫的领口系着深灰领结,
左手按在胸前口袋,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阳光斜斜打在他额前碎发上,发梢泛着金芒,
左边嘴角有颗极小的梨涡,陷得恰到好处。苏晚的呼吸猛地顿住。这张脸……她霍然抬头,
视线越过修复室的玻璃窗,落在走廊尽头。林砚之刚从茶水间出来,白大褂的袖口卷到手肘,
露出小臂上淡青色的血管。他低头看着手机,侧脸线条冷得像块冰雕,鼻梁高挺,
唇线抿成一条直线——可那眉眼的弧度,尤其是笑起来时左边嘴角的梨涡她见过一次,
上周项目组聚餐,他被同事灌了半杯啤酒,唇角不经意勾起时,那梨涡像藏了颗糖,
分明与照片里的少年如出一辙。林砚之是三个月前来古籍研究所的实习生,
计算机系的高材生,据说是被导师硬塞进这个“古籍数字化归档”项目组的。他总穿白衬衫,
戴黑框眼镜,说话语速快得像敲代码,三句里必有一句“操作手册第X页写了”。
上周苏晚修复的《清代花鸟图谱》被他误存成压缩包,两人在会议室吵到深夜,
最后他摔门而去时,白大褂下摆扫倒了她桌上的冷咖啡,深褐色的液体在图谱扫描件上晕开,
像朵难看的墨花。就是这个总爱皱着眉怼她的实习生,
怎么会和一张近百年前的老照片长得一模一样?苏晚捏着照片凑近台灯,
少年身后的图书馆拱门雕着缠枝纹,
门楣上“文渊阁”三个篆字隐约可见——这正是研究所后院那栋民国老楼的图书馆,
去年翻修时特意保留了原貌,只是门楣上的字被风雨侵蚀得只剩浅痕。
她忽然想起日记里的句子,慌忙翻到前几页。
果然在九月二日的日记里看到:“每周三下午三点,西窗的光会在第三排书架投下光斑,
阿珩说这是时间在眨眼睛。今日他借走了我的《昆虫记》,说明日三点,
要在光斑里藏个秘密给我看。”苏晚的心跳漏了一拍。今天正好是周三。下午两点五十九分,
她抱着本《古籍修复技艺考》,假装找资料溜进图书馆。木质书架泛着旧木头的香气,
阳光斜斜切进来,在地板上投下窗格的影子。三点整,云层忽然散开,
一道细长的光斑从西窗漏进来,精准地落在第三排书架第三层,像枚金色的书签,
嵌在一本深蓝色封皮的《昆虫记》上。苏晚的指尖在书架上微微发颤。“你在这里做什么?
”冷不丁的声音吓了她一跳。林砚之站在书架另一头,手里拿着平板电脑,
屏幕上是古籍扫描图。他皱着眉,眼镜滑到鼻尖,左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指节抵着布料,
像是在攥着什么东西。“找、找资料。”苏晚把《昆虫记》往身后藏了藏,“你呢?
”“归档。”他低头划着屏幕,语气平淡,可苏晚分明看见,
他的视线越过屏幕落在光斑上时,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接下来的三周,
苏晚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每周三下午三点,她总会找借口出现在第三排书架附近。
林砚之果然也在,有时是蹲在地上整理扫描件,有时只是站着看窗外,
眼神空濛得像蒙着层雾。她发现了更多细节。他总在三点零五分低头看表,
左手从口袋拿出来时,手腕会无意识地摩挲几下。上周他俯身捡掉落的U盘时,
白大褂口袋敞了道缝,露出里面深色的表链——那款式看着就有些年头了,
不像现代的电子表。真正的突破口在一个暴雨夜。项目组加班到十点,苏晚整理修复工具时,
发现林砚之落在会议室的平板电脑没关。屏幕上是他未完成的代码,
背景却是那张老照片的扫描件,文件名是“???.jpg”。
她鬼使神差地点开图片编辑记录,最新一条是调整对比度,
下面附着一行备注:“1932.9.3,文渊阁,晴。”民国二十一年,正是1932年。
走廊传来脚步声,苏晚慌忙关掉页面。林砚之拿着两把伞走进来,
看见她时愣了下:“还没走?”“马上就好。”她的声音发紧,
目光落在他敞开的口袋上——那枚怀表的一角露了出来,金属表面磨得发亮,
边缘有处月牙形的缺口。“你的表”苏晚的指尖在发抖,“能借我看看吗?
”林砚之的脸色瞬间变了,手猛地捂住口袋,像是被烫到一样:“不行。”“为什么?
”苏晚追问,“是不是因为表盖里的字?”他猛地抬头,
黑框眼镜后的眼睛里翻涌着震惊和慌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进了石子。雨越下越大,
敲打着会议室的玻璃窗。林砚之沉默了很久,久到苏晚以为他会直接转身离开,
他却慢慢掏出了那枚怀表。银质的表壳布满划痕,打开时发出“咔嗒”一声轻响。
表盘里的指针早已停摆,表盖内侧刻着两个小字,笔画被磨得很浅,
却依然能看清——“砚之”。日记主人的名字,是“砚之”。而他的名字,是“砚之”。
只差一个偏旁,却隔着近百年的光阴。“每周三下午三点,”苏晚的声音带着颤音,
“你是不是也能看见光斑里的东西?”林砚之的喉结动了动,抬手摘下眼镜,指腹按在眉心。
灯光落在他脸上,左边嘴角的梨涡若隐若现,忽然就有了照片里少年的影子。
“我从小就做一个梦,”他的声音很轻,像雨丝落在青石板上,
“梦里有个穿长衫的人总跟我说,等光斑落在《昆虫记》上时,要记得把怀表还给它的主人。
”他顿了顿,看向苏晚,眼睛亮得惊人,“他说,那个人会拿着半张照片来找我。
”苏晚下意识地摸向口袋——那半张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窗外的雨还在下,
会议室的时钟指向三点零五分。苏晚忽然想起日记里没读完的那句话,在泛黄的纸页末尾,
少年用红墨水补了一行小字:“若你见我,记得告诉我,阿珩等到了光斑,却没等到你。
”她慢慢拿出照片,递到林砚之面前。两张半片的照片拼在一起,
刚好是少年和另一个穿长衫的青年并肩站在图书馆前,青年手里拿着本《昆虫记》,
光斑落在他们交叠的手背上,像颗不会熄灭的星。怀表的齿轮忽然“咔嗒”转动了一下,
停摆的指针开始倒走。林砚之的白大褂口袋里,不知何时多了片干枯的梧桐叶,
和苏晚窗台上那片,一模一样。第二章 梦呓怀表指针倒走的声音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像有只无形的手在拨动时间的齿轮。当指针彻底停在“3”的位置时,
林砚之忽然按住太阳穴,闷哼了一声。“怎么了?”苏晚伸手想去扶他,
指尖刚碰到他的胳膊,就被他猛地避开。“没事。”他把怀表塞回口袋,重新戴上眼镜,
镜片后的目光恢复了平日的冷淡,“雨停了,我送你回去。”一路无话。
研究所门口的梧桐叶被雨水洗得发亮,林砚之撑着伞走在左侧,伞沿刻意往苏晚这边倾斜,
自己的肩膀湿了大半。苏晚几次想开口问什么,都被他避开了眼神。到了苏晚住的老巷口,
他停下脚步:“上去吧。”“林砚之,”苏晚叫住他,“那个穿长衫的人,
在梦里还说过什么?”他的背影僵了僵,过了很久才说:“他说,别弄丢《昆虫记》。
”苏晚回到家,翻出那本民国日记继续读。日记主人叫沈砚之,是金陵大学的学生,
日记里写满了对一个叫“阿珩”的人的惦念。三月十七日:“阿珩今日教我骑自行车,
他扶着后座跑了整条街,白长衫的下摆都沾了泥,却笑说‘砚之你再学不会,
我就要变成车夫了’。”五月二日:“阿珩寄来北平的槐花,说泡在茶里香得很。
我分了些给图书馆的苏先生,他说这香气像极了十年前的北平。”苏先生?苏晚心里一动。
她想起奶奶说过,祖上曾在金陵开古籍修复铺,太爷爷正是姓苏。第二天去研究所,
苏晚特意绕到图书馆,第三排书架的《昆虫记》还在原位。她抽出来翻了翻,
扉页上有行模糊的字迹,像是被水洇过:“赠砚之,愿你永远像光斑一样明亮。
——阿珩”“在看什么?”林砚之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苏晚吓得手一抖,书掉在地上。
林砚之弯腰捡起,指尖触到扉页时,忽然“嘶”了一声。“怎么了?”“没什么。
”他把书递回来,指腹泛红,像是被什么烫到了,“数字化扫描需要这本书,借我用一下。
”他拿着书转身就走,苏晚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僵硬,左手始终插在口袋里,
像是在护着那枚怀表。下午,苏晚去项目组送修复好的古籍扫描件,
听见林砚之的同事在闲聊。“小林今天不对劲啊,上午扫描《昆虫记》时,
盯着扉页看了半小时,问他怎么了,他说看见上面有字。”“何止啊,刚才喝咖啡,
他把糖当成盐往里面撒,还说‘阿珩总爱放这么多糖’,吓我一跳。”苏晚的心沉了沉。
她敲了敲林砚之的工位隔板,他抬头时,眼下有淡淡的青黑。“一起去吃饭?
”她扬了扬手里的餐盒,“我带了红烧肉。”他愣了愣,点了点头。茶水间里,
苏晚把红烧肉推到他面前。他拿起筷子,却迟迟没动。“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苏晚轻声问。林砚之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忽然说:“我小时候总梦到一个院子,院里有棵玉兰树,树下有个石桌,
桌上摆着两碗桂花糕。穿长衫的人坐在对面,说‘砚之,这是城南张记的,你最爱吃的’。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可我从小就不爱吃甜的。”苏晚的心猛地一跳。
日记里七月十六日写着:“阿珩买了城南张记的桂花糕,说要逼我吃半块,
不然就把我的《昆虫记》藏起来。他总说我太瘦,要多吃点甜的。”“那个穿长衫的人,
是不是总穿件月白色的长衫,袖口绣着玉兰花?”苏晚追问。林砚之的筷子顿在半空,
眼睛里闪过一丝茫然:“你怎么知道?
”苏晚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张照片:“沈砚之的日记里写,阿珩有件月白长衫,是他母亲绣的,
袖口的玉兰花能以假乱真。”她指着照片里青年的袖口,“你看。”林砚之凑近看,
指尖轻轻抚过照片上的玉兰花,忽然低低地说了句:“玉兰开的时候,
阿珩总爱摘一朵别在我衬衫口袋里。”这句话说得自然又亲昵,像排练过千百遍。说完,
他自己也愣住了,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个。”“没关系。
”苏晚递给他一张纸巾,“想起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或许我们能一起弄明白。
”接下来的几天,林砚之的“异常”越来越多。他会在整理古籍时,
突然说出某页有虫蛀的痕迹,
而那正是苏晚还没来得及修复的地方;他会在路过图书馆拱门时,下意识地停住脚步,
说“这里以前有块牌匾,上面的字是阿珩写的”;甚至有次,他看到苏晚用金箔补书页,
突然说“要用糯米浆混着金粉,这样才能保存得更久,阿珩教我的”。
苏晚把这些都记在笔记本上,和日记里的内容一一对照,发现惊人地吻合。周五下午,
研究所收到一批新的捐赠古籍,其中有个樟木箱,里面装着几本民国线装书。
苏晚打开箱子时,一股淡淡的玉兰花香飘了出来。箱子底层压着一件叠得整齐的月白长衫,
袖口绣着朵玉兰花,针脚细密,栩栩如生。长衫的口袋里,掉出一本小小的通讯录,
第一页写着“阿珩”,下面是个地址:金陵市鼓楼区文渊巷37号。苏晚的呼吸急促起来。
文渊巷,就是研究所所在的这条巷。她拿着通讯录去找林砚之,他正在给古籍拍扫描图。
看到通讯录上的地址,他突然捂住胸口,脸色发白。“怎么了?”苏晚扶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