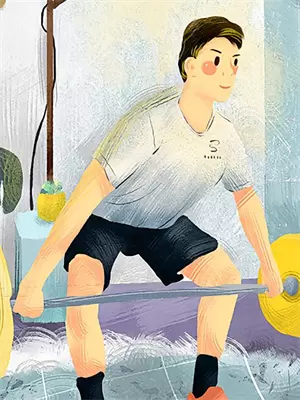
1 画皮镜现世1973年寒冬,送亲队伍在山崖遭遇诡异浓雾。
新娘在祖传梳妆镜中看见自己七窍流血,发出凄厉尖叫。花轿坠崖,
梳妆镜被泥土掩埋整整七十年。直到拆迁队挖出它,我贪便宜搬回家。镜面开始莫名结雾,
深夜自动梳头。我的头发大把脱落,脸上出现诡异抓痕。
村长惊恐警告:“那是秀娥的‘画皮镜’,她在找替身!
”我颤抖着看向镜中——红盖头下的女人正用发簪划开我的脸皮。
她无声翕动嘴唇:“揭我盖头者,剥骨换皮……”---那唢呐声撕扯着1973年的寒夜,
像钝刀子在刮骨头。纸糊的灯笼在风里打晃,光晕昏黄粘腻,活像垂死之人散开的瞳仁。
抬轿的汉子们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湿滑的冻土上,呼出的白气在惨淡月光里凝成鬼爪似的形状。
山崖边的路窄得像鬼门关的门缝,底下黑沉沉一片,深不见底。新娘秀娥端坐在花轿里,
大红的盖头遮住了视线,只有轿帘偶尔被风吹起一条缝,
漏进外面冰冷刺骨的夜色和汉子们压抑的喘息。怀里紧紧搂着那面祖传的紫檀木梳妆镜,
沉甸甸的,冰冷的镜框硌着她的小臂。这是娘压箱底的宝贝,说是能照出百年福气,
保佑新人白头。可此刻,这镜子贴在胸前,却像捂着一块千年寒冰,
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阴气,顺着皮肤丝丝缕缕地往骨头缝里钻。轿子猛地一颠,
她下意识扶住镜框,盖头滑落了一角。轿帘的缝隙恰好被风吹得大开,
月光像一瓢冷水泼了进来,正正打在怀里的镜面上。镜子里映出的,
本该是她年轻姣好的脸庞。可那里面——盖头下本该是红唇的位置,
赫然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脸颊撕裂,露出森白的牙床,眼角淌下蜿蜒浓稠的黑血,
粘稠得像是凝固的墨汁,糊满了半张脸!那双眼睛,只剩下两个血红的窟窿,直勾勾地,
穿透镜面,死死钉在她身上!“啊——!”一声凄厉到非人的尖叫,硬生生劈开了死寂的夜,
盖过了呜咽的唢呐和呼啸的山风。那声音尖利得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每个人的天灵盖。
抬轿的汉子们被这声鬼叫骇得魂飞魄散,脚下一滑,整个轿子瞬间失去了平衡!
沉重的紫檀木梳妆镜从秀娥僵硬的怀里滑脱,“哐当”一声巨响砸在轿底。
就在这电光石火间,一股浓得化不开的白雾,毫无征兆地从悬崖底下翻涌上来,
如同无数冰冷的鬼手,瞬间攫住了整支队伍!“稳住!稳住啊!”领头的汉子嘶哑地吼着,
声音里全是绝望的破音。可太晚了。脚下的路像是突然被抽走,
轿子在令人牙酸的木头断裂声中猛地倾斜,带着秀娥最后那声被浓雾吞噬的惨叫,
直直地坠向那深不见底的、墨汁般的黑暗深渊。轰隆一声闷响,从崖底传来,
随即被翻腾的浓雾彻底吞没。只剩下几片碎裂的红布和纸灯笼的残骸,在冷风中打着旋儿,
缓缓飘落。那面沉重的紫檀木梳妆镜,在泥泞的崖壁上一路翻滚撞击,发出空洞的悲鸣,
最终被塌陷的湿冷泥土和碎石彻底吞没,再无一丝痕迹。2 年沉睡七十年时光,
足以让高山变矮,沧海变桑田。可有些东西,只是沉睡了。七十年后。“轰隆——!
”巨大的挖掘机铲斗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砸下,瞬间撕裂了崖边最后一片残存的土坡。
尘烟如同浑浊的巨浪冲天而起,碎石泥块下雨般簌簌滚落。
阳光惨白地照在裸露出的嶙峋山石上,像一块巨大的、剥了皮的伤口。“王头儿!有东西!
”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小工尖着嗓子喊,声音在机器的轰鸣里显得有些失真。
工头王老五顶着个油腻腻的光头,骂骂咧咧地走过去,一脚踢开几块碎石:“妈的,
挖出金元宝了还是咋的?嚎什么嚎!”他粗鲁地拨开浮土,动作猛地一顿。
半截深色的木头露了出来,沾满了湿泥,但边缘那繁复得有些妖异的雕花,
在尘土里透着一股子格格不入的阴森劲儿。“操!还真有货!”王老五眼睛一亮,
贪婪的光一闪而过。他招呼旁边几个工人,“愣着干啥?快弄出来!轻点儿!
别他妈给老子碰坏了!”他搓着手,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这老物件,转手一卖,
油水指定少不了。几个工人七手八脚地刨着土,渐渐挖出一个半人高的物件。
沉重的紫檀木框架,早已失去了光泽,呈现出一种被岁月和泥土浸透的、死气沉沉的乌黑。
木头上雕刻着纠缠扭曲的蔓草和形态奇诡的鸟雀,那些鸟的眼睛,空洞地镶嵌在木纹里,
仿佛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些打扰者。镜子背面糊满了干结的泥壳,
隐约能看出暗红的底色和一些同样繁复的描金纹路,只是那金也黯淡得像凝固的血渍。
最诡异的是正面。那面椭圆形的镜子,竟然没有碎裂!厚厚的泥垢覆盖了大半镜面,
但露出的几小块地方,依旧光洁得瘆人,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出刺眼、冰冷的光斑,
像死人睁开的眼。“嘶……”一个小工倒抽一口冷气,下意识地缩回了手,“王头儿,
这镜子……有点邪门啊,看着心里发毛。”“毛个屁!”王老五啐了一口,
掩饰着心头莫名掠过的一丝寒意,强作镇定,“值钱的老物件都这样!少见多怪!
”他指挥着,“赶紧的,弄我办公室去!找块破布擦擦!”他瞥了一眼那镜子,
不知是不是错觉,那几块露出的镜面,光线似乎暗了一瞬,映出他自己那张被贪欲扭曲的脸,
格外丑陋。3 镜中诡影我,林晚,
就是那个被王老五哄着接手了这“邪门老物件”的冤大头。
他唾沫横飞地吹嘘着紫檀木的价值,说这是“前清宫里的娘娘用过的宝贝”,
只收了我象征性的两千块“保管费”,还摆出一副“你占了大便宜”的肉痛表情。“林记者,
你是文化人,识货!这东西放你那儿,比在我这工棚吃灰强!”王老五拍着胸脯,
眼神却闪烁不定。我看着角落里那块被工人随意丢在破麻袋上的梳妆台,
紫檀木框在昏暗的工棚里像一块巨大的、凝固的污迹,镜面被泥垢覆盖,
只反射出模糊扭曲的光影。不知怎的,靠近它时,
一股极其细微、难以言喻的寒意就顺着脊椎爬上来,
混杂着泥土深处的腥气和一种……若有若无的陈旧脂粉味。那味道钻进鼻腔,
让人胃里一阵轻微的不适。贪便宜的心理最终压倒了那点不适。我咬咬牙,付了钱,
叫了辆小货车,把这沉重的“古董”运回了我在城郊租住的旧公寓。
梳妆台被安置在卧室角落,正对着我的床。它实在太大了,
像一堵沉默的、散发着阴冷气息的黑墙,瞬间让原本就不算宽敞的房间显得更加逼仄压抑。
我找来湿抹布,仔细擦拭着紫檀木的框架。
那些繁复得令人眼晕的雕花在清水下渐渐显露真容——纠缠的藤蔓如同扭曲的蛇,
怪异的鸟雀空洞的眼睛似乎在木纹里缓缓转动。每擦一下,指尖传来的触感都冰凉刺骨,
仿佛那不是木头,而是某种冷血动物的鳞片。当抹布终于移到那面椭圆形的镜子上时,
我屏住了呼吸。厚厚的泥垢被一点点抹去,露出底下光洁得不可思议的镜面。
它像一泓深不见底的寒潭,清晰地映照出我疲惫的脸和身后凌乱的房间。
镜框边缘镶嵌着几颗小小的、黯淡的石头,大概是某种劣质的水晶或琉璃,
在灯光下反射着幽幽的、不怀好意的微光。擦干净后,
那股子若有若无的陈旧脂粉味似乎更浓了些,幽幽地弥漫在房间里。我皱了皱眉,
打开窗户通风。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喧嚣而温暖,可这温暖似乎被那面镜子隔绝了。
卧室里的空气,依旧沉滞冰冷。第一夜无事发生。
除了那股挥之不去的脂粉味让我睡得不太安稳。第二夜,凌晨两点左右。
我被一种极其细微的、持续不断的“沙沙”声惊醒。
那声音像是有人用指甲在粗糙的纸面上轻轻地、反复地刮擦,
又像是……梳齿缓慢地刮过头皮。声音来自卧室角落。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几乎要撞碎肋骨。房间里一片死寂,只有那“沙沙”声,
固执地钻进耳朵,清晰得令人头皮发麻。我僵硬地转过头,一点一点,像生锈的机器。
目光投向角落里的梳妆台。月光吝啬地从窗帘缝隙挤进来一小缕,
惨白地投射在那面椭圆形的镜子上。镜面一片模糊,仿佛刚被人呵了一大口气,
凝结了一层厚厚的水雾。而就在那片朦胧的雾气中央,一把黄杨木梳子,正一下、一下,
缓慢而执着地……梳着空气!没有手握着它!它就那样凭空悬停在镜子前方几厘米的地方,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冰冷的手操纵着,进行着某种古老而诡异的仪式。
梳齿每一次划过虚无的空气,都带起一声令人牙酸的“沙沙”声。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
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冰冷的恐惧像无数条毒蛇瞬间缠遍全身,勒得我无法呼吸。
那梳子梳动的节奏,带着一种近乎贪婪的耐心。时间仿佛被冻结了,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像一尊石雕,被钉在床上,
眼睁睁看着那把诡异的梳子在惨淡月光下的雾气里,重复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动作。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分钟,也许有半小时。那把悬空的梳子,终于停了下来。
它没有掉落,就那么诡异地悬停在雾气中央。然后,镜面上那层浓密的水雾,
开始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无声无息地消散、退去,如同被一张无形的嘴吸走。
镜面重新变得光洁如新,清晰地映出我因极度恐惧而扭曲惨白的脸,
以及身后空荡荡的房间角落。梳妆台上,空空如也。那把黄杨木梳子,静静地躺在抽屉里,
就在我昨天随手放进去的位置,仿佛从未移动过。我瘫软在床上,浑身被冷汗浸透,
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卧室里静得可怕,只有我粗重得如同破风箱般的喘息声。
那股陈旧脂粉的味道,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浓郁,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带着一种冰冷的、令人作呕的甜腻。4 剥皮替身从那天起,
我的身体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清晨醒来,枕头上不再只是几根落发,
而是一撮一撮,乌黑地纠缠在一起,触目惊心。轻轻一捋头发,指缝间就带下大把的断丝。
镜子里的人,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曾经还算浓密的头发变得稀疏枯黄,头皮清晰可见。
更可怕的是脸上的变化。起初只是几道浅浅的、微红的划痕,像是不小心被指甲刮到。
我以为是睡梦中自己抓的,没太在意。但很快,这些划痕开始加深、延长、蔓延。
它们出现在脸颊、额头、甚至脖颈。颜色由浅红变成深红,继而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暗紫色,
边缘微微肿胀、发硬。摸上去,皮肤底下像是埋着无数细小的冰针,
刺骨的寒意顺着指尖直往骨头缝里钻,伴随着一阵阵麻木和难以忍受的刺痛。我跑遍了医院,
皮肤科、神经科、内分泌科……抽血、化验、CT、核磁共振。医生们拿着各种报告单,
眉头越皱越紧。“林小姐,各项指标都显示……基本正常。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
“你描述的皮肤症状和脱发,我们目前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病变依据。神经性皮炎?
压力性脱发?……但像你这样发展如此迅猛的,确实罕见。”他顿了顿,斟酌着词句,
“或许……考虑一下精神因素?最近是不是压力特别大?或者……生活环境有什么大的改变?
”生活环境?改变?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卧室角落,那个巨大的、沉默的紫檀木阴影。
那面光洁的镜子,此刻正静静地映照着诊室惨白的灯光和我枯槁的面容。
一股寒意猛地攫住了我。走出医院大门,夏日的阳光明晃晃地刺眼,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包里塞满了医生开的镇静剂、营养神经的药和一堆激素药膏,沉甸甸的,
像压着一块绝望的石头。
脸上和头皮那种被无数冰针穿刺、被无形之物抓挠撕扯的痛楚和寒意,
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我的神经。“林晚?”一个带着浓重乡音、迟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猛地回头。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皮肤黝黑布满深刻皱纹的老人站在几步开外,
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他看起来有些面熟,
似乎是……老家邻村的村长,陈伯?“陈伯?”我有些意外,声音因为虚弱而沙哑。
陈伯没有应声,他像是根本没听到我的招呼,那双浑浊的眼睛像钩子一样,
死死地钉在我的脸上,更准确地说是钉在我脸上那些纵横交错、颜色诡异的抓痕上。
他的嘴唇哆嗦着,脸色在阳光下瞬间变得灰败,如同蒙上了一层死气。
“你……你……”他抬起枯树枝般的手指,颤巍巍地指着我,
又猛地指向我来的方向——那是医院,但陈伯的目光仿佛穿透了高楼大厦,
笔直地射向我公寓的方向,射向我卧室里那个该死的梳妆台!他的声音陡然拔高,
尖利得变了调,充满了极度的恐惧:“你沾了那东西?!是不是?!
是不是从崖子口挖出来的那个梳头匣子?!”陈伯枯瘦的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眼睛,
他整个人都在剧烈地颤抖,仿佛看到了世间最恐怖的景象,“那是秀娥的‘画皮镜’啊!
她在找替身!她在找替身啊——!”“画皮镜”?秀娥?替身?这几个词像淬了冰的锥子,
狠狠凿进我的耳朵,直抵天灵盖!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瞬间冻结了四肢百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