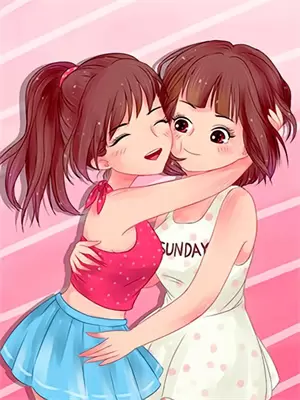
第一章东儿的出生转眼间又到了立冬时节,天地间仿佛被一层冰冷的纱幕所笼罩,
寒风如冰刀般刺骨,呼啸着掠过冷清的街头。行人们紧裹着衣裳,
匆忙的脚步朝着回家的方向奔去,只剩下那颤抖的吆喝声,还在空荡的街头回荡。就在这时,
几声清脆的啼哭声打破了这份寒冷与寂静——我们可爱的主人公王东儿出生了。
在那简陋的产房里,正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只见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
汗珠正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贴在脸颊的几缕头发。漫长而痛苦的分娩过程,
已将她的体力消耗殆尽,可她的眼神却格外明亮。那是初为人母独有的温柔与欣喜。
她微微地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握住身旁刚出生的女儿那粉嘟嘟的小手,
此刻的她仿佛握住了整个世界,像是要把自己全部的爱意与温暖,
都通过这握手的瞬间传递给女儿。接生的奶奶手脚很是麻利,
只见她迅速地给小东儿做了简单的擦拭和包裹,随后快步跑到隔壁屋子,
笑着给爸爸报喜:“王大树啊,你媳妇儿生了,生个大胖女娃呀!
这浓眉大眼和胖嘟嘟的小脸蛋儿,可像你了!还不快来瞧瞧?
”爸爸本就因王家世代单传的压力,内心满是焦虑。
他自幼听着长辈们念叨延续香火的重要性,深知自己肩负着家族的期望。
在这个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村儿里,若是没有儿子,就仿佛断了家族的根脉,
会被邻里指指点点。此时听到接生奶奶的报喜,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眉头紧紧锁成一个“川”字,满脸垂头丧气。只见他缓缓地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仅剩的半支烟,哆嗦着手把烟点燃。独自走到窗前,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寒风拍打着窗户,发出“砰砰”的声响,
却丝毫扰不动他满心的失落与惆怅 。东儿是怀胎时爸爸就取好的名字,
他是多么盼望着能生个男娃啊!第二章东儿的家庭成员听到接生奶奶的报喜后,
只见年过八旬的奶奶,佝偻着背,杵着那根磨得光滑而陈旧的拐杖,
拖着瘦小的身子颤颤巍巍地走到爸爸跟前。她那布满老茧的手,像干枯的树皮,
轻轻地拍了拍爸爸的手背,声音里带着岁月的喑哑:“不打紧,不打紧,明年再生一胎,
准是个大胖小子。” 奶奶是个要强且善良的人,在村子里,不管谁家有个难处,
她总会力所能及地去帮衬。爷爷在爸爸年幼时,去河边打鱼不幸掉入河中,
直到第二天村里人打捞起来时发现爷爷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从此,
奶奶一个人扛起了抚养爸爸的重担。那些年,日子过得特别苦,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为了给爸爸挣口吃的,农忙时奶奶就给人帮工,农闲时就去山里采些草药去集市上换钱。
每到夜深人静时,她总会独自坐在老槐树下喊着爷爷的名字,随后开始念叨起一天的琐事。
也会时常去河边静静地坐着发呆,茶不思饭不想,日子久了,身体也就愈发消瘦。
而作为奶奶悉心养育长大的儿子便是王大树,“我的爸爸”。
这个名字寓意着爸爸要像大树一样粗壮,结实。为我们一家人遮风挡雨,
爸爸作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虽不善言辞,却有着一颗赤诚的心。他为人老实本分,
村里不管谁家有大小事务,只要招呼一声,他二话不说就前去帮忙。哪怕从早忙到晚,
嘴里也不喊声累字,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活儿,都得经过他的这双手。农忙时,
他在田里挥汗如雨,无论是播种、施肥、收割,每一项都得亲力亲为;农闲时,他也不闲着,
不是去帮邻居修农具,就是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挑水劈柴。正因为长期的劳作,
才使他比同龄人显得苍老许多。平日里,没活儿的时候,他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院儿里,
泡上一壶茶水,再点上一支烟,那是他褪去一身疲惫的方式。在他心里,
家人的安稳就是他最大的追求,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我的妈妈叫张花儿,
这是外婆给她取的名字,就希望她像花儿一样美丽,动人。妈妈的性子爽朗又坚韧。
前些年闹饥荒,她从十里外的王家村逃荒过来。当时一起逃荒的有十几个姑娘,
可大多因长时间不进食,赶路时体力不支从而失去了生命。唯有妈妈凭着一股顽强的求生欲,
一直硬撑着,直到瘫倒在路边,幸好被隔壁的陈大娘上山砍柴的途中遇见,
将其救下并好心收留。妈妈有着一双灵动的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像月牙。她手脚很是麻利,
操持家务是把好手,家里总是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她爱说爱笑,
给这个原本有些沉闷的家里带来了许多欢乐,当初陈大娘介绍她与爸爸相识,
就是看中了爸爸的老实和勤快,觉得跟着这样的人,日子虽不富裕,却能过得踏实安稳。
她在这个家,不仅是妻子、母亲,更像是家里的黏合剂,用她的温暖和热情,
维系着一家人的感情。第三章东儿爸爸去砍柴日子虽然有些平凡,但还过得去,
原本以为一家人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可谁知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火辣辣的阳光晒得人只想找阴凉的地方去躲避。
爸爸见着家里的木柴所剩不多了,于是便拿起斧头上山去砍柴。
原本以为一下午的功夫爸爸就能回来,
可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黄昏的脚步急促地笼罩了整个村子。
妈妈把做好的饭菜端到桌上,像往常一样把饭打好,把筷子摆放整齐,
就等着爸爸回来开饭了。接着她静静地站在院子里,望着爸爸去砍柴的方向,
期盼着爸爸回来的身影早些出现。
奶奶杵着拐杖拖着瘦弱的身子走到妈妈身后微微地说道:“今儿是怎么了,
我这眼皮子跳了一下午,该不会是要出啥事儿吧。
”妈妈紧紧地握住奶奶那瘦弱的手并安慰着:“没事儿,妈,应该是您最近没休息好,
加上又做了一下午的针线活儿,有些疲倦了。”奶奶连忙微笑着点了点头:“没事儿就好,
没事儿就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奶奶和妈妈就这样站在院子里等了好一阵子,
却始终不见爸爸回来的身影。正转身往屋里走时,
突然听到村口边刘奶奶家的大孙子牛牛一边朝着院子跑来,一边大声地喊着:“不好了,
不好了,出事儿了,”此时奶奶紧紧地握住妈妈的手,反复地问道:“这是牛牛的声音吗?
是不是朝着咱们家院儿来了?”妈妈焦急地说着:“妈,好像是的,正是牛牛的声音”。
只见牛牛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到奶奶跟前,支支吾吾地说着:“王,王奶奶,不好了,出,
出事儿了。李大叔让,让我来通知你们,快去,去,后山上的石墩边儿,路太黑了,
你们得带,带上火把”。第四章东儿爸爸去世奶奶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
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枯瘦的手死死地攥着妈妈的衣角。声音抖得不成调:“花儿,你说,
到底是不是大树?是不是他出事了啊?”妈妈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奶奶的肩膀,
不停的安慰着奶奶:“妈,您先别急,我扶您进屋歇着,我去去就来。
”随后妈妈急忙从柴房里点燃一根柴火把,跟着牛牛往后山的方向跑去。
山路的石子硌得妈妈的脚生疼,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攥着——她不敢多想,
可又忍不住拼命地想。她多希望那石墩边躺着的是别人,又或是一场荒唐的误会。
妈妈远远地看见石墩旁围满了人,村民们见她来了,自觉地纷纷往两边退去,
像是给她让出一条冰冷的路。牛牛的哭声刺破了此刻的沉默:“花儿婶,那是大树叔叔!
”妈妈的火把“哐当”一声,掉落在地上,火星四溅。石墩上,爸爸一动不动地躺着,
旁边还堆着没捆完的干柴,小腿上几道带着牙印的伤疤不停地流着鲜血。
嘴角还挂着细密的白泡,在暮色里泛着凄冷的光。妈妈颤抖的身体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轻轻用手指伸到爸爸的鼻孔前,去感受爸爸的呼吸。接着又用手掌摸了摸爸爸的胸膛,
“呼吸没了,心跳也停止了”。只见妈妈紧紧地握着拳头,食指被牙齿咬出深深的红痕,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向下滑落。可她喉咙里就像被堵着滚烫的棉絮,
怎么也发不出一点声音。只有肩膀在剧烈地抽噎着,就像狂风里快要被折断的树枝。
村民们也纷纷擦着泪水感叹着:“这大树多好的一个人啊,咋说走就走了呢!”是啊,
“这以后一家人的重担不得又落到花儿一人头上了,”“要赡养八旬的婆婆,
还要照顾这刚出生的东儿,”“还要忙田地里的农活儿”,“哎,
这穷人的命咋就这么苦呢”!就在这时,李大叔正哭丧着脸缓缓地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轻轻地拍了拍妈妈的肩膀,红红的眼眶里带着哽咽而沙哑的声音:“大妹子,
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好受些。”“下午我带着牛牛他爸和牛牛来后山砍柴时,
路上撞见一条毒蛇钻进林子。地上还留着血滴。我们跟着血迹找了过来,
就看见大树哥……”“等我们到的时候,人已经没气了。都怪我们,都怪我们,
要是早些发现……”!李大叔自责地用拳头拍打着地面。夜晚的凉风卷着松涛掠过石墩,
把妈妈的最后一点力气也卷走了。她慢慢蹲下去,额头抵着爸爸冰冷的手背,
这时眼泪终于冲开喉咙,变成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呜咽,在暮色沉沉的后山里荡开,
却又被更深的寂静吞没着。第五章东儿七岁了得知爸爸离世的消息后,奶奶悲痛不已,
她的屋门已经整整关了十天。门缝里漏不出一点声响,只有每日清晨妈妈端去的粥碗,
到了傍晚仍原封不动地放在石阶上,瓷碗边缘凝固着一圈干硬的米渍。到了第十天夜里,
妈妈因担心奶奶只好偷偷地隔着门板只听见一声极轻的叹息,
像是冰棱从屋檐坠落在那冻土上。她悄悄地推开门,
看见奶奶正望着窗外院子里的那张石凳子,那是爸爸生前经常坐的位置。每当忙完农活儿,
爸爸总会泡上一壶茶水,点上一根烟,就独自坐在石凳子上面歇着。奶奶一动不动地望着,
她满是皱纹的眼角泛着红,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妈妈也会常常在夜里惊醒。
床边衣柜的最底下压着爸爸那件缝满补丁的蓝布褂子,每当夜里喂完东儿后她总会点着蜡烛,
把爸爸的蓝布褂子抱在怀里。粗布上还留着淡淡的柴草味儿,袖口磨出的毛边蹭着脸颊,
就像爸爸生前那双粗糙而温暖的手。有时东儿在夜里哭闹的时候,妈妈哄着哄着,
忽然对着空荡的屋子喃喃起来:“大树,你说东儿这眉眼,是不是随你?”可这话音刚落,
眼泪就顺着妈妈的脸颊滑落在东儿熟睡的脸上……时间如梭飞奔,
日子就好比踩着霜花往前挪。转眼几年过去,又到了立冬时节,这是东儿出生的第七个年头。
这天清晨,妈妈刚把东儿从被窝叫起来,就看见奶奶颤颤巍巍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手里捧着个蓝色的布包。“给东儿的,”她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一般。
妈妈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轻轻地打开布包,是件粉白相间的小棉袄。
针脚细密得像蜘蛛网,领口还绣着朵歪歪扭扭的小梅花,“前些日子就缝好了,总觉得手笨,
没敢拿出来。”东儿伸出小胖手去抓棉袄上的线头,奶奶忽然笑了,只是笑着笑着,
眼泪就滚落在棉袄上,洇出个小小的湿痕。下午的阳光难得有些暖和,
看见妈妈正在灶台前忙碌的东儿趴在炕桌上摆弄着奶奶的顶针。“妈妈,锅里啥味儿呀?
咋这么香”。只见小东儿的鼻尖冻得通红,像颗熟透的山楂。妈妈往灶膛里添了把柴,
火光映得她脸颊发亮:“你猜猜?”东儿踮着脚尖往锅台上凑,
被妈妈笑着拍了下屁股:“小馋猫,奶奶说今儿要给你做好吃的,”正说着,
奶奶端着个青花碗从里屋出来,碗里装着两个圆滚滚的鸡蛋,是前几日攒着舍不得吃的。
锅里的蒸汽“咕嘟咕嘟”顶得盖子直响,东儿挣脱了妈妈的手,光着小脚丫,
再次踮起脚尖:“妈妈,我闻见了!是饺子!肉饺子!”妈妈故意皱起眉头:“不对哟,
再闻闻?”东儿把鼻子凑到锅沿边儿,小辫子随着她的小脑袋左右摇晃着:“就是饺子!
妈妈骗人!”说着就去拽妈妈的衣角,妈妈笑着往院儿里跑去,
东儿跟在后头迈着小短腿追赶。坐在屋门口的奶奶微笑地看着,手里还攥着没纳完的鞋底。
阳光穿过她花白的头发,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锅里的饺子在沸腾的水里翻滚着,
扑鼻而来的香气混着柴火的烟味飘满了整个小院儿。这是爸爸走后,
这个家头一次散发出这么浓的烟火气。妈妈被东儿拽着衣角绊倒在柴堆上,娘俩滚作一团。
在东儿咯咯的笑声里,妈妈忽然看见院墙角爸爸生前种下的那棵石榴树,
枝桠上还挂着几个干硬的空果壳儿,在风里轻轻摇晃着,像是在点头应和着这久违的热闹。
然而好景不长,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第六章东儿和妈妈去抓鱼冬去春来,花谢花开,
院角的樱桃花落了满地,新抽的绿芽裹着晨露,随着微风的吹拂轻轻摇晃着。天刚蒙蒙亮,
东儿还在被窝里翻了个身,就听见院外传来一阵劈柴的脆响声,“哦!是妈妈砍柴回来了。
”东儿坐起身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便看见妈妈肩上搭着块半湿的粗布帕子,
鬓角还挂着汗珠。怀里抱着的柴捆比她人还高,脚步却轻快得很,
身影在灶房和柴房之间来回旋转,很快就飘来一阵窝窝头和米粥的香气。“东儿,
起来吃早饭咯。”妈妈掀开门帘时,围裙上还沾着灶灰,手里端着的瓷碗里,
粥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米油。东儿光着小脚丫踩在微凉的泥地上,很快就蹿到灶台边儿。
刚要伸手去抓窝窝头,就被妈妈轻轻地拍了下手背:“慢些,小心烫手哦。
”她朝着妈妈吐了吐舌头,乖乖地端起自己的小碗。
跑到门口的老槐树下——奶奶正坐在石墩子上纳着鞋底,手里的银针在布面上穿梭,
线轴在膝头转得嗡嗡直响。“奶奶先吃。”东儿快速地把碗递了过去,
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两个温热的窝窝头,热气熏得她的小鼻尖通红。奶奶抬起头,
放下手中的针线接过碗,小口小口地抿着米粥,另一只枯瘦的手轻轻捏了捏东儿的小脸蛋儿。
手指头还带着被针线活儿磨出的薄茧,蹭得东儿咯咯直笑:“小馋猫,奶奶早吃过啦,
灶台上还给你留着刚煮熟的鸡蛋呢,快去趁热吃吧。”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向地面,
在奶奶银白色的发丝上跳动着碎金似的光片,东儿凑了过去,
闻着奶奶身上的皂角香味儿开心地笑着。吃过早饭后的东儿像只小尾巴似的黏在妈妈的身后,
妈妈去喂猪时。她就蹲在猪圈边数着小猪仔;妈妈去晒谷时,她就抓起谷粒往天上撒,
她不停地拽着妈妈的衣角晃啊晃:“妈妈,你带我去河边抓鱼嘛,
你看牛牛哥昨天抓回几条金闪闪的小鱼,装在玻璃瓶里可好看了!”她仰着个小脸,
眼睛瞪得圆圆的,手指还在半空中不停地比划着,“我保证不玩水,
我就坐在石头上看着你抓,好不好?”“好不好嘛”。这时,
妈妈正在擦农具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看着女儿额头前的碎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鼻尖上还沾着些刚晒的谷糠,她放下抹布,伸手把东儿的头发别到耳后。
用严肃的话语说着:“河边石头很滑,得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跟着走,不许乱跑。
”听到妈妈的准许后,东儿立刻转身就跑去柴房翻出那只掉完油漆的小木桶,
桶底还残留着去年装过的桑葚紫渍,她拎着桶蹦蹦跳跳地向着村角的方向走去,
轻快的脚步就像踩着弹簧。出门时,妈妈回头望了眼老槐树下,
奶奶还坐在那儿低着头认真地纳着鞋底,针脚在布面上排得整整齐齐。“妈,您要是累了,
就回屋躺会儿,我们抓两条小鱼就回来。”妈妈的声音里带着微笑,
此刻的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几乎要碰到奶奶的布鞋。奶奶抬起头,
挥了挥手里的针线:“去吧去吧,河边儿风大,给东儿把外套披上,早去早回啊。
”妈妈的目光追着东儿蹦蹦跳跳的背影,随后渐渐地消失在村口的石桥后面。
微风吹着老槐树的叶子沙沙直响,奶奶低头继续纳着鞋底。针尖穿过布面的瞬间,
她忽然愣了愣——看了眼空荡荡的村口,又继续纳着鞋底。可谁也没料到,
那句“早去早回”,竟成了她对儿媳最后的叮嘱,
…第七章东儿妈妈去世来到河岸边的东儿高兴地趴在一块光滑的石板上数着水里的小鱼,
手指戳着水面惊起一圈圈涟漪。妈妈把前几日新做的红色碎花布衫铺在石头上晾晒,
袖口上还沾着清晨干活时留下的小泥点儿。“你看这红红的小尾巴和圆滚滚的小肚子,
怕是怀了小鱼崽了吧”。妈妈蹲下来,掌心轻轻地贴在水面上,
只见几条金色的小鱼不停地摇摆着尾巴游过来蹭她的手指。东儿咯咯地笑着,
突然看见对岸的牛牛举着竹篓挥手,竹篓里晃着几条银闪闪的白条。“妈妈,咱们也去那边!
”她拽着妈妈的衣角晃啊晃,“等等”,
妈妈把晒好的红布衫叠成方方正正的一块塞进木桶里。随后拿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罐子,
“先把刚抓的小鱼放进去,省得等会儿跑了。”罐子里清澈的水还在摇晃着。
当妈妈紧紧地牵着东儿的小手过河时,瞧着东儿的鞋底有些薄,
她便让东儿踩着自己的鞋跟走。“慢点儿,石凳子很滑,
去年王奶奶家的老伴儿就是在这儿摔下去的。”话音刚落,突然东儿指着水里大喊:“妈妈,
快看,那鱼在往上跑呢!”水流不断地在河中央打着漩涡,那条银色的小鱼像一片碎银子,
拼了命地往上游。东儿突然探头时脚下猛地一滑,天旋地转间,
她只闻到妈妈衣襟上皂角的清香,紧接着便是刺骨的凉水漫过全身。
“妈妈”瞬间妈妈的布衫在水面上绽开出一朵白色的莲花,东儿在水里不停地扑腾着。
只见妈妈的手抓了过来,她被猛地往上一托,屁股磕在石凳子上面硌得生疼,
可妈妈的手却突然松开了。原来是无数颗水草死死地缠着她的裤脚将她往下拽,
只看见妈妈的头在水里浮浮沉沉。“妈妈”,东儿想要伸手去抓住妈妈,可是水流太急,
妈妈的身影也跟着往下游去,就像一片被风吹走的叶子。东儿不停地大声喊着:“快来人啊,
快救救妈妈,妈妈掉下去了。”她不停地抹着眼泪,牛牛见状后赶紧跑去通知村名。
牛牛妈也跑了过来背着东儿一边喊着“花儿姐,你在哪儿,
”一边朝着妈妈被冲走的方向跑去,却始终不见妈妈的身影。当村名们赶到已是黄昏时分,
李大叔二话不说脱去上衣便顺着妈妈被冲走的方向跳了下去。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看到李大叔把妈妈抱上了岸,她的头发上还缠着许多水草,
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东儿一下子扑了过去,她摸着妈妈冰凉的身体,
手里还紧紧地握着几条小鱼,东儿不停地摇晃着妈妈的身体。“妈妈,你醒醒,你快醒醒,
咱们回家,东儿不抓鱼了,东儿以后都不抓鱼了。你快醒醒啊”。
这时牛牛妈妈用力地把东儿抱到一旁,李大叔快速地按压着妈妈的胸口,
那沉闷的声音狠狠地捶在每个人的心上。东儿用力挣脱开牛牛妈妈的手,
再次扑到了妈妈的身上。“妈妈,我再也不抓鱼了,也不淘气了,你起来骂我吧,
你骂我不听话,骂我笨,或者你打我都行,求求你快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家,
奶奶还在等着我们”。听着东儿的哭泣声和哀求声,
就像是一把尖锐的刀子不断地刺痛着所有人的心。村民们也纷纷跟着抹泪,跟着抽泣,
不断地感叹着:“这小女孩的一生怎么这么坎坷呀”。“是啊,这回父母都走了,
就留下八旬的奶奶和她作伴了,”“小东儿还是个孩子啊,她也才七岁,
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凉风卷着晚霞掠过河面,把东儿的哭声狠狠地撕成了碎片。
在妈妈冰冷的身体旁,只见那罐摔碎在石头上的小鱼,它们在渐渐干涸的水洼里蹦跳着,
就像无数颗碎落在地上的星星。第八章东儿被牛牛家收养在这万物复苏,
生机勃勃的美好季节里,东儿的世界却因妈妈的离去一夜之间彻底变成了黑白色。
村里的大伙儿们帮忙办理了妈妈的后事。下葬那天,东儿蜷缩着小小的身子,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河岸边。眼神空洞地看着河面,她多希望时间能够倒回抓鱼的那天,
她多希望她跟妈妈没有来抓鱼,她多希望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可她只是用着沙哑的声音轻轻地对着河面说了一句:“妈妈,东儿今后再也不抓鱼了,
因为东儿不喜欢小鱼,东儿最讨厌抓鱼了,以后东儿也会乖乖听话,
乖乖听奶奶的话”……最近东儿没有像往常那般早起,而是整日缩在冰凉的土炕上。
裹着打满补丁的旧棉被,奶奶端来的玉米糊在炕边放凉了,还结了层薄薄的膜。
她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也许是妈妈走了,
那口热乎气儿好像也跟着散去了……奶奶的咳嗽声也越来越严重了,
夜里时常能听见她在灶房偷偷地抹泪。才不过半月,奶奶原本就佝偻的背现在变得更驼了,
银白色的头发上像落满了雪霜。有一回她想去给东儿热饭,刚挪到门槛边儿,
就踉跄着往下倒去。幸亏路过的二婶子遇见了连忙跑过来扶了她一把,
她才不至于摔在冰冷的泥地上。“哎哟,王大娘啊,
你这身子骨……”二婶子红着眼圈儿轻轻地叹了叹气。奶奶只是摆摆手,
在她枯瘦的手背上一根根显露的青筋就像颗老树根似的盘虬着。
近日王大伯隔三差五就背来一捆干柴,
码在灶房墙角;李嫂子挎着竹篮送来几个刚蒸的窝窝头,
那热乎气儿能暖半个炕;连最淘气的小石头,都学着大人的模样,
把自己攒的野栗子倒进东儿的布兜里。大伙儿对咱家的帮衬奶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反复地叮嘱着小东儿以后长大了要记得感谢大伙儿。
奶奶杵着她那光滑而陈旧的拐杖站在屋门口,眼神空洞地望着院儿里的那颗老槐树,
心里跟明镜儿似的:“我这把老骨头,怕是熬不了多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