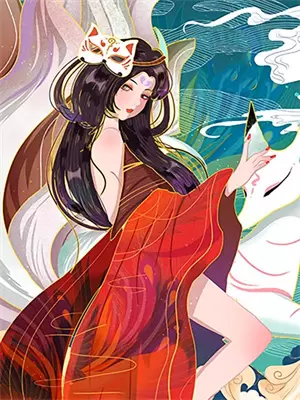张单生在西汉初年的南阳郡,村东头的歪脖子柳树下就是他家的茅舍。
爹娘是种庄稼的老实人,爹总爱在犁地时哼着 “灶火暖,日子甜” 的调子,
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 “单”,盼他这辈子像灶膛里的火苗,安安稳稳烧着就好。
可这孩子打小就不一般,别家娃娃追着蝴蝶跑,他总蹲在灶房门口的青石板上,
看娘往灶膛里添柴时,火苗如何顺着柴缝钻,如何把锅底舔得发亮。他还爱捡些碎瓦片,
在地上垒出巴掌大的迷你小灶,用晒干的蒲公英绒当柴,嘴里念叨着 “添柴要空心,
烧火要实心”,那认真的模样,常惹得路过的婶子们笑:“这娃怕不是灶王爷托生的。
”七岁那年秋收,金黄的谷穗压弯了田埂,爹却在打谷场被脱粒的石碾砸伤了腿。
血顺着裤管流进泥土里,染红了半捆刚割的谷子,家里的顶梁柱就这么塌了。
娘白天要下地挣工分,手指被镰刀割出的口子缠着布条,夜里就在油灯下缝补浆洗,
常常累得趴在灶台上打盹,额头抵着冰凉的铁锅。张单看在眼里,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
踩着小板凳往灶膛里添柴。他记得娘说过 “火要虚,人要实”,总把柴火架得松松的,
让火苗能自在地窜。有回他把红薯埋在灶膛的余烬里,想给娘个惊喜,
却被隔壁二丫喊去摸鱼,忘了时辰。等娘披着星光从地里回来,红薯已烤成了焦炭,
黑黢黢的像块烧过的石头。他蹲在灶前哭,眼泪砸在灶台上的水渍里,娘却笑着剥开焦皮,
掏出里面还软乎的芯:“咱单儿有心,这红薯焦得有滋味,像咱日子里的甜。
”九岁那年冬天,雪下得能没过膝盖,村里的老灶匠王瘸子得了风寒,缩在漏风的土坯房里,
连口热汤都喝不上。王瘸子年轻时修灶摔断了腿,无儿无女,靠给人修灶糊口,
工具箱里的铁锨比他还老。张单每天提着陶罐,把家里省出的米汤送到王瘸子家,
罐子外面裹着娘的旧头巾,怕汤在路上凉了。他还学着大人的样子,
用布蘸着爹喝的烈酒给老人擦手心,酒气混着药味,呛得他直皱眉。
某天王瘸子咳得像拉风箱,指着墙角的工具箱说:“娃,想学修灶不?这手艺能换口饭吃,
还能看清人心。” 张单眨巴着冻得通红的眼睛点头,从此每天做完功课,
就蹲在王瘸子床边的草堆上,看他枯瘦的手指比划着讲灶膛的构造:“灶膛要像人的肚子,
上窄下宽才装得住火气;灶门要留三分斜,风才能顺顺当当往里走,就像做人要懂转弯。
” 王瘸子还教他认灶土,捏起一撮黄土在他手心搓:“你看这土,要攥成团不散,
摔在地上能裂开,才配得上灶王爷的窝。”十二岁生辰那天,
王瘸子把那柄磨得发亮的铁锨送给了他。锨柄被几代人攥得油光水滑,
靠近刃口的地方刻着个歪歪扭扭的 “灶” 字。“这是我师父传下来的,
” 老人喘着气说,“修灶先修心,心不正,灶火就歪,烧出来的饭都带着苦味。
” 当天下午,邻村的李大户家新砌的灶总烧不旺,请来三个灶匠都没辙,
气得李大户摔了新买的铁锅。张单背着工具箱赶去时,
正见李大户的管家拿鞭子抽砌灶的帮工。他蹲在灶前观察半晌,
灶膛里的火苗有气无力地舔着锅底,像只病蔫蔫的猫。张单伸出手指敲了敲灶壁,
“咚咚” 的空响里带着闷声,他操起铁锨在灶膛底部轻轻一撬,
竟挖出块拳头大的石头 —— 原是砌灶的帮工偷工减料,把废石填在了灶心,想省些好土。
他重新垒好灶膛,又在灶门两侧各嵌了块碎瓷片,“这叫‘引火石’,太阳一照就聚热,
灶王爷见了也欢喜。” 等李大户往灶里添柴,火苗 “腾” 地窜起半尺高,
铁锅很快就冒了热气,惊得众人直咋舌,李大户当场就赏了张单两串铜钱,他却只拿了一串,
说:“另一串给帮工兄弟吧,天怪冷的。”十五岁那年,南阳郡闹旱灾,井里的水见了底,
井底裂开的缝能塞进手指。村民们要走几十里路去河里挑水,扁担压得肩膀红肿,
水桶晃悠着洒一路,到家只剩半桶浑水。张单看着娘挑水时佝偻的背影,脊梁弯得像张弓,
心里直发酸。他想起王瘸子说过 “地下有水气,灶火能感应,火旺水近,火弱水远”,
便带着铁锨在村里转悠。哪家的灶火烧起来 “扑扑” 发闷,像被捂住了嘴,
他就在灶旁做个记号,用石灰画个小小的水纹。三日后,
他在村西头的老槐树下画了个圈:“在这儿挖井,准有水。” 村民们半信半疑,
有人说这毛头小子瞎胡闹,村长却拍板:“单儿这娃实诚,让他试试。
” 挖井的汉子们抡着镐头,挖到三丈深时,镐头突然 “当” 地一响,
接着就听见 “咕嘟” 的水声,清冽的泉水顺着石缝涌出来,映着太阳闪闪发亮。
泉水顺着他设计的竹管流进各家灶房,连烧水都比往常快了许多,
锅里的水 “哗哗” 地翻着花,像在唱歌。王瘸子拄着拐杖来看,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
摸着张单的头说:“你这不是修灶,是在修人心啊,人心顺了,日子就不渴了。
”十八岁那年,梧桐花落在灶台的时节,王瘸子撒手人寰。临终前,
老人从枕下摸出个油布包,里面是那包独门泥料秘方,纸页泛黄,边角都磨圆了。
“陈年灶心土要晒够三百六十日,风吹雨打都不能收,” 老人的声音轻得像羽毛,
“鸡蛋清得是头窝鸡下的,带着晨露的气;发酵时要对着月亮说三句好话,‘愿家家灶火旺,
愿户户有热汤,愿人人心不凉’。” 张单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磕在青砖上,
闷响传得很远,他把秘方贴身藏好,从此接过了老人的工具箱,成了村里新的 “小灶王”。
他走街串巷时,总在货担一头挂个竹筐,专门收集各家换下来的旧铁锅。
敲敲打打改成喂猪的食槽,边缘磨得光滑,送给家里困难的农户。有回路过山神庙,
看见个讨饭的孩子在啃树皮,树皮上还带着泥,孩子啃得满脸通红。
他把刚挣的铜钱全换了馒头,看着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自己饿着肚子走了三十里路回家,
夜里饿得睡不着,就喝口灶上的热水,心里却暖乎乎的。二十岁那年春天,
他在洛阳城的集市上摆摊,货担旁插着块木牌,写着 “张单修灶,保您火旺”。
正低头打磨铁锨,忽听旁边酒肆里吵吵嚷嚷。见个穿华服的公子哥正打骂店小二,
只因端上来的汤面烫了嘴,青瓷碗摔在地上碎成八瓣,热汤溅了店小二一裤腿。
张单忍不住上前劝:“公子息怒,灶火煮出来的东西,带着烟火气,哪能没点烫嘴的热乎劲?
凉了的汤面,就像没了魂的人,不好吃了。” 公子哥恼了,抬脚就踹翻了他的货担,
铁锨 “哐当” 掉在地上,磕出个新的豁口,像咧着嘴在哭。张单没跟他计较,
捡起铁锨时,眼角的余光瞥见旁边包子铺的灶台在冒烟,黑灰色的烟裹着火星子往外窜。
跑去一看,原来是灶膛裂缝漏火,引燃了旁边的柴堆,火星子正往油桶上飘。
他抄起铁锨铲土灭火,手背被火星燎出个水泡,火辣辣地疼,
却笑着对掌柜说:“我给你修修灶,保准以后不裂缝,蒸出来的包子能香三条街。”就这样,
张单的名声渐渐传开,从南阳到洛阳,人们都知道有个心善手巧的年轻灶匠。
他的铁锨上的豁口越来越多,每个豁口都藏着段故事:有的是帮孤儿修灶时,
铁锨磕在石头上留的;有的是为救落水孩童时,
在岸边乱碰蹭的;还有的是驱赶恶犬护着老妇人时,被狗咬在锨柄上留下的牙印。
而那包独门泥料,他总也用不完,有人说他是得了灶神相助,也有人说,是他心里的善念,
让泥土都有了灵性,用一点就能长出一点,像春天的种子。
以下接前文三十岁之后的故事三十岁那年深秋,洛阳城西南隅起了场大火。
北风卷着火星子窜得比城楼还高,像条火龙在天上翻滚。
半条街的草房在噼啪声中蜷成焦黑的木架,浓烟遮得日头都成了昏黄的铜钱,
呛得人睁不开眼。张单刚巧挑着货担路过,货担里的铁锨还带着余温,
是刚给城西的豆腐坊修完灶。他听见火场里传来微弱的哭喊,像只受伤的小猫,循声找去,
正撞见个白发老妇人在火场里摸索,枯瘦的手指在坍塌的屋梁下乱抓,指甲缝里全是黑灰,
嘴里含糊地喊着 “我的绣花鞋,给孙媳妇做的”。“娘哎 ——” 他扯开嗓子喊着,
把货担往地上一摔,扯过旁边染坊晾晒的蓝布被单,在水缸里浸得透湿,连头带脸裹住,
闷着头就冲进浓烟。?火烫的木渣子掉在背上,像无数根烧红的针在扎,疼得他龇牙咧嘴。
他在呛人的烟里摸到老妇人枯冷的手,那手冰凉得像块铁,
才发现她眼窝是空的 —— 原是个瞎眼老太,年轻时哭瞎的,
脚上的绣花鞋早被火星烧了个洞,露出的脚趾冻得发紫。“跟我走!
” 张单背起老太往外冲时,一根烧断的横梁带着火星 “呼” 地砸在他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