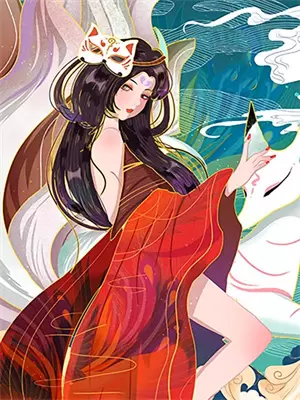林越在一阵剧烈的眩晕中睁开眼,刺目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挣扎着坐起身,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颠簸的马车里,
身上穿着的粗布麻衣散发着淡淡的草药味。“醒了?” 一个清朗的声音从车外传来,
随即车帘被掀开,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男子约莫二十七八岁年纪,身着月白道袍,
发髻用一根木簪束起,眼神清澈如溪。林越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得发不出声音。
他记得自己明明是在图书馆查阅敦煌遗书,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种地方?
那些记载着佛教东传历史的残卷仿佛还在眼前,其中《三教论衡》的抄本尤其让他着迷。
“贫道清虚,自终南山而来。” 男子递过一个水囊,“三日前在山涧发现你昏迷不醒,
看衣着并非本地人氏,不知如何称呼?”“林越……” 他接过水囊一饮而尽,
冰凉的泉水让混沌的头脑清醒了几分,“这里是哪里?现在是什么年代?
”清虚挑眉:“此地乃长安城南,如今是开元二十三年。看你的样子,莫不是摔坏了头?
”开元二十三年?林越心头巨震。公元 735 年,正是盛唐气象最盛之时,
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代。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
那本随身携带的《唐代佛教与本土文化交融》竟然还在怀里,只是封皮已经被水渍浸透。
“多谢道长搭救。” 林越定了定神,决定暂时隐瞒穿越的事实,“在下家乡遭了灾,
一路流落至此,实在不知身在何处。”“原来如此。” 清虚颔首,“我正要前往大慈恩寺,
参加三教论道大会。你若无处可去,不妨随我同行,寺中或许能给你寻个杂役的差事。
”大慈恩寺!三教论道!林越的心脏猛地一跳。
这正是他研究的核心课题 —— 佛教自东汉传入后,历经数百年发展,
到唐代已与本土的道教、儒教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而三教论道正是这种文化碰撞最直接的体现。马车驶入长安城时,林越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朱雀大街上车水马龙,胡商牵着骆驼穿行其间,身着各色服饰的行人摩肩接踵。
街边酒肆传出胡姬的琵琶声,与道观的钟磬、佛寺的梵呗交相辉映,构成一曲盛唐的交响。
大慈恩寺的山门巍峨壮丽,朱红漆门上方悬挂着唐太宗亲题的匾额。进得寺来,
只见殿宇连绵,香火鼎盛。往来僧俗中,既有身披袈裟的高僧,也有身着道袍的羽士,
更有头戴襆头的儒士,各色人等往来穿梭,竟无丝毫隔阂。“三教论道明日正式开始,
今日各方正在准备。” 清虚带着林越穿过庭院,“此次论道由玄宗皇帝亲自主持,
意在调和三教,共辅大唐。”林越注意到,
寺中不少建筑都体现着奇特的融合 —— 观音像的衣饰带着明显的汉服特征,
而大雄宝殿的鸱吻却采用了道教的龙形装饰。这种文化交融的细节,比任何史书都来得直观。
当晚,林越躺在僧舍的硬板床上,辗转难眠。他翻开那本湿透的书,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但脑海中的知识却愈发清晰。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吸收儒道思想,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而道教也在与佛教的论争中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甚至借鉴了佛教的寺院制度。儒家更是从佛教中汲取养分,发展出宋明理学。
……1 菩提院:壁画前的论争第一日?菩提院:壁画前的论争次日清晨,
论道大会在寺中的菩提院举行。菩提院四周古柏参天,树干上布满岁月雕琢的沟壑,
晨雾如轻纱般缭绕其间,将院墙上那幅三教合一壁画晕染得愈发朦胧。壁画中,
老子骑牛的姿态悠然自得,牛蹄下的祥云似在缓缓流动;佛陀结跏趺坐,
衣袂的褶皱间仿佛有金光流转;孔子立于二人之间,双手作揖,神色谦和。三人目光交汇,
似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殿内,三足铜炉中升起的檀香与柏木的清香缠绕着上升,
在梁间凝聚成淡淡的云霭。三百余众分坐两侧,
僧人的袈裟、道士的法袍、儒士的锦袍在晨光中交织出斑斓的色彩,衣袂翻动时带起的气流,
让烛火微微摇曳。林越站在殿外廊下,目光穿过敞开的殿门,将殿内景象尽收眼底。
玄奘法师身披的紫袈裟上,金线绣就的卍字图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他端坐于铺着明黄色锦缎的法座上,案前的青铜烛台雕刻着缠枝莲纹,
《大藏经》抄本的封面用朱砂题写着经名,边角已被摩挲得发亮。
司马承祯所坐的青玉蒲团莹润通透,旁侧的桃木剑剑身刻着北斗七星,
剑穗上的五色流苏垂落在地。贺知章的案几是整块紫檀木雕琢而成,
上面陈列的《论语》用蓝布封套包裹,青铜酒爵的三足雕刻成兽首模样,
爵沿还留着淡淡的酒痕。玄宗皇帝的龙椅设在三阶高台之上,
椅背上的金龙仿佛要挣脱木刻的束缚,背后屏风上的日月山河图中,江水用螺钿镶嵌,
在光影下如真水流动。玄奘法师首先开言,声音洪亮如钟磬撞响,
震得梁上积尘簌簌飘落:“佛法无边,普度众生。然东土有圣人之教,亦能导人向善。
贫僧以为,佛儒虽异,其归一也。” 他指尖轻叩《金刚经》,书页翻动时发出清脆的声响,
“《金刚经》言‘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譬如《维摩诘经》‘入污泥而不染’,
与儒家‘出淤泥而不染’之意相通。众生皆有佛性,正如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
差别只在是否觉悟。”“荒谬!” 殿外一位捧着《孝经》的儒生突然站起,
锦袍上绣着的黼黻纹因激动而抖动,腰间的玉带撞击出清脆的声响。
他将《孝经》重重拍在案上,书页散开,露出里面朱笔圈点的痕迹:“佛家弟子抛家弃亲,
剃发毁形,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相悖,何谈归一?《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昔日颜回事亲至孝,曾子临终易箦,皆为守礼之典范,
佛家弟子能及吗?”玄奘坦然应答,指尖滑过案上一片刚摘下的菩提叶,叶尖的露珠滴落,
在案上晕开一小片水痕:“施主有所不知。我佛弟子以‘上报四重恩’为要,父母恩居首。
《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于饿鬼道,佛陀为净饭王说法四十九日,皆为孝行。”随后,
他突然提高声音,目光如炬,“《梵网经》明言‘孝顺父母师僧’,出家非无孝,
乃是以大孝求众生解脱。”说完,他举起菩提叶,阳光透过叶片的脉络,
在地上投下细密的光影,“就如这菩提叶,落地看似凋零,实则滋养根基,待到来年,
新叶便会从同一枝头萌发,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施主只知‘身体发肤’之孝,
却不知‘救度父母出轮回’之大孝,正如只见叶之凋零,不见根之新生。”“哼,强词夺理!
” 那儒生冷笑,“《礼记》有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佛家弟子既不事生,又不祭祖,空谈轮回,何孝之有?
”玄奘法师从容回击:“施主可知《大方便佛报恩经》?经中言‘父母之恩,深如大海,
广如虚空’,我佛弟子虽不居家,却以诵经回向父母,以功德超度先祖,此乃‘法孝’,
较之于世俗之礼,更胜一筹。昔日目连之母堕入恶道,非世俗葬礼所能救,
唯有佛法方能解脱,可见孝有深浅,不可一概而论。”司马承祯抚须轻笑,
花白的胡须在胸前微微晃动,桃木剑在案上轻叩,发出 “笃笃” 的声响:“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佛道同源,本是一体。《南华经》云‘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此乃至理。佛说‘诸法空相’,却不知空即是道,道即是空,
何必另立门户?” 他从袖中取出一卷《抱朴子》,书页泛黄,上面有蝇头小楷的批注,
“昔年葛洪在《抱朴子》言‘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本末早有定论。
”人群中一位年轻道士霍然起身,道袍下摆扫过身旁的丹炉,火星溅起,
落在青砖上烫出细小的黑点。他手中握着一本《楞严经》,
书页上用墨笔写满了注解:“师父所言极是!弟子读《楞严经》‘常住真心性净明体’,
此‘真心’不正是我道‘元神’吗?何必绕舌称‘佛性’?就像这丹炉,道家用来炼丹,
佛家却要换个名字叫‘宝鼎’,实则一物也!”“痴儿浅见。” 司马承祯摇头,
取过案上的玉如意,如意头部的云纹在晨光中流转,“道佛如登山,东麓西峰路径不同,
登顶后所见日月并无二致。” 他话锋一转,看向玄奘,“然法师说佛儒归一,
贫道却不敢苟同。《道德经》言‘大道废,有仁义’,儒家标榜仁义,恰是大道崩坏之兆,
佛家执着于慈悲,亦是同理。”玄奘法师挑眉反驳:“道长此言差矣。
《法华经》言‘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此慈悲非刻意标榜,乃是本性流露。正如儒家仁义,
本是人心固有,何来‘执着’之说?就像这阳光普照,难道是刻意为之?”贺知章站起身,
腰间的金鱼符碰撞出悦耳的声响。他举起青铜酒爵,将其中的酒液一饮而尽,
酒液顺着嘴角流下,他用袖角轻轻拭去:“臣以为,三教如鼎之三足。儒家明伦理,
道教养心性,佛教劝善业。”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所过之处,众人皆敛声屏气。
“昔日汉武尊儒,却也遣方士入海求仙;梁武佞佛,仍以《周礼》治天下。
可见三教本就相辅相成,若论高下,便是舍本逐末了。” 他将酒爵顿在案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董仲舒曾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百年之后,道佛依旧盛行,
足见其存在之必然。就如这殿宇,需梁柱儒支撑,彩绘道装饰,香火佛供奉,
方能成其庄严。”一位老僧突然合十,念珠在指间转动,发出 “嗒嗒” 的声响。
他眉须皆白,脸上的皱纹如刀刻一般:“贺学士既言相辅相成,然近日关中大旱,赤地千里,
百姓流离。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教求‘长生久视’,佛家说‘因果业报’,
敢问哪家能解眼前之困?”贺知章指向殿外,
那里有几个小沙弥正提着水桶浇灌枯槁的草木:“老僧问得好!大旱之时,
儒家当行‘荒政’,开仓放粮,遣官赈灾;道教可设坛祈雨,调和阴阳;佛家能施粥济贫,
超度亡魂。” 他引用《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
本就是儒家古礼,与道教祈雨何异?去年河南水灾,
正是官府开仓儒、道士作法道、僧人施药佛,三方合力,才得平安度过。
” 他走到殿门处,指着院中的古柏,“就如这殿外古柏,需根茎儒深扎于土,
汲取养分;枝叶道舒展于空,承接雨露;还需僧人时常修剪佛,除去枯枝,
方能参天耸立,荫庇众生。”老僧追问:“若论救灾,佛家确能施粥,然‘因果业报’之说,
难道要百姓自认前世造业,逆来顺受?”玄奘法师接口道:“老僧此言片面。
《业报差别经》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非是让人逆来顺受,乃是警醒世人行善避恶。就像这干旱,既是天灾,亦是人祸,
官府赈灾是解燃眉,劝人积善是断根由,二者缺一不可。”司马承祯冷笑:“法师说人祸,
贫道却以为是天道循环。《阴符经》言‘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大旱乃是阴阳失调,
唯有修道之人调和元气,方能祈得甘霖,非儒家政令、佛家经咒所能为。
”“道长未免太小看政令之力!” 一位年轻儒士反驳,
“《荀子?富国》言‘善治者使民安其居,乐其业’,若官府平日兴修水利,
何至今日大旱成灾?道教祈雨不过是治标,儒家治水方是治本!”一时间,殿内各执一词,
争论不休。林越转头看向身旁的苏绾,发现她正凝视着壁画,眉头微蹙,似在思索着什么。
晨光落在她握着《金刚经》的手上,指尖的银钏反射出细碎的光芒。“林公子觉得,
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 苏绾忽然转头问道,眼中带着一丝好奇。
林越望着殿内仍在继续的论争,沉吟道:“或许,他们说得都有道理。就像这阳光,
穿过不同的窗棂,会投下不同的光影,但阳光本身,并无不同。”苏绾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明悟,嘴角露出浅浅的笑意,如壁画旁悄然绽放的一朵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