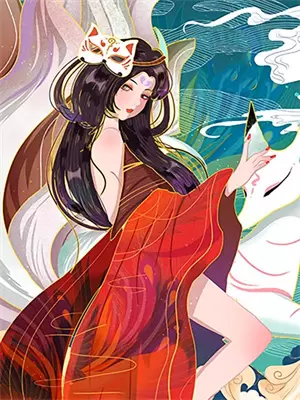第一章 老槐树与旧藤椅陈念第一次清晰地记得槐花的香气,是在她六岁那年的小满。
彼时她正蹲在老槐树下,看蚂蚁搬运一片被风吹落的花瓣,爷爷陈守义坐在藤椅上削竹篾,
竹片划破空气的轻响里,混着槐花簌簌坠落的声音。“小念,接住。
”竹蜻蜓带着槐花香落在她手心里时,爷爷的白胡子上还沾着星点碎屑。
他总爱在暮春时节做这些小玩意儿,竹篾在他膝间翻飞,像有了生命的银蛇,
转眼就变成蚱蜢、灯笼或是小巧的竹篮。陈念举着竹蜻蜓跑过晒谷场,
看见隔壁的阿婆在翻晒油菜籽,金闪闪的颗粒粘在她蓝布帕子上,像撒了把星星。
那时的陈守义还能背她走过三亩地的距离。每当放学铃响,校门口那棵老槐树下,
准能看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藤椅旁摆着个粗瓷缸,里面盛着晾好的金银花茶。
陈念会扑进他怀里,闻到他身上永远带着的艾草味 —— 那是清晨去田埂割的,
用来熏蚊子最好。“今天先生教了什么?” 他总爱这样问,
布满老茧的手替她理好歪掉的羊角辫。“教了‘爷’字。” 陈念掰着他的手指,“先生说,
上面是‘父’,下面是‘卩’,就像爷爷总背着我。”爷爷的笑声震得胸腔发颤,
怀里的陈念能清晰地听见那声音穿过骨头缝,混着他身上的艾草香,
酿成她整个童年最安稳的底色。晚饭时的煤油灯总带着昏黄的暖意。
爷爷的左手边永远摆着个缺角的青瓷碗,里面盛着给她留的溏心蛋。
他自己则就着一碟腌萝卜干喝糙米粥,喉结滚动的声响在寂静的堂屋里格外清晰。
陈念总趁他不注意,把蛋黄拨到他碗里,他察觉后又默默推回来,如此反复,
直到蛋黄被筷子戳得不成样子。“爷爷,奶奶长什么样?” 某个暴雨倾盆的夜晚,
陈念蜷缩在藤椅旁,听着雨点砸在瓦片上的闷响问道。煤油灯芯爆出个火星,
照亮爷爷突然怔住的侧脸。他放下手里的竹篾,从樟木箱底翻出个红绸包裹的相框。
玻璃面上蒙着层薄灰,里面的女人梳着两条粗辫子,笑得露出白牙,身后是同棵老槐树,
只是树干比现在细得多。“你奶奶年轻时,辫子能垂到腰窝。
” 爷爷的指腹轻轻摩挲着相框边缘,“她总说槐花蜜太甜,却每年都把最好的那罐留给我。
”那晚陈念做了个梦,梦见穿蓝布衫的奶奶站在槐花雨里,手里提着个陶罐,
蜜香漫过整个院子。第二章 褪色的怀表陈念上四年级那年,爷爷的手开始抖。
起初只是削竹篾时偶尔偏斜,后来连端碗都要洒出半碗粥。那天她放学回家,
看见灶台上的铁锅倒扣着,红薯在灶膛里烤成了焦炭,爷爷蹲在门槛上,
手里攥着块碎瓷片发愣。“爷,你怎么了?”他缓缓抬头,
眼里蒙着层白雾:“我想烧红薯给你吃,可……” 话音未落,那只总替她系鞋带的手,
突然剧烈地抽搐起来。去镇上医院的路有七里地。陈念牵着爷爷的衣角走在田埂上,
看他每走三步就要停下来揉膝盖,裤脚沾满草籽。秋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像两段快要断开的棉线。医生说这是老毛病,神经退化,开了些五颜六色的药片,
嘱咐不能再做重活。爷爷的怀表就是从那时开始走不准的。那是块黄铜外壳的老怀表,
据说是奶奶当年用三斗米换来的定情物。以前每天清晨,他都会把表贴在耳边听一阵,
然后对着墙上的日历校准时间。可现在,表针常常卡在某个时刻,像被冻住的溪流。
“它老了,就像爷爷。” 陈念听见他对着怀表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叹息。
深秋的某个周末,陈念在学校排练文艺汇演的舞蹈。她扮演的是小天鹅,
白色纱裙是用蚊帐改的,裙摆上还沾着爷爷补缀的补丁。演出结束时,
别的同学都被父母接走了,只有她站在槐树下等。暮色漫上来时,
才看见爷爷拄着木棍蹒跚走来,怀里紧紧抱着个保温桶。“爷爷来晚了。” 他解开桶盖,
里面是温热的红糖糍粑,“路上摔了一跤,幸好没洒。” 他的裤腿沾着泥,
手肘处渗出血迹,可递过来的糍粑却个个圆整。那天晚上,陈念躺在床上,
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咳嗽声。她悄悄爬起来,看见爷爷正借着月光数药片,手抖得厉害,
好几粒从指缝滑落在地。她走过去帮他捡,发现他鬓角的白发又添了许多,像落了层霜。
“小念,” 他突然抓住她的手,掌心烫得惊人,“要是爷爷忘了你,怎么办?
”陈念把脸埋进他的衣襟,闻到熟悉的艾草味混着淡淡的药味:“不会的,
爷爷忘了谁都不会忘我的。”可命运总爱撕毁笃定的诺言。那年冬雪来得格外早,
陈念放学回家,发现爷爷坐在堂屋中央,对着空荡荡的灶台发呆。“爷,我回来了。
” 她像往常一样喊他,却看见他茫然地转过头:“你是……?”那一刻,
灶膛里的火星噼啪爆开,却暖不透陈念突然冰凉的指尖。
第三章 手札里的光阴爷爷开始认不出人了。他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傻笑,
会把阿婆送来的鸡蛋放进米缸,甚至有次把陈念叫成 “阿月”—— 那是奶奶的名字。
医生说这是认知障碍,记忆会像被潮水冲刷的沙画,一点点消失。
陈念在樟木箱底找到个蓝布封面的手札。纸页已经泛黄发脆,上面是爷爷遒劲的字迹,
记录着从 1958 年开始的生活:“今日与阿月栽下槐树,
她说明年要在树下教娃娃认字”“阿月生了场大病,家里的米缸见了底,
我去山上挖了些野菜”“小孙女出生了,眉眼像极了阿月”……最后几页的字迹变得潦草,
甚至有多处墨团,想来是手抖得握不住笔了。陈念坐在老槐树下一页页翻看,
阳光透过叶隙落在 “小孙女” 三个字上,暖得让人心头发颤。
她开始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爷爷。每天早上帮他系好鞋带,把药片按早中晚分好,
用温水喂他喝下。晚上给他洗脚时,
总能摸到脚踝处那个月牙形的疤痕 —— 爷爷说那是年轻时为救落水的村民,
被河底的石头划的。“爷,你看这是什么?” 陈念举起手札,指着某段关于槐花蜜的记载。
爷爷的眼睛亮了一下,浑浊的瞳孔里闪过微光:“蜜…… 甜。”从那天起,
陈念每天放学后都给爷爷读手札。读到奶奶教他认字的段落,
他会咧开嘴笑;读到她生病时的记述,他就不住地抹眼角。
有次读到 “今日小念掉了第一颗牙,把牙齿埋在槐树下”,爷爷突然抓住她的手,
准确地说出:“牙仙子会来的。”陈念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原来那些被遗忘的时光,
只是藏在了心底最深的地方。开春时,学校组织春游。陈念想带爷爷一起去,
却被他固执地推开:“我不去,会给你添麻烦。” 她没说话,
默默找出奶奶留下的蓝布帕子,在他胸前系成个漂亮的蝴蝶结。“就像奶奶带你出门时那样。
” 她轻声说。那天的油菜花田金灿灿的,爷爷坐在田埂上,看着孩子们追逐打闹,
突然哼起支陌生的歌谣。陈念凑近了听,才发现那是手札里写过的,奶奶当年最爱唱的调子。
风吹过花海,掀起金色的波浪,也吹动了爷爷鬓角的白发,恍惚间,
陈念仿佛看见两个年轻的身影,正牵着手走在时光的深处。
第四章 槐花与药香爷爷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他会突然想起陈念的名字,
甚至能准确说出她的生日;有时又会把筷子当柴禾往灶膛里塞。
陈念渐渐学会了在这些起伏里找到平衡,就像在摇晃的船上稳住自己的脚步。
五月槐花开得最盛时,爷爷的咳嗽加重了。陈念记得手札里写过,
奶奶曾用槐花和蜂蜜熬成膏,治好了他的咳嗽。她趁周末爬上老槐树,
篮子里很快装满雪白的花瓣。树影婆娑间,她看见爷爷坐在藤椅上,正对着空气说话,
神情温柔得像在跟谁撒娇。“爷,你在跟谁说话呢?”“阿月说,今年的槐花比去年甜。
” 他指着枝头,眼睛亮晶晶的。陈念的心猛地一揪。她把槐花倒进陶罐,
按照手札里的方法,加了两勺红糖慢慢熬。蒸汽氤氲中,她仿佛看见奶奶站在灶台前的身影,
蓝布衫的衣角随着搅动的动作轻轻晃动。膏熬成时,爷爷已经靠在藤椅上睡着了,
嘴角还挂着浅浅的笑意。那天夜里,陈念被一阵窸窣声惊醒。她走出房间,
看见爷爷正蹲在灶台前,用勺子舀着槐膏往嘴里送,嘴角沾满了褐色的糖渍。
“阿月做的…… 真甜。” 他含混不清地说。陈念没有惊动他,只是悄悄回房拿出手帕。
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在爷爷佝偻的背上,像覆盖了层薄薄的雪。她走过去替他擦嘴,
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别离开我……”“我不走,爷。
” 陈念把脸贴在他手背上,那里的皮肤松弛得像揉皱的纸,“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暑假里,陈念带着爷爷去赶集。他非要给她买支塑料蝴蝶发卡,
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毛票。“阿月以前也喜欢这个。
” 他把发卡别在陈念头上,笑得像个孩子。回家的路上,爷爷突然在老槐树下停住脚步。
他抬起头,看着枝繁叶茂的树冠,突然说:“这树该剪枝了,不然要挡住屋里的光。
” 陈念愣住了 —— 这句话,手札里也有记载,是五十年前爷爷写给奶奶的。
她扶着爷爷坐在树下,听他断断续续地讲起过去的事。阳光穿过叶隙落在他脸上,
那些被遗忘的碎片,正像槐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回记忆里。
第五章 永不褪色的暖光深秋的某个清晨,陈念发现爷爷的怀表彻底停了。